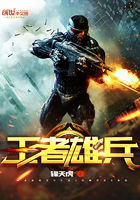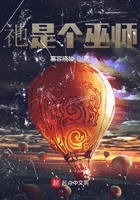那商贩所言之事虽非真实,但也不是凭空捏造,吐鲁番之地,久为商贾云集之所,日积月累,汉人便多了起来。梁姓女子,原名梁娟,祖籍湘西,十多岁时随父母迁徙之此,以买卖布帛权作营生。俄英支持阿古柏叛乱后,叛军骄横,强行没收了梁家布行,梁父鸣冤却被活活打死,梁母一时忍耐不住触墙而亡,可怜怜家中只剩了梁娟一人。偏巧这梁娟豆蔻年华,人又生的标致,窈窕身段,柳叶细眉,无意中被一盐商看上,买通吐鲁番一众蛮兵,便要强娶。
说来也巧,迎娶那日正是冬月头上,正赶上马伯远帅兵夺了吐鲁番。那盐贩自以为十拿九稳,一早骑了大马,赁了花轿,雇了鼓乐便来迎娶,谁知那梁娟忒认死理,竟挣脱出来,跑到守备府告状。若早一日,这女子早遭了毒手被拘了去,可巧正赶上伯远到来,便问明情由,叫衙役安排了梁娟,斥责了盐贩。此事倘或搁在他地,那盐贩自然无理,也就只能改恶向善去了;此事倘或搁在他日,伯远也会周密考虑,免生事端;偏偏这日刚刚平乱,万事缠身,伯远也就没顾别的,自个处理其他要紧事去了。
那盐贩自打被逐,便生了恨意,不过碍于吐鲁番换了政权,一时无可奈何。这日,他又去喀喇沙尔贩运盐土,一路走来,自然是处处说吐鲁番守备的不好。喀喇沙尔守备也是阿古柏麾下悍将,此人名叫布鲁花,诡计多端,心思缜密,偶然听得盐贩之言,便编造了马伯远贪恋梁娟容貌、在吐鲁番腐化堕落之事,一来借清廷之手铲除对头,二来败坏清军名声,三者也可以叫清军内部互相猜疑。
盐贩贾徒,来往南北,今日他讲,明日便有更多人听;又兼新疆地广,城镇之间距离颇遥,旅途人人困顿,更喜拿此花边新闻作乐;不得半月,此事竟越传越广,愈描愈真,大半个新疆都有了耳闻。俪如闻听的便是这些。
入疆以来,已经数月,虽以恪尽职守为乐,时间久了也难免显得孤单。那梁娟既是湖南人氏,算来与伯远也是半个同乡,伯远又怜起命苦,也就少不了接济,梁娟受人有愧,也就缝缝洗洗,尽点绵薄之力,两人走得近些倒也不是虚话。
这日伯远了了公差,辞了府衙,便去城中驿站查视,途中经过梁家,顺路便进来串门。梁娟见守备到来,忙沏了茶水,迎请伯远座下,只是不如往日热情。两人聊了一会,伯远见梁娟支支吾吾,似乎有甚话不好直说,便鼓励她道:“家里可是有难处?”那梁娟忽然敛衣跪倒,道:“大人,请您以后别来我家啦。”伯远不防,忙上前搀她起来,梁娟坚辞不肯:“大人若不答应,小女子决计不起。”伯远只得点了点头,说道:“我答应你,只要一样,细中原委还请详述。”那梁娟说道:“大人可能有所不知,前日我在那南山集市路过,听一伙人说得有趣,便凑过去听。当时也有我认识的,不认识的,那些认识的见了我如见了瘟神早早躲去,我觉不妥,便详细侦听,你道他们说些什么?”伯远忙道:“说些什么?”
梁娟回忆道:“他们说大人救我绝非为公,实则私欲作祟、包藏祸心。”伯远见他激动,不忍打扰,静静听她详述。“他们说你赶走那盐贩,一则贪他钱财,二则为了霸占……霸占我。”言语未毕,脸颊已是绯红,接下来之言便是絮叨:“这项罪名,小女子实承担不起,小女子名节倒在其次,大人若因此坏了名节,岂非是我的不是?”伯远闻言,轻轻道了声“知道了”便拂衣而去。
其实这日比俪如所闻还早几日,伯远闻言梁娟所言可能也有道理,此地毕竟民情复杂,大国角力,稍有差池便会前功尽弃。只是伯远近日虽刻意与那梁娟保持距离,城内谣言却越演越凶,有的说做贼心虚做样子的,有的说刻意掩藏实则暗通款曲的,及至今日收得俪如手书,才恍然大悟,吐鲁番必定混了奸细进来,故意混淆视听、蛊惑作乱。当即手书一封,递给哈密新任守备杜迁,劝他安定民心,细查究竟;另书一封递给左帅,一则讲述事情之来龙去脉,二则劝谏大帅察人防人。
两封书信既毕,伯远点齐兵将,从中择选精明矫健者五十人,十人一队,共作五队,在城中沿东西南北中猫定,打探消息,细究奸细。又选出聪慧敏捷者五十人,终日济困扶危,安抚百姓。同时请了当地士绅,烦请他们讲解经义,劝民为善;又告知有司,严惩恶意造谣者。吐鲁番地处要冲,往来商贾颇丰,伯远就在城东、城西各设置市集一处,派执法无私、威望持重者主持商贾之事。
一应事务安顿妥帖,伯远手书给俪如一封,既为辨别清白,也当好生抚慰,书中俱言往来之故事,备述局面之诡谲,叫她一切安危为上。正是聪明人遇囫囵事,欲解囫囵却糊涂。预知俪如情势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