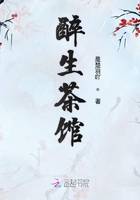下午,经过了在城门处的试探后,袁思德认为他已经基本的探了一下陈柳的底,而陈柳也觉得在跟他聊下去怕不是就要去唱《铁窗泪》了。
也一路大家都没有谈刚刚的事情,又恢复了陈柳东张西望,袁思德充当导游介绍西安城景色的时候。便是直走在东门大街上,过了行都司后众人右转,前方远远的便能看到路尽头高耸的城门和,原来那就是秦王府的府城了。
之前不说话的夏把总倒是像吴达和陈柳介绍起萧墙,内里还有道护城河,过了河才是砖城的宫墙。便又在吹嘘秦王府的宫墙高二丈九尺五寸,下阔六丈;女墙高五尺五寸;城河阔五丈,深三丈。
“嘿,这数重墙数重壕的待遇,天下藩王也只有我们秦王府可以有,虽说总有些酸溜溜的穷酸攻击说王府这是逾制,可这是太祖高皇帝特准的,他们到处说又能怎样?咱是什么?天下首藩!那些文人攻击我们王府这的那的,天下都是皇家的,秦王是天下首藩,便是又增了庄田,那也是他们的福气,看得起他是不是。”
“休得胡言乱语,这话便是皇上都不敢说也不会说,轮得到你?休要多嘴!”
“是,道长,这不是就是想介绍一下王府,冲冲门面吗。”
夏把总便是不住的陪笑道,袁思德也不睬他,如今国事颓唐,正是需要中兴之际,藩王们不为国出力,反而四处找事,本身就让皇帝非常不满了,还这么招摇便是生怕言官不会盯上自家王府。尤其是鞑子入寇据说部分围了济南府,而皇上正心烦意乱,而王府内又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在这时在外面乱说话,节外生枝。
当下便是入了灵星门后,夏把总交接了差事,袁思德便以王府私物为由拒绝了夏把总进一步跟着的请求。
“看来很多人是巴结你啊?”吴达似笑非笑的看着袁思德,袁思德也心知这是对刚刚他嘲讽的报复,便耐心的解释道:“不过是人红是非多,在外人看来我是近臣,有人私下咒我,也有人艳羡,当然更不缺巴结贫道我,以为这样他就能被看中平步青云的人。当然,也有人是想盯着我一举一动,好找到让我,让那位万劫不复的证据。”
“啧,难怪说天家无亲情,一个没有权只能天天在这破囚笼里散步的王位,还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大位不知得打成什么样。”
“这位相公慈悲,却只知其身陷宫城兮哪得自由,却不知一事。”
吴达见他突然礼貌了起来便知他又有什么坏心思,但还是顺着他配合道:“道长慈悲,还望道长指点迷津。”
袁思德做得到高人悟道状,颔首,微笑,念了句“福生无量天尊”,这才缓缓说道:“王爷除正妃之外还有妻若干,宫女无数……”
吴达心知此人果然吐不出象牙,便快步离开,袁思德赶紧上前带路,过了南过门和吊桥,又一路带着他们下了马,步行进了南的端礼门,而董策和成管事却因为运输货物,有了袁思德出示的特许,反倒是得以驾车进来。
便是又右转,进了一偏殿,地上正中画着八卦,中间太极的位置摆着一丹炉,便知道这是,陈柳和吴达便知是他炼丹的地方,不多时,成管事和董策便抬了箱子进来。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袁思德唤了几声,进来一个小内侍,“去,请三殿下,铜镜已到。”又摸了几文铜钱出来“传完话后若是无事自去玩去,我这今个有客人,不需你在这伺候着。”
那小内侍便喜出望外的跑了出去。袁思德见他离开了,便又轻声地问吴达,“确认东西完好的吗?”
“你问过好几次了,完好,而且车队里还有一片完整的备份。”
“那我就放心了,你的官服带了没?”
“带了,总有需要狐假虎威的时候,怎么?”
袁思德瞥了眼陈柳,:“明日不要乱走动,晚上王府有宴,带上侄子一起来。”
陈柳听了倒是有点纳闷,虽然说作为一个吃货听说有宴会可以去还是很心动,但是明显这种级别的宴会,自己去要么是当枪使,要么就是引荐,总之,都是他不太喜欢的场合。
而袁思德显然没打算放过他,一本蓝皮的书便放在了陈柳面前:“秦王世系谱,今天把他看一遍,重点是最近的。明天说不定会有人问你,难得不记得倒是不丢人,但若是基本的王爷祖上是谁都弄错了,便会引来不必要麻烦。”
陈柳想了想,好奇地问了句:“王爷的祖上不就是上一个王爷吗?或者最多兄终弟及,为什么会说容易弄错呢。”
成管事和董策做眼观鼻鼻观心保持沉默,他们不是第一次来,自然明白其中缘故,袁思德做故要烧水沏茶待客也闪了出去,吴达一脸古怪的看着陈柳,想了想还是说道:“关于天家的事,多想总是没错的,但是千万不要说出来。”
谜一样的气氛弥漫在了整座宫殿中,如同薄雾一样,乍一看都在那,却又看不真切。陈柳明白了自己还好面对的都是自己人,不然刚刚的话便会引来麻烦,但是一方面,这又着实如同猫挠痒一样,令他好奇掩藏在这危险的王威下,秦王府的世系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秘密。
但是此刻他却是不能表现出这样,便乖乖地如同好学生一样将书塞入怀中。吴达对他这一举动很满意,因为若是等会那人来了,看到陈柳在看世系图,或者陈柳问了什么,总之是不好的。
就在袁思德终于手忙脚乱的烧好了水给他们沏茶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迅疾的脚步声,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哈哈哈,道长,小子等你佳音多时了,可是吴先生带铜镜到了?”
袁思德心思一恍惚,便是在给董策沏茶时漫了。也顾不得收拾,将铜壶放回桌上,便整理了一下衣服快步走向门口,见到陈柳时,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便叮嘱道:“不管待会那人做啥,或者他是谁,记得,不卑不亢。”便又提起拂尘,在距门口几步处站定。
“道长今日怎的在门口候着小子,可是折煞了小子啊。”陈柳倒是心有好奇,明明是王室中人,为何如此自下身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