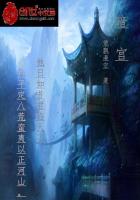魏藻德冷冷地说:“这偌大产业,与我等有何关系?那位每次献饷,都是直接交给宫里,发俸发饷,何曾过我们的手?既然咱们沾不到好处,又何必操心?落到黄雀、渔人的手里,咱们可能还能沾点光。”
光时亨点点头,一饮而尽,说:“上面那个刚愎自用,忌刻寡恩;下面那个更是只用私人,丝毫不敬文臣。咱们也不亏待谁,唯有作壁上观!”饮罢,手指转动酒杯,忍不住说:“这酒杯实在精美,让人爱不释手!”
陈演笑道:“若非如此,那裕东皇店哪来的银子?”
“何止裕东皇店!”光时亨说:“还有那裕东钱庄,金镰粮行,哪一个不是日进斗金?东宫那位,尚在冲龄,为何有这样的心计才气?”
魏藻德哼了一声,说:“他行的,尽是管仲、桑弘羊那套杂学,与仁君之术没有一丝关系!名曰筹饷,实则敛财;看似不曾搜刮,其实与民争利!”
“与民争利!”陈演击节赞叹说:“一语道破天机!”
“与民争利,这实在是弹劾劝谏的好题目!然而,他《肃奸条例》在手,随时都能以‘毁谤储君、离间骨肉’的罪名实施构陷,谁敢公开议论?”光时亨说。
魏藻德把酒杯一放,说:“钳制百官之口,京城已经是道路以目了!他以储君之位,嚣张跋扈至此,岂能一直容他?暂时不用多说,且看眼下这一战如何!”然后说微微一笑道:“自古以来,未闻太子如此聚敛!诸位放心,这些产业早晚都是朝廷的——不管哪个朝廷的,都会有我们文臣的份。”
光时亨忙问:“如果他侥幸击败李闯呢?”
“太子年纪尚幼,筹饷、练兵、打仗,实在太辛苦了。越是英姿天纵,越是要养身惜福啊!而且,一旦李闯败退,大难纾解,太子应该及时大婚,传宗承嗣呀!”陈演笑道。
光时亨会心地笑了:“无论成败,我等进退自如。”
第二天朝会,大臣们一齐恭贺真定大胜。崇祯面带微笑,答礼格外响亮。
但是谈及京城防务,众臣并无建言。崇祯问魏藻德,魏藻德只是作揖,说:“一切伏维皇上圣裁!太子提督京营,统筹粮饷,想来自有安排。”
散朝以后,崇祯才回到乾清宫,就接到禀报:“太子回京了!”不禁大喜,说:“叫他骑马入宫来见朕!赐他紫禁城内骑马!”
此时,太子大军已经抵达京城西,准备绕到北边,从德胜门入城。
黄得功、高杰在这里扎营,都带着部将出来观看,亲眼目睹了太子大军从南边浩浩荡荡过来了。最前面的是前面的东宫师,人人骑马,蹄声隆隆,烟尘飞到半空;艳阳当空,大旗飘扬。
黄得功在营门口看了,道:“这骑兵,看不出多厉害呀!只穿战袄,未着铠甲,马札更是没有,如何冲锋陷阵?塘报称剿灭闯贼南线大军,莫非是吹的?”
部将田雄在一旁道:“显而易见是吹的。朝廷的文章,都是书生坐在屋里编的。”
一批前锋过去,只见大纛之下,一个少年将领金盔金甲,骑着白色骏马,被一帮侍卫的簇拥着缓缓驰来,显然那就是太子。黄得功和高杰都离开自己的营门口,一齐上前跪地迎驾。
“微臣黄得功,叩见皇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微臣高杰,叩见皇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朱慈烺停马,接受两人的参拜,抬头望望两个营寨的门口,那边跪倒大批部将校尉,才开口说:“你们二位,勤王来得迟了!”
黄得功一愣,瞬即道:“微臣有罪!只是微臣驻守庐州,掩护中都、南都,责任重大,不敢轻离。待到防务安排妥当,才星夜兼程,奔赴京师!望殿下恕罪!”
高杰瞟了一眼周围的如林侍卫,慌慌张张地说:“微臣自山西辗转而来,一闻勤王之诏,立即奔赴京师!”
“尔等心思,孤全知道!”朱慈烺冷冷一笑:“不是孤斩杀刘泽清,讨平山东镇,你们是不会来得这么爽快的!”
黄得功汗发沾背,伏地说:“微臣忠心,苍天可鉴!”
高杰也跟着伏地说:“微臣与闯贼深仇大恨,不死不休,敢不忠于朝廷?望殿下垂鉴!”
“黄得功,你的本性,还是不错的;忠心,也是有的。但是,一定要不忘本心,不为身边人扰乱,好好为朝廷尽忠!”
“微臣遵旨!”
朱慈烺又转向高杰:“好你一个高杰!自潼关败后,一路奔逃,从潼关逃到陕北,从陕北逃到山西,又从山西逃到直鲁之间!若不是最终赴京勤王,刘泽清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
高杰叩首于尘埃之中,说:“微臣死罪,谢殿下宽恕!”
“你们都起来吧!”
“谢殿下!”
朱慈烺忽然笑道:“高杰,你的两个故人来了!”
高杰惊疑地向南一望,只见数匹骏马从路侧奔来,后面还有马匹拉着一辆槛车。前面被人簇拥着的,分明是老上司孙传庭!
高杰故意表现得就像狗见了主人,拱手作揖,热切地喊道:“孙帅,高杰在此有礼了!”
孙传庭表情冷峻,气宇深沉,直到高杰面前才停马,开口道:“高杰?你很好!”
高杰尴尬地说:“卑职不好……”
“不,你好得很。潼关一败,部将星散,纷纷降贼,你倒是不错,死不投降,一路逃到这里。”
“卑职惭愧……”高杰扭扭捏捏地说:“卑职心里是装着朝廷的……孙帅,卑职想你啊!潼关一别,真没想到还能生见督师!卑职死而无憾了!”
“你一路东撤,到此勤王,本帅也无话可说。只是你在奔逃途中,一路掳掠,残害百姓,实在罪孽深重!”孙传庭忽然变色,厉声道。
高杰吓得一下子跪倒在地,说:“督师明鉴……卑职撤逃路上,粮饷全无,不得不向百姓借粮;兵马溃散,不得不拉丁壮入伍,这都是迫不得已,日后再也不敢!望殿下、孙帅恕罪!”
孙传庭一字一顿地说:“如今太子奉旨伐罪,重申大义,为生民立命!时时处处,以爱民安民为要,力挽民心。你所率之兵,若是毫无约束,只能为朝廷树敌,为太子招怨!朝廷留你何用?”
高杰擦了把汗,泣道:“卑职知道了!从今洗心革面,约束部伍,不敢再有滋扰百姓之举!”
朱慈烺开口说:“既往不咎,一切自今日起!从今往后,斧钺由得你,富贵由得你,就在你一念之间!”
高杰向朱慈烺叩首说:“多谢太子殿下大人大量,给卑职一条生路。微臣一切铭记在心!”
朱慈烺望了一眼肃立一旁的黄得功,说:“黄总兵不错,率兵征战江北,不曾掳掠百姓,父老都愿意为你立生祠,可见民望之高。”
黄得功忽然得到赞誉,忙躬身拱手道:“谢殿下谬赞!微臣尽职而已,不敢承当。”
“你们给孤记着!”朱慈烺忽然在马背上坐直,朗声道:“民心!民心!民心!重要的事情,孤说三遍。朝廷要扫平流贼,再造太平,就必须赢得民心。军事仗要打赢,民心仗更要打赢!否则武力再强,天下也永远不能平定!”
“微臣受教!”“微臣铭记!”黄、高二人连忙答应。
朱慈烺补充道:“民间有云: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可见扰民之兵,甚于流贼!孤不能一手剿贼,一手纵容官兵扰民资敌!所以,扰民之兵,若是知错不改,只能当流贼一样剿除!”
高杰打了个冷战,说:“微臣铭记!回去之后,立即教训将士,整顿军纪!”
朱慈烺点点头,说:“高杰,你还有个故人在后面!”
“敢问殿下,是谁?”
“刘芳亮!”朱慈烺断然道:“拉上来!”
士卒推动槛车,呈上前来,刘芳亮头颅留在囚笼外面,目光如电,望见高杰,笑道:“高杰?你是义军叛徒,老子手下败将!”
高杰一看,吃了一惊:“果然是刘芳亮?”
“哈哈哈!正是!”
“你身为李自成心腹,也有今天?”
“老子落到如此地步,与你何干?这都是朱家小儿造的铳炮狠毒,老子才吃了大亏,输个干净!若是靠刀枪,你们都不是老子的对手!”
高杰有些不理解,问:“你的南线二十万大军呢?”
刘芳亮哈哈大笑:“老子号称二十万,实有人马八万!带到真定有五万,被朱家小儿坑了!”
高杰倒吸一口凉气,黄得功则暗暗心惊:太子练兵不久,整顿京营也不久,如何就如此强悍?其铳炮究竟犀利到何等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