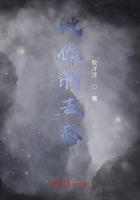教室的扫帚只有两把,每次扫地都是和同桌两个人一起做值日生,在家时就没怎么扫过地,我扫地也总是只有一个扫地的样子却没能把地扫得很干净,在家我觉得扫帚特别的硬,因为那是就地取材用竹子枝做的扫帚,又大又长的竹子扫帚像一柄大刀,很多层竹枝捆绑在一起看起来就觉得很厚重,我也拿过扫帚的柄,却轮不起来,只是拖着它在地上走一个圆形,然后松手将其丢弃。家里也不止这一个扫帚,还有一种叫铁扫把的植物做成的扫帚,干枯之前的质地就像一株蒿枝,可是它的结构却像一棵开枝散叶的树一样,主杆上分出很多细枝,干枯之后就变成黄橙橙的枯枝,像是专门为做扫帚而生的一样,把主杆部分稍微修饰一下,然后再一捆就是一把最受农村人青睐的扫帚了。这个扫把我也拿着玩过,比较轻可以很容易的舞动起来,只是扫地时要用手按着才能把地的上石子和枯枝扫走。
屋后有一片很老白杨树,风一吹常会带下来一些断点的枯枝,夹杂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的石子,我去扫却看到地上只留下一道道扫帚划过的痕迹,按着扫帚去扫就感觉掌心被硌得生疼,扫帚柄满是剃掉小枝留下的突起。
学校里又轮到我和同桌一起扫地,本来在学校里就没有特别计算过哪天是谁扫地,听别人说了就去扫,就想平常不看课表也认不得课表,谁来了就是谁。教室的扫帚是高粱穗做成的,上边还残存着一些高粱种子,没吃过高粱米的我一度以为高粱只是用来做扫帚的。
高粱扫帚特别的轻也很柔软,偏偏在教室里又有那么多桌子、板凳,仔细一看全是桌子腿、凳子腿,像一群立着的雕塑一动不动的,而正真的人也就是这些亲爱的同学们,他们有时也成了雕塑的帮凶,在座位上一动不动,有时又像被狗追急了的兔子,在教室里疯跑。
柔软的扫帚将过道的铅笔屑一下子弹起好远,而桌子的脚护着那些纸屑、木屑不让它们被弹走,板凳的脚也在桌子下边别着,心浮气躁的我一手拿扫把一手推搡板凳,终究我还是忽略的那些藏得不明显的纸屑、木屑。没来得及去下一排扫地身后又出现一个飞驰而来的人,慌张而夸张的表情,在撞到我时才说了句让一下,然后将我一推又跑到了教室外边。一排一排只是简简单单挥一挥扫帚,虽然没有没有扫得很干净,却把每一寸地面都经过了一遍。坐在座位的人也总是那样无所顾忌的坐着,扫到他脚边再到跳过他去下一排,他只是偶尔换一下落脚的位置恰好就把高粱穗子又踩掉了一根。
像是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路过一座座山,遇到一个个人终于到了教室的后面,孤独的垃圾桶已经等候多时了,铲起的垃圾更多的是一层土,倒进垃圾桶里扬起一阵灰,好像在庆和值日到此结束。
见过这么多扫帚,它们也都是为扫地服务的,我却没觉得有哪一个是用着特别顺手的。它们生来就是能够变成扫帚的,哪又有什么用呢,有时候几条桌椅板凳就让扫地这件事变得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