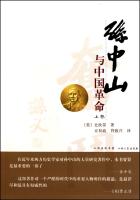山上除了草就是树,在山林之中若是有悠闲的心态倒是一种享受,然而本没有任何负担的小孩子们身在其中只会觉得非常无聊。鸟叫声是无聊的、蝉的鸣叫是焦灼的,徐徐的微风只是过客,斑驳的树影也只是在孤芳自赏。虽然身边有这么多事物相伴却总不能在心里融合它们,依旧感到一切都很孤单。
表哥常去放牛所以他学会了打发时间,在石头上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可有时他又突然动一下,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睡着。
而表姐也不在这儿了,由于表哥抢了她的桃,她生气的走了。走的时候还大骂表哥自己没长手,表哥则在哪时说让她多摘几个过来。本来负气而走的表姐不搭理表哥了,这时又像是受到了提醒只连连答应,既不骂人了也不埋怨翻越山包不好走了。
他们就是这样吵吵闹闹的,总会在各种事上吵架然后再和好,接着又会吵起来。而我常作为一个附庸被两头争抢,摘桃我不愿意去,表姐只说了一句不去算了就独自走了。我看着表哥得意的笑和手中分到的桃,又陷入了犹豫之中,然而不想离去依旧是真实的想法。
不远处雍家兄弟两人在细心地给牛赶蚊子,小的那个居然还多才多艺,他嬉皮笑脸地唱歌,听到后来我才听出他把我编入了他的歌里,虽然只是把我比作牛在吃草、马在打滚这类的话,也让我很生气。
本就在一个孤寂的环境下,也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表哥还睡起觉,表姐也走了,而且还有人挑衅。看到天空的一朵圆圆的云,我开始想念桃子,也对表姐迟迟不再来感到失望。看到表哥弓着背对着我还是在睡大觉,我开始后悔没和表姐一起离开这儿,看着身旁的荒草枯木又感到一丝绝望。
终究表哥又重新活了,他削了一节柳树枝做成哨子,拿起来吹了吹可以响。接着他又剥下一节树皮卷成牛角状,再从一棵木瓜树上摘下几枚刺把树皮钉起来,最后装上哨子。一个号角就这样做成了,我看得目瞪口呆,拿到这个号角就激动得不得了。
表哥拿着号角重新找了一个较高的地势坐在上面,仿佛一个王者,还时不时吹一下号角。雍家兄弟对号角并没有什么兴趣,可能不是第一次见了,然而对这个制高点却情有独钟。两边的大哥都爬到了制高点的大石头上,像是有什么魔力一样谁都不下来了。
下午的蚊虫多了起来,牛也变得不安分,开始变得爱跑了。只听到哪边那个小的总在咋咋呼呼地通告这边,要么说表哥家的牛跑了,或者说自己家牛又跑了……
我表哥听到自家牛跑了到总会客气地喊那个小的帮忙赶一下,而雍家大哥听到小家伙喊叫他们的牛跑了就会直接命令小家伙赶就行了。反反复复赶了好几回牛,小家伙终于爆发了,说他不管了。于是表哥亲自去牵住自家的两头牛,而雍家两兄弟却相互赌气谁也不管了。最后雍家兄弟只剩两头牛,还有一头丢了不再周围了,可他们还在责怪对方失职,匆匆找了一下也决定回家了。
刚回到大姨家就听到邻居家炸锅了,弄得鸡飞狗跳的。听到大人在谩骂怒吼,小孩在嘶声裂肺地哭。这不由得让人心惊胆寒,正在破鱼的表姐、做饭的姨夫和大姨都跑出来问怎么回事。
姨妈说牛贵得很损失大了,姨夫说那个小的鬼得很,打的好!而我想到的是帮别人忙可以得到一份人情和客套话;而一个家庭的亲兄弟往往没有客套,而且认为对方会处理。平平淡淡才是真,一起好好吃一顿饭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