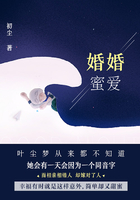清溪郡有个胤流年,胤流年里有江湖客,江湖客皆为江湖事,有三个便要赔银子。
说到这蒋宣政是何等人物,那是中原道家魁首真武观宣字辈大弟子,搁到中原武林便是小一辈里头排个座儿,他也敢坐一坐第一席!
行走江湖,便是要增长见识的。
这般事,却是头一回见着。
巧嘴刘也不恼,只是笑眯眯得看着,刚刚还指点江山、滔滔不绝的那张嘴如今却是严丝合缝的,似乎连气儿都不用喘上几下。
交过钱了,张嘴说话。
“梁王冢牵扯无数人的心弦,可那地方是个要人命的,没有三重天的功夫连沾都不敢。”
巧嘴刘张口吃茶,轻轻抿一口,既是品香又是润喉:“你们三个的功夫先不说,单说这年岁,不值。”
“小道答应了人,这趟浑水终归要蹚一回,才安心的。”
蒋宣政接了话,说起来这几回话茬似是都让他接了去,连那巧嘴刘都瞅着。思虑半响,巧嘴刘还是摇头:“你玉晓剑的名头不小,但到底也就是五重天的火候,进了那死人待得地方,有命进去却没命出来。”
“梁王冢的深浅,我多少也算是知道些。”
田七接过话来,他把自己随手拎着的朴刀往桌子上一摆,刀把手的柄儿使劲一扭,朴素的刀柄上便扭出一块烫金的印字,是古篆书的‘雷’字:“我们这一回过来,打听的也不是梁王冢的旁枝末节,我们要找那样式雷。”
样式雷!
巧嘴刘放下杯盏,一双铮明瓦亮的眼睛在三人身上来回转悠,最后,又拿起杯盏,收敛那骇人的眼神,只余下一帘笑意:“我只当诸位来此是为了梁王冢里那个醉人的梦,谁知你们原是盯上了那件东西。”
“它应该就待在郡城里,您也应该知道它的下落。”
田七指一指刀柄上映出的雷纹,接着说道:“这东西如今牵动着太多性命,已然不能让它待在这世上了,它要属于它真正的主人。”
“半个,”巧嘴刘打断了田七的话:“田家人顶多算是它的半个主子。”
那个‘田’字被咬得很重,也被拖得很长,长到让田七想到自己儿时父亲讲述族史时的咬牙切齿。那四个字就像梦魇一般缠着,就如同现在一样,田家人永远永远只是半个人。无论是江湖、武林、朝堂,只要有人的地方,田家人便是缺了脑袋的。
“梁王府已经空了。”
田七是这么接下来了,接的很用力。释鸿生看着田七,这个人比自己大不少,但现在他就是一个倔强的孩子,用这样近乎耍赖的方式维护着自己和族人的尊严。
但他其实没有尊严,田七是有尊严的。
释鸿生这般想着,他觉得巧嘴刘和蒋宣政也会这么想,也许不会。但是,田七是完整的有尊严的人,这是没错的。
“是,”巧嘴刘摆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仿佛刚才只是开了个顽劣的玩笑:“那和我这胤流年有甚么关系,你们该去花酌楼的。”
话说到这儿,便是论价钱的时候了。蒋宣政素手探袖囊,将一张方正票据按在了桌上,那巧嘴刘瞄一眼,摇摇头不接话。
又是一张,又是摇头。
待到蒋宣政第五次压上银票了,在最上头那张上折个纸角,一只手顺势压在那一小沓银票上,这便是压底儿价了,巧嘴刘再瞄一眼,手捻住了那沓银票的另一个角。
五百两,成交!
“你们还不了解咱这清溪郡,”收了银子便好说话,这位刘巧嘴儿也就真正张嘴说话了:“除开缴给朝廷那一份,咱清溪郡的银子一半归了各大家族和商会,另一半则归了三个销金窑。”
“花酌楼、胤流年,还有一个?”
“花酌楼号称是郡城里头第一大销金窑,可说到底也就是个窑子,他也配?”刘巧嘴接着说:“这郡城里头最大的窟窿埋在地下,吞进去的银子再没听个响。”
顿一顿,刘巧嘴儿压低了声音,吐出三个字:“叁难鬻!”
这三个字好似有着莫大的魔力,整个屋子里就因为这三个字便如冻结一般,一种莫名的气氛充斥着这个屋子。
“活人安居乐业,死人的手倒是伸得够长的。”
蒋宣政眯着眼,手搭到了剑鞘上:“难怪这东西难找,原来是叫死人拿去了。”
“所以这样式雷也是个难啃的骨头。”
刘巧嘴说道:“这玩意原本不值几个钱,可谁叫这几年梁王冢的事让人挖出来大做文章,这东西也就值大钱喽。值钱的东西,那些小鬼比狗都灵,被他们拿了不奇怪。”
“小鬼要赚钱养阎王,这买卖他们何时做。”
田七似乎很熟悉那个‘叁难鬻’的作风,说话干净不拖拉。
“这得进去才知道,他们的买卖不作外面的活人。”
刘巧嘴说完了,留下一截修长细竹在桌上,走到门口,突然回首补了一句:“你们要等得人已经到了,城东有家不错的客栈,她们便在那里歇脚。”
其实,刘巧嘴还是个江湖人,至少他还保留着当年走南闯北那股干脆劲儿,还留着一身的义气。
田七拿了那细竹筒儿,用手捻一下,破开了那上头薄薄的封纱,扣出一卷黄纸。拿手摊开,上头是拿工楷写得七个字‘天字十六绿牡丹’。
出了茶楼,便少了几分喧闹。
可到了城东,便赛过了区区一座茶楼。
城东多市而少坊,市井中人多了,便显得热闹些。叫卖的人顺街走,各色商铺也是沿街开,在茶楼里头耽搁许久,如今已经接近晌午,但凡有点余钱的多回朝街边面摊饼铺去,或是一碗撒了酱角菜的素面,或是俩热气腾腾的胡饼,要是能尝着那包进去圆滚滚羊肉丸子的馄饨,便是了不得的一餐了。
再富些,出入不是缠着贯钱就是揣着银子的,那就能找个像模像样的酒肆食楼,点俩或腥或苏的小菜,再来上点小酒,那就是城外头的泥腿子想都不敢想的神仙日子了。
那若是能点上十数道菜又当如何?
那便会像是这位清秀可人的小道姑一般尴尬了罢。
水晶鸭、酱肘子、笨鸡汤、元宝肉、玉兰虾、白云猪手、红烧鲤鱼……
一连串的鱼肉硬菜,便是郡城的郡守,若无开府设宴也决计摆不出这么一桌。
“说说吧,这就是你信中说的妙音谷规矩众多,怕耽误了大事,干脆在郡城碰头?”
蒋宣政抱着剑,因为这桌上再没有能挤出一块可以放下剑的地方了,一双比女子还灵秀的眼睛里好像能点着火来。
正对着他的便是他之前说过的师妹了,亦如上文说得,是位清秀可人的小道姑。
“这个、那个……”
小道姑端端正正坐着,搜肠刮肚得找寻可以为自己开脱的法子,可小脑袋里头一片空白,一个字也说不出,只能低着头、红着眼,一副梨花带雨的可怜样儿。
“哎,算了算了,既然菜都点了,便边吃边聊吧。”
再看看小道姑逐渐绽放的笑颜,蒋宣政也只能没好气地打趣几句,便掏出随身的锦帕拭去小道姑嘴角的油污。
接着,蒋宣政便招呼同行二人入座同吃,田七大刀阔斧提溜个凳子往那酱肘子边上一坐,边拎起一块往嘴里塞,丝毫不与人客气。释鸿生虽然入了席,却是独要了一碗素净的阳春面,细细品味着手艺人的这股子劲道。
蒋宣政恍然赔礼,说:“小师傅莫不是还想着那乱坟岗里尸山血海,方才难以下咽,却是小道的过错。”
释鸿生抬起头来,嚼断了嘴里的面,笑道:“世间之事何其多,甚于地狱也胜似佛,我着相一日已然是莫大的过错,哪里会再生痴嗔。”
“我随不知道你佛的事,”田七也劝道:“可也知道佛经之中戒酒戒荤,却并没有戒除腥食,这些菜本与你无有因果,算得上是净肉。净肉难得,今日不吃,就不知那顿上才能尝得。”
“正因如此,才吃不得。”
释鸿生看着那些肉菜,说:“小僧才疏学浅,这些年在山上青灯枯佛便以为生了几分佛性,谁料刚下山便一朝破去。净肉随不犯佛戒,却犯我戒,今日食肉,明日便不知要找什么由头寻些‘净肉’来食,人欲无穷,自当从根治之。”
说到这,话便不好接过去了。幸好有这位小道姑邀田七拼酒,才勉强圆了回去。
一张桌,五个座,三个男郎,两个女娃。
和尚有面吃,刀客吃肘子,一个小道姑逮找啥就吃啥,胃口好得很,那除开一味跟着那师妹的道士,剩下的一个女的呢。
这就是最奇的地方了,整个客栈如今可是满满当当,一半是看哪家的败家子儿吃顿饭还摆出这般架势,另一半便是来看貌美如花的绝代风华。
一个只看得见酒肉的刀客,一个眼中纳得下师妹的道士,还有个压根就没睁眼的和尚,任凭身边坐着何等佳人,硬是没一个开口搭话的。
酒过三巡,那一大碗的阳春面也见了底。
释鸿生一直闭着眼,却看得清清楚楚,田七吃了两块肘子,蒋宣政只是尝了几口酒,更别提自己身边坐着的女子,连滴水都没有沾过,可这满满一桌子就这么空了。
非要说,就是那小道姑的嘴角总是拭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