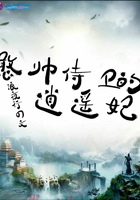巴黎圣母院属下的孤儿院里的几十个孩子,随着城市市政官先生及夫人的好心帮助,将孤儿院迁到了近水绿化的城市一角。原本冷淡、严肃、神经质的孩子们一个个的开始舒缓了神经,慢慢的恢复了与年龄相彷的心灵。原本一片寂静的孤儿院仿若变成了一间喧哗声不断的小学校园,吸引了附近小学背着小书包穿着校服的学生在孤儿院的大门外向内瞻望:并且好奇的询问那户大房子里是否新搬进了人家,里面可是住着何人?
巴黎圣母院里的小少爷呀,终于的愿意让家里的女仆拉开高高的窗帘,让阳光照进自己的房间。看那窗户的阴暗角落,跟光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长期的阴暗后的光明,仿是一个人的心灵悄悄的起了变化。
巴黎冬天的街上,缓步行走着戴礼帽手拿柺杖的绅士及戴淑女帽着长礼服裙戴手套的女士们;他们相互间都保持着平行的目光,隔着礼貌的距离;若是遇着了熟悉的人,只是轻轻的行点头礼。一位手拿公文包的中青年没有亮点却以极轻快的身姿及脚步走进了法堂。齐小圣、祝火、罗沫、马春等几个人的案子已经在法堂里拖了几年。那还是几年前,大法官正准备审理那桩案,岂知巴黎圣母院里的夫人难产,大法官不也是人、也有人的人情世故及焦虑?他在第一时间放下了手头工作赶到了巴黎圣母院,同好多市政官员一起,祝愿夫人能够顺利的产下胎儿;为此,大法官在心里起誓:“只要夫人此胎顺利产下胎儿,我大法官甘愿五年里停下手里的一切公务。“随着夫人的孩子健康的出生带来的喜悦,巴黎的天空反倒是多了一丝阴霾。在小少爷出生的几日后,从别的地方也有一对抱着新出生女婴孩的夫妻千辛万苦风尘仆仆的赶到了巴黎:为了一桩灭门夺家的案子。那位父亲用手去敲大法官家屋外的石院墙,手都敲出了血来,可是屋内的大法官却不为所动。后来,终于听不见响了,待大法官的家人去屋外查看,那对夫妻双双暴毙在院墙外,妻子的手里还抱着位婴孩。大法官出来见了,吩咐人将那对夫妻找个地方给葬了;然后将小婴儿捡回了屋内。大法官对家里的嬷嬷説:”这位女婴呀,今后就叫唐黎;你给她找户人家,将她给照顾起来吧。“
小少爷已经长成了八九岁的小绅士,穿着小礼服手拿小拐杖戴着小礼帽的模样跟家里墙上挂着的老爷像就像一个模子刻出的大小版;今天,是他第一次走进大法堂陪审;也是大法官那么多年后第一次走进大法堂。
小少爷在审判前的那么大半个时辰内,开始翻阅齐小圣、祝火、罗沫、马春几个人的案卷。用小孩子的眼光来看,那呀,都是青春年少者在精力充沛下的肆意妄为;而状告者也是奇了,都是那几个人家里的亲眷。正在此时,又送来一桩新案子:一位叫唐黎的小女孩,还属一个孩童,却因偷拿拐骗而成了惯犯,再一次被拘。
大法堂的墙壁内外似乎有个什么,唐黎小女孩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似乎带着丝惶恐的在张望;她反倒丁点也不怕法官们。小少爷忍不住也随着她的眼神去瞧了瞧,窗外似乎有一丝影子快得惊人的一闪而过;莫若眼花?他顺着眼光看了看外面的天空,感觉似乎有点什么。
大法官环视了一下四周,敏锐的感觉到今天的案子似乎是审不了啦。
正在此时,一架四轮马车急冲冲的载着一位相似乎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到了。她衣着得体,眼神凝重,然后步履庄重的直接走上了审判席。法官宣布,今天的案子呀,全部将由她来审理。原本静得诡异的大法堂内瞬间有了交头接耳声,有听众像是知道此小姑娘的来历一般的在悄悄的説:”听説这是教皇的亲孙女,亲自培养出来的;从五六岁开始,就被送到了大名鼎鼎的查理大法官名下耳濡目染的,这种小案子看来今天是要有个结果的了。“
小姑娘开始翻阅案卷,然后宣布齐小圣、祝火、罗沫、马春几人所犯之罪过属无罪,但却必须要接受所在地的监管及家庭劳教;未来,必须由各自所在地的地方官监管考核属健康青年并且得到其家族长辈尤其是状告者的无过认可,方可获得其原本应该拥有的有为之人的自由。至于唐黎小女孩,被认定为无行为能力者;其必须要接受官方及群众的保护,但因其身世背景又不恰当享有过多的物质财富,所以,适合在一段时间的隔断保护后送进环境好一些的孤儿院或者公共教育机构培养。审案完毕的小姑娘在离开大法堂不足几百米的距离,就车毁人亡了!好在马车夫是一个老手,在车毁的前几秒纵身跳进了沟渠里,才算捡回了一条命。夜静悄悄的,马车夫在夜晚悄悄的潜回了车祸现场,他不停的在寻找,并且还隐隐的伴着小小声的自责的哭泣声。他小小声的在説:”这不正常呀,这怎么可能会发生的呢?如果是有人要杀我,那怎么不早一点动手呢?如果是要杀你,看你都还是一个小女童,这样的杀法,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得出来的呀。你知道吗?我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车夫,我可是我门派内跟全部的师兄弟比武的优胜者,赶了这么多年的马车,还真没发现有超过我的。除非这车里坐的是我师傅,要杀我师傅,人家才会有这样的手法呀。可你还只是一个小姑娘。“找了二三个小时,马车夫终于找到了小姑娘的身影;然后在已经警觉到事态严重后,他卷起衣服悄悄的将小姑娘藏在衣服内,家也是不敢回、怕不安全;而是直接等到了天明,经过层层的关卡,才终于将小姑娘秘密的送到了他找的最安全之处。马车夫直接在外面给自己易妆改面,也不改再自称自己是车夫,也是不敢再赶车了。他奇怪呀,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呢?从今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极度谨慎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