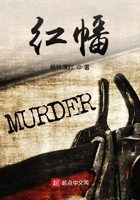栾肃彻底的陷入了沉默,或者说一种接近凝固的状态。他身形不动,甚至连呼吸声都变得非常的悠长、轻微。
在花散问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他自己的答案。只是这个答案却并不会是他想要的,也不会是他所想到过的,所期盼的,甚至不是他想承认的。
虽然栾肃从来都没有把自己在圣堂中的升迁调度与提升和自己本身所拥有的那些天然的资源割裂开来,他也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地位,权势自然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出身,家世,以及自己本身所代表的可能的未来,自己的名字所具有的潜力。
但这也只是一部分而已,他也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自己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不仅仅是依靠着自己的背景,还有自己本身的能力也应该是得到了认同的。这样念头也不是最近才出现在他的头脑中的,或许在栾肃刚刚进入圣堂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原本,他走的路就和其他的那些天幕贵族子弟不同,他在圣堂的路更加艰苦一些,但却也能比那些通过极乐城的名额进入到其中的大家族子弟走到更高、更上层的位置,甚至隐隐之中有进入到圣堂核心圈子的可能。
“真是太迟钝了,有人还以为当初,在你再一次进入的圣堂的时候,你就已经明白了呢。再不济,到了你来到他的身边,你总该明白,这根本就不是因为你这个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也不是你有什么超越了同类人的价值,只是你正好牵扯到了一件旧事而已。到了此时你总该明白了吧,你能走到现在,一半是因为安抚,而另一半则是补偿,你却把这份安抚当作了自己的身价,把这补偿当作了你应得的奖赏。你到也未必什么都没有,能安居在自己的位置上,多少也算是有些自己的本事,但这些东西并不足以支撑你走到这里,你应该看得出来。”花散仿佛越说越有劲,整个人却是越来越放松,连言语中都透出一种惬意的意味,“既然你接受了别人的邀约,站在这里,那么无论你出于怎样的目的,你都已经失去了你在圣堂可以立足的根本了。既然没有人和你提过这些事,那么就让我来为你说个明白吧。”
花散忽然停了下来,她的脖子稍稍地向下沉了沉,似乎在那精致的面具下,花散正在观察着周围的动向,观察着栾肃的表情,等待着他的回答。
不过,栾肃只是一脸的阴郁,什么其他的反应也没有,虽然他肯定是切切实实的听到了花散的话,但是他的表情模样却好像他还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一般,即使身体上已经接受到了这样的信息,他的头脑与精神却在一时间无法反应过来。
花散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坐姿,似乎已经完全瘫在了她的座位上。栾肃也许在面具之下,也是一脸诡计得逞的窃喜之色吧。不知道是故意还是巧合,她越是摆出这样满不在乎的姿势,就越是让周围的听众感到揪心。这明明是一个无比沉重的话题,但在花散的言辞与肢体言语之下,却仿佛变成了一个笑话,但这个笑话的唯一受众却只是花散自己,她是真心实意的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笑话的,而且这个笑话好像还真的成了她用来寻开心的最佳途径。
这显然不是一个笑话,对于听者或者是当事人来说,这整件事或许是误解,或许是失败,或许是宽容,但无论是什么,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都是带着些许沉重的抉择。但对于花散来说,这件事在很久以前或许就已经是一个她料想中的笑话了。而在这个笑话得以证实的今天,她也完全没有一点儿想法要遮掩自己的欢乐。
“曾经,在你的身上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在当时即时的追捕你;或者放任你回归到属于你的世界,只需要一点小小的手段,就足够让你形如放逐;或许在你回到圣堂之后,折磨你,让你知难而退,或者调度你到送命之处。这些都是在计划之中的方法,有一些和善,有一些强硬,但说到底都不需要费上多大的力气,而且完全处于。可偏偏有些人——”花散的脖子似乎刻意的扭了扭,朝向了迦的方向,“——好听的说,叫充满善意,难听些,就是天真。以为用安抚和补偿就可以平复延绵的仇恨和积蓄的怒火。很可惜,当年不过是一句荒谬的预言,如今倒诚真了。”
“我的队伍,到底是被用来做什么了呢?我们什么也没有做,连求得一条活路都成了错误的选择吗?”栾肃的手已经抖了起来,他的眼中闪烁着不可言喻的光芒,一种闪烁的痛苦,仿佛和他断断续续,一字一字蹦出来的言语调和在一起,好像是在演绎着一段旋律,时而凸显,时而隐没。但这一字一字的回响之音却绝不只是单纯断断续续的震动,反而像是一柄反射着光芒的尖锐刀刃,一刀接着一刀扎在栾肃自己的心口。
“既然我说过要说个明白,那就告诉你也无妨。”花散摆出了一副十分大度的模样,“或许你还是没有弄明白,你还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你和你在的队伍又有什么重要的,你们能活下去,或者全部死去,都无所谓,也根本就不可能影响到这个计划——”但是花散的话还没说完,才刚刚开了个头,却被另一个旁边的声音打断了。
“算了吧,就算他能从你嘴里了解到这些,又能怎么样呢?”迦忽然开口了,他的声音非常的低沉,闷闷地,但在这种低落之下却萦绕着无法忽视的悲怯,甚至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的,“他的过去已经不能改变了,又何必要搬出来这些已经发霉的事情影响他的现在呢?”
这一次,花散不再只是扭动自己的脖子了,她整个人都转了过来,面向了迦。即使言语的对象是毫无疑问与她站在同一立场的人,她的“被辩护者”,花散的语气依然没什么好的,依然是非常的毒辣:“这件事可由不得你做决定,就算你能做决定,也只会像你现在所说的话,和你当年所做的决定那样,只能是错误的。况且,这个人的现在,未来,可不是因为他现在了解还是不了解这件事情而决定的,在他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我可是很善意的教导一下他而已,也省得他再为这件事情心力交瘁了。”花散的话似乎对迦来说很有力度,她也没有说什么太重的言语,却让迦十分自主的闭上了嘴,再没有多说一句。
迦说话的确是出于他的善意,即使现在开口说什么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以他的立场来说,也最好是什么也别说,但他还是开口了。他已经完全搞明白了这些事情的联系,也大概明白了当年计划的来龙去脉。虽然并非是他一手操控的,但毕竟他也深度参与到其中,只需要打通几个关节,自然就能明白了。他知道,花散接下来所说的这些,无论落到其他人的耳朵里会有怎样的理解,至少对于栾肃来说是一颗炸弹,而且是填满了剧毒的炸弹。一旦沾染上,恐怕栾肃还很长的时间里都未必能够从这个事实中走出来了。
但迦也很清楚的知道,他的话或许真的也只能是说说而已。他是不可能说服花散的,他既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资格。这个事情对于栾肃来说,是栾肃这些年来唯一追寻的事,对迦自己来说,也算得上是在圣堂经历中的一件大事,但对于花散来说,这或许真的只是一个笑话。曾经,在迦作了决定,留下栾肃的性命,把他放到自己的身边,还作为补偿为他大开方便之门的时候,花散就拿这件事当作一个笑话来评论。只是,当时还是当作笑话,如今却是成真了。
而花散,原本就没有任何的负担,相反她还乐得见到这个笑话成为事实,也算是事实遂了她的心愿。花散抖了抖肩膀,把头转向了一旁,说道:“这是一场大戏,可不会把所有的剧幕都压在你们这些小配角的身上,你们充其量不过是走过舞台的小角色,用来和道具互动一下罢了。你们原本就是用来蒙骗那些异教徒的弃子,你们想活也好,想死也罢,最后还是都得死的,因为你们只是用来激起那些异教徒愤怒的导火索而已,这把火迟早是会烧起来的。这下,你总算是可以明白你们的用处了吧?只是这其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原本,你们从异教徒手上逃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你们到了天幕的地界,属于圣堂的领地也没什么。但偏偏你们之中逃走一个人,这会导致什么呢,你明白吗?”
栾肃愣了,他的表情凝固在显然的惊诧上,不过他也并不是真的蠢笨,这样的推断他只凭直觉也能得到:“如果我把这支队伍的情况说出去,会让人听到风声,会暴露这一切。而且,这原本就是一个不好听的计划,即使在这之后,也会影响圣堂的声誉。可这两件事,无论是破坏计划,还是辱没圣堂,我都不曾想,也不会去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