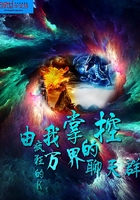刚刚说话的人是栾肃,他的动作原本并不在计划中,甚至都不在这偌大的厅堂中任何人的预料当中。即使栾肃自己,或许也不会觉得自己会这样做。这是众多巧合与机缘在这种奇妙的搭配下才导向了这样的结果。
如果凌忆没有回忆起这件事,如果喀诺没有用那样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如果凌忆没有那样回答,如果……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一个部分不是样方才那样呈现出来,或许以栾肃的心性与性格,他都不会开口,也不会有任何的表示。但是,一切偏偏就像是被设计好了一般,每一个问题,每一句回答,都仿佛像是一根一根的刺,刺破了栾肃的心防,刺破了他的耐心,终于让他感到了一种疼痛,一种或许算得上是久违的疼痛。栾肃甚至都不想掩饰这种疼痛,他紧紧地皱着眉头,但脸上的表情却并不像是痛苦,反而像是爽快。
栾肃并没有在忍耐什么,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把自己的思维朝着这件事上靠。原本,喀诺要拿什么事情发挥,要从凌忆甚至是自己身上问些什么,对栾肃来说,都并不是什么太值得他去在意的事情。他不会说谎,但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事之后,他也不会再隐瞒什么了。但偏偏,随着喀诺与凌忆的对话进行下去,栾肃似乎在某个时刻,忽然醒悟了过来她们在说的事件究竟是什么。
严格来说,这个事件问他的效果要比问喀诺有用百倍千倍,只是,没有人知道栾肃也知晓这个事件的情况,所以自然也不会有人来问他什么。栾肃甚至不仅仅是这个事件的知晓者而已,他还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参与者,还有……幸运者。
有关这个事件的一切都早就被栾肃所掩埋了,无论是出于他主观的念想,还是出于某些客观方法的影响,这个事件到底是被深埋在了他的记忆与意识的底层。而在这个记忆上的镣铐,也有着极为复杂的组成,情绪、思维共同作用,不仅仅是单纯的一种压制而已,而是一种特殊的包裹。对于栾肃自己来说,他也并不是很愿意回忆起这件事。至少按照他往常的理解,应该是这样才对。
但现在,栾肃却突然感觉到自己很兴奋,他甚至都没办法用身体来控制这种突然在意识中泛滥的触感。这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在迦的治下。圣堂虽然庞大,也有着严密的结构,但是圣堂高效的运作实际上也并非是以圣堂整体为单位来计算的,这种高效的建立基本是落在不同的团组上的。而每一个团组,自然是以这个团组的团长,领导者的风格为主,因此,栾肃与他的那些同在一个团组的圣堂战士们一样,都接受着迦的引导与教诲,自然他们也多少会学习到一些迦的独家秘术,去尝试用意志与头脑来控制自己的身体。自然,他们当中谁也不可能做到迦那样的程度,但相比于自己的同僚,栾肃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也一直都在尽量的保持着这种修炼。
但今天,在这一刻,这种用来调控身体的机制似乎完全瘫痪了。栾肃无比的兴奋,他的身体并没有在表面上有任何的反应,除了面部有些抽动,眉头有些扭曲之外,他的身体似乎仍然像之前一般。但是在暗处,栾肃的身体却已经越过了他的掌控,他用四指包裹着自己的拇指,但是这拇指无法抑制的在抖动,几乎要连带着让他的整个手都抖动起来。他感觉自己正在发热,突然整个人的体温都急速的飙升,他的人没有因为兴奋而颤抖,但他的血却在颤抖。
曾经,栾肃以为这个事件永远也不会被再次提及。曾经,栾肃也以为对于他来说,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也不可能看见这个事件翻出一点水花。毕竟,这个事件已经被埋到了地下,连坑都被填的满满的,或许还在上面牢牢地盖上了几块石板。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原本的封锁不仅没有任何的松懈,甚至在这上面还被加上了一座大山,变得更加得密不透风,更加地严严实实。
栾肃当然明白,秘密是不能被永远保存的。但对于栾肃来说,这句话有也是有着一个前提的,这些话是针对那些有意义的事情的,事情有了意义,那才能够被叫作秘密。而失去了意义的秘密,秘密本身的属性也会伴随着这样的情况而褪色,自然是可以被永远的被保存下去的。因为,不再有人会在意,不再会有人追问,不再会有人想要听闻,也不会对现实与现在的世界产生什么影响的事情,连这个事件存在本身的意义都已经被否定了,更何况曾经穿着的外皮呢。
“听上去,我们的另一位证人有话要说了。作为斥讼人,我愿意暂时打断自己,让证人来尽量的陈述,当然,是在保证审判原则的前提下。这样,应该不会违反流程吧,仲裁官大人?”喀诺把头朝向了云尚,问道。
“当然不违反流程,斥讼人。其实你不用如此拘谨的,在斥讼陈述的环节,你可以自由的决定现在究竟是由谁来发言,或者提出什么问题,还有什么时候结束提问与回答。”云尚抬起手,做了一个“请”的动作,“你并不用事事都向审判庭请示或者汇报的,这样我能轻松些,你也能放松一点。”
“感谢您,仲裁官大人。只是,我还是尽量表现的谨慎些好,这些也不至于会有什么问题。”喀诺看了看云尚,然后把自己的头转向了栾肃,她眼珠一转,继续说道,“那么,栾肃,作为证人,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栾肃并没能够看明白喀诺和云尚之间的对话到底是因为什么,又意味着什么。不过,他也并不觉得自己需要明白,现在他的头脑也全都被自己的情绪和过往的事件填满了,完全没有装下任何其他东西的可能,这也让栾肃遗漏了一些细节。他的想象并没有错,但这个事件却又被翻了出来,这样的情况有且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要挖掘出这个秘密的力量,要远比当初封锁这个秘密的力量要强的多,也更加的蛮横霸道。栾肃的确没有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甚至是在很久之后才明白了过来。但是,即使是之后的他,也不能下定结论,就算此时此刻他清楚地明白这其中的门道,摸透了这深水,他究竟是会沉默不语,还是依然会开口。很多事情,原就是一时的情绪所左右的,到底是没办法在当下情境之后再去分析,得出所谓正确的结论的。更何况,时间原本就是无法用后悔来挽回的。
栾肃一直都觉得,自己是永远也没有机会在任何时候在把这件事情翻出来了,甚至这个念头都已经算得上是根深蒂固,完全占据着他的头脑。客观上,这个事件的确不太应该会被翻出来,而他在自己主观的意识上,也尽量在规避着这件事情。而这么多年以来,他也的确没有在任何场合、任何人身上再听到任何东西,会触碰到他的这根心弦。
没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竟然有了一个机会,让他可以亲手把这件事重新挖掘出来。虽然是旧事重提,但再次提出来,却好像是让栾肃重新经历了一遍一般。他兴奋得仿佛全身的鲜血都在沸腾,都能冒泡,但这段回忆,却仿佛是掠过他身体的带霜寒风,是紧贴在他肌肤上的冰片,是渗透到了骨髓的刺骨寒意。在这样一冷一热的夹击下,他的身体在感官上已经彻底的扭曲了,但即使在感觉上崩坏,他却越来越清醒,越来越能够明白的回忆起有关这件事,他所知道的细节。
“圣堂派出的,根本就不是什么边缘的队伍。那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从组成上来说,那是一支圣堂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那之后也不曾再出现过的队伍。”栾肃终于开始了他的说法,“即使单从这一点来讲,也应该写得清楚才对。”
喀诺皱着眉头,不过不是因为为难,而是因为她在非常仔细地听着栾肃所说的话,甚至仔细到琢磨每一个字的程度,在栾肃说完这句话之后,她甚至是回味了片刻,才问道:“那么,这个队伍究竟是怎么组成的呢?单从这一点又是什么意思呢,你是想说这个事件还有其他捏造的地方么?这可是一项很严重的指控啊,你可要想清楚,说明白。”
喀诺也并非是在威胁什么,她也搞不明白栾肃半路跳出来是怎样的意图,但只求不要出什么乱子就好。所以,这话听上去不太好听,却也要提个醒才行。
姑且不说合理还是不合理,圣堂议员们在事实上的确有权力来决定如何书写他们亲历的事件与任务,但这显然不代表他们能够随意的捏造,或者编纂事实。
隐瞒一部分的秘密和说谎是两种在性质上截然不同的行为,前者虽然也有可能造成误导或者理解上的偏移,却不会像后者那样被认为带有显著的恶意。虽然这也是巧合,但在喀诺之前的几番话之后,栾肃现在的话却实实在在的在进行着一种严肃的指控。
到了现在,谁也不会认为这是单单针对于迦的,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上的事情了,是对于圣堂议员们来说的。这是严重的控诉,其中的严重性甚至比听者,甚至比栾肃这个提出者想象中的都要严重的多。喀诺希望,这是一个能够站住脚的控诉。
“那么,就让我慢慢的来说吧。当时,这一支队伍,是由一批年轻人组成的,作为圣堂的新人,他们接受了来自圣堂总部的任务,这也是这个队伍的第一次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