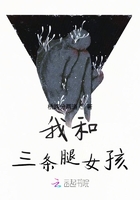殿外。
草木清雅。
霞光莹润。
莺鸣雀和,百叫无绝,一如既往一派祥和。
殿内。
跪着的两人有些萎靡。
香炉内燃着的乳香快烬了,玄清尊适才想起二人来,缓缓从几案前起身,随手将那卷书册放在博古架上,语气不轻不重道:“天兕还似这般不长记性。”
顿了顿,“想是磨练的少了,这样罢,方才普贤真人传了人求助于本尊,同为仙僚,本尊不好推拒,便允了,你去西镜瀛洲却是正好。”
天兕愣忡,旋即领命,似乎早便知道会是如此,没成想这个‘如此’却是自己。执了个礼,躬身快速退到殿外。
银笙忙正了正跪姿,恭恭敬敬等着玄清尊的下文,然,就没有然后了……
她眼看着玄清尊重新拿了卷书册,重新回到几案前,复又重新坐下,再执起酒盏泯了一口,整个过程行云流水,风姿卓然,却是全然没理会自己。
银笙不明,适时仰着头,挺起小身子,学着天兕的样子行了个礼,开口说道:“帝尊,天兕仙君去西镜瀛洲,那,我去哪儿?”
玄清尊眉眼一挑,状似不经意回答,“你退下罢。”
银笙:“……”
自己在这是碍他眼了么,想罢,磨磨蹭蹭的从地上爬起,又磨磨蹭蹭的拍了拍膝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再磨蹭着转身,一步三回头的揪着小手挪到殿门边,然后整张脸纠结在一起,目光一瞬不瞬的盯着玄清尊。
玄清尊似有所感,放下手里的册子,对着银笙不咸不淡的问道:“还有事?”
银笙摇头,幽幽转到殿外,飘回了青渊阁,旁的小茅屋。
躺在竹榻上,有些百无聊赖,银笙抱着被子翻过来再滚过去,玩得不亦乐乎,那副靥足的表情让躲在茅屋左侧下方的天兕看得牙直痒痒,当即想要出手戏弄银笙一番,却又觉得不能便宜了这小妮子,倏的收回手,嘿嘿一笑,神情动作都万般猥琐。
银笙自顾怡然自乐,突的瞧见帝尊尊躯,霎时被震得僵在榻上,样子十分狼狈,且,滑稽。
天兕心里憋着笑,面上学着玄清尊的样子故作目空一切状,冷着嗓子道:“银笙,你这胆子向谁借的?敢躲在这里偷闲,玩忽职守。本尊让你退下却不是让你无所事事,一个小小的九等宫娥见到本尊也不知行礼,派头倒是比本尊大了许多。”
话到此处又稍作停顿,一脸的高深莫测,把银笙唬得一愣,后知后觉间慌不择路的从榻上滚了下来,跪在‘玄清尊’脚前。
正欲出口的话,突的,银笙察觉不对,又险险咬住舌头,刹时心绪万千。
不对,不对,帝尊身上的味道不对,说话的语调也不对,此时出现在这里更不对,这一番细细思索,哪哪都透着违和感,银笙即料定眼前的帝尊定是他人假扮,这般遮遮掩掩准不是好事。
银笙抬头,眼神紧紧锁住对方,扯着脖子理直气壮的高声呼道:“帝尊,您是吩咐了的。”
这下换天兕不淡然了,嘴角直抽抽,剧情好像有些偏了,话本里不是应该有“银笙慌不择路跪到自己脚边,鬼哭狼嚎求自己原谅,然后忏悔自己的不该,最后求自己饶恕她的罪过么?”
再或者,“碎步莲花,身娇体弱,翦瞳含泪,柔声细语的把所有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再道句与旁人无关,模样无辜,泫然欲泣”等等一系列的事吗?这慌不择路是有了,跪也是跪了,可鬼哭狼嚎呢?泫然欲泣呢?她这一问,自己还怎么接下去,天知道帝尊吩咐她什么。
这理直气壮的语气,弄得天兕都开始怀疑那些话本的真实性了,当初向日及神君借来看,他还宝贝得不行。
“帝尊,您刚才一打扰,那抱着被子滚的任务我是进行不下去了,这罪过谁担着?”语气满含嫌弃,怨怒,此刻天兕确认话本骗人无疑,里面没有如此厚颜大胆的宫娥。
重重吸了口气,天兕觉得再装下去受伤的会是自己,有些挫败的恢复原型,嗡声嗡气道,“你怎的这般惹人嫌。”
银笙嗤笑,“我道是谁,原来是咱们可爱的小~天~兕~啊,你这趣味当真别致!”
“住嘴,住嘴,谁是‘小天兕’那掉价的名儿,哼,我是天兕仙君,你就说你,就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是假的。”
“你破绽百出,姑娘我目光如炬,趴地上那会儿就知道了。”银笙有些得意道。
天兕气急,“本仙君我又不是易容,法术幻化的你从哪里看出破绽了。”
银笙挑眉,徐徐道来,“第一,你身上的气味不对,帝尊因着香炉内常年燃乳香,身上自然而然有股子乳香的空灵。”
天兕:“……”
不理会天兕那副错愕的表情,银笙就着天兕凑近鼻子闻了闻,蹙眉,继续道,“你身上气味太过浓烈,恕姑娘我实在闻不细致。”
“第二,你说话的语调不对,帝尊说话时气息很平淡,语调没有波澜,而你说话时情绪起伏太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以帝尊的仙姿怎么可能来我这随时面临倒塌命运的茅屋。你说你是不是破绽百出。”
天兕:“……”
他有些后悔不该问的,她每每列举一点都要抬高帝尊再贬低下自己,这种强烈,毫无悬念的对比,如利箭直戳戳的扎在人心上。
天兕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眼含怨念的看着银笙,你才气味浓烈,你说话就一大破嗓门,你姿态猥琐,怎么办,好想喝酒。
银笙没理会天兕的怨念,到有些好奇,天兕不是去西镜瀛洲了吗?这会怎的有闲心来捉弄自己,便问了天兕由头,天兕似是怨念够了,哼哼唧唧道:“当然是来看看你还活着否,死了我好给丢出虚庭峰,免得占地界。”
银笙诧异,“这话何解?”
天兕神神秘秘,把头压得极低,语气沉沉道:“不告诉你,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银笙额角青筋突起,眼瞳幽暗,正欲发火,又听得天兕说,“不过,日及神君快回来了,应当明日就到,这几日你可去他那避避难。唔,估计五日过后你就可以回小茅屋了……吧!”
这一番话说得银笙更迷糊了,什么灾难什么避难的,没头没尾,揪得人心忒没底了,自己怎么地就有难了,这才幻形没两天吧,事儿就一堆堆的。
天兕这般没得是故意连累自己同他一块儿受罪,就这么见不得自己比他好过么……这人怎么这么欠呢?
银笙觉得天兕危言耸听,有谁敢在虚庭峰造次么?不要命了?再说,自己修为虽低却也是能自保的,慌哪门子的闲心,想通了,便不予理会。
天兕仍自顾说着,银笙心里却惦记着巳时那会儿跑掉的那名男子,在殿内因着帝尊的缘故没敢问,之后又以为天兕已经去西镜瀛洲,没机会问,就把这事给忘了。
银笙琢磨着,虚庭峰的概况自己已经了解大半,可是对虚庭峰以外的事却全然不知,就好比那名男子,竟才是目前为止自己遇到的第三个人。
在水云间那会尚且不论,如今化了形,无论如何不能活得那般狭隘。自己受了帝尊眉心血的福泽,没历劫便修得仙身。
天道酬勤,自古就没有平白能得的好事,这劫迟早会来,躲不了,也躲不得。不若在九幽之境放肆恣意,洒性个痛快,也比过拘泥于一角变得鼠目寸光的好。
想罢,不待天兕继续说话,银笙循循善诱:“天兕仙君,巳时离开的那男子,是谁啊?他看到我们俩个似乎有些惊恐,礼行到一半就跑了,真是怪哉!”
天兕闻言翻着眼睑:“不是看到我俩,是看到你惊恐才对。”
银笙:“……”怎么就扯到我身上了?
想是看出银笙的疑惑,天兕慢悠悠说到:“帝尊十丈之内从未有过女子,越进十丈的,都自请削去仙籍,堕入凡间。”
银笙呼吸一窒,曾离帝尊不过两尺之距的自己。
看到银笙睁大的眸子,天兕表示甚为满意,接着说:“虚庭峰至始至终只有四人,如今,五人,且其中一人还是女人。”
银笙张大了嘴,天兕面上沁出点点笑意,继续,“而那男子是白鹤峰普贤真君门下,排不上号却也能叫出名字之人,他下摆的三连海棠,可看出其品阶居中等。”
天兕说到这,似有不屑,冷哼道:“普贤真君有求于帝尊,却只派个品阶一般的人来,君帝都不似他这般作派,太不把帝尊放在眼里于他未必是好事。”
银笙哑然,似是懂了,那男子虽惊恐自己一女子在虚庭峰安然无恙,更多的是出于对他自己的担忧。
“可是帝尊并未生气,还应允了那男子的请求,怎么就不算好事?”
天兕指着自己,“帝尊是借此事作为惩罚。”语气尽显对普贤真君的不满。
而被天兕幽怨目光刮着的银笙:“……”
讪笑着捏了捏耳垂:“小天兕,你看啊,如今我也算是这虚庭峰的人了,出去以后端的是咱们虚庭峰的脸面,仰仗的是帝尊的身份,可是我对九幽之境的概况知之甚少,你能否与我说说,免得糊里糊涂的得罪了人。”
嘴里边说着,手上动作不停,殷勤备至的为天兕倒了杯茶,示意其继续。
天兕觉得这小妮子的问题有点多,想着这些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自己寻个时机也是要知会她的,现下她问起却是正好。
执起那杯茶喝了一口,微微皱眉,冷的?是这小妮子故意为之,还是其它?可看她一副傻乐的样子,分明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说起来,自己还不知她的来历,但观她修为与自己不相上下,居然会甘心做个侍女,心中多少有些疑虑。
帝尊做事一向只凭心意,这女子出现的莫名,至少在自己眼里是这样。
觉得自己想得太多,天兕闭了闭眼,忽略那杯凉茶,重重呼出一口气,微笑道:“九幽乃仙家所在,是修习仙法的人或妖,心中最向往之地,可修成仙身何其困难,大多都在历劫时功亏一篑,甚至,万劫不复。”
银笙不知道天兕已在心里把她来回想了个遍,只听了这话,似有感慨:“欲成仙,却不能断其念。”
天兕点头,为银笙此番难得的境界。
“九幽之境虽大,可天地之广何止于此,凡人修仙,妖也修仙,都是被欲望驱使,他们认为九幽是强者的巅峰,踏入了便有无尽的权利与荣华,却不知九幽之上还有七峰,那才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及的。”
天兕嗤笑一声,继续道:“在九幽,籍籍无名的散仙何其多,那些人九死一生历经劫难,修得仙身,除了活得久些,却并无用处,尽管如此,却还是有无数人趋之若鹜。”
银笙适时接话:“想是活得久些,对权利的把控才能更久,舍不得站在巅峰的感觉罢了。”
天兕不置可否:“那些与你无甚干系,不过是让你心中有个大概,你只需记住,弥罗峰的最高掌权者君帝,上掌三十六天,下握七十二地,才是这天地的主宰。”
银笙暗自记下,复又正色道:“那其他几峰如何?”
“离恨峰的元阳上帝,坐下只一名弟子,名唤玄都元君,掌着大小行宫百余,且听说治下有方,凡属离恨峰者皆须着淡蓝衣饰,其上刺金菊,按数量论品阶。”
“不错!可防不臣之心的人,想法也很独特。”银笙咂舌。
“是不错,其他峰也效仿这般,崇恩圣帝的云霄峰以金月丹为记,道行天尊的玉屋峰是一支金梅,扶乐神姬的长佑山则是牡丹,白鹤峰你已知晓。这些峰虽说标记不同,但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就像每个峰的标记,都是有其特殊的秘法,旁人是无法仿效的。”
银笙有些惊讶:“扶乐神姬怎的还单独一座山,可即便如此,难道不也应该是峰么?”
天兕好笑:“这有什么可奇怪的,众仙皆知,君帝向来偏爱这个九女儿,便把长佑山改名长佑峰赐给了扶乐神姬,也才会有如今的七峰之说。”
银笙大略了解了,想来也是,若非君帝偏爱,又怎劳得动帝尊出手,让自己养了她万年,想到这,不知怎的,银笙心里就堵的慌,有种自己的东西被觊觎的感觉。
大抵是有些上火,银笙端起茶喝了一口,发现茶水透凉,才注意到这大半天的,天兕面前的茶丝毫未动,面上有些讪讪,“天兕仙君渴了吧?我这就重新砌一壶茶来。”
嘴里说着,忙起身,端着茶壶便要去烧水,却听得天兕打趣道:“不用,多麻烦您啊!”
银笙尴尬的将身子僵在半空,“不麻烦,不麻烦,您坐好就是!”
天兕起身,将手背在身后,故作高深道:“时辰不早了,再不去西镜瀛洲,这惩罚怕是得加重了,茶,就不喝了,可话,你听进去没有,本仙君,也不感兴趣。”
银笙一脸赔笑:“仙君说的话那般在理,小仙自是都听进去了的。”
天兕闻言,不禁有些欣慰,像个授业的老先生笑得脸上堆满菊花,他深深觉得自己果然是个大好人,是这虚庭峰仅存的善良人,草草说了句,“好生保重!”便向着西镜瀛洲的方向飞去。
天兕一走,小茅屋就恢复了安静,显得银笙一人有些孤寂,偏银笙性子喜闹,待在水云间万年也没修得个娟好静秀,许是那会儿听天兕叨念惯了,这会子静下来倒有些不习惯。
四周草木沙沙作响,鸟儿的啼叫声显得过分突兀,阳光斜斜的刺过来,让那颗歪脖子树投下稀稀疏疏斑驳的光晕,落到银笙脸上,有些忽明忽暗。
银笙略一思索,揪着耳垂漫不经心扯了几下,再重重点头,决定了,去竹蘭殿找帝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