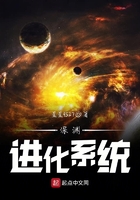钱是个好东西,这我知道。有了它老人家那真是如鱼得水,潇洒方便。比如说要赶着办件什么事,就不必骑一辆叮哐乱响的旧单车,没头没脸地在南国骄阳下暴晒;或是奋不顾身挤上某路公共汽车,沙丁鱼似地人挨人站着直冒臭汗。我只要穿一身时装袅袅婷婷步出家门,玉手一招便坐上空调“的士”绝尘而去,或者干脆买一辆“奔驰”呀、“宝马”呀什么的,管它晨昏日夜,雨暴风狂,都随时可以成行。又比如说有朋自远方来,聊得兴起自然不想系条围裙洗菜切肉忙得昏天黑地,于是只管择一僻静咖啡厅,柠檬茶加糖,酸酸甜甜地细聊慢喝直到夕阳西下。然后携友去品尝正宗粤菜、生猛海鲜,席间还喝上两杯陈年好酒。吃饱喝足了如果还有兴致,就悉听客便,唱卡拉OK、跳交谊舞、逛夜市,听音乐会都行。当然,要是不提这些凡人俗事也没问题,诗琴书画、高雅精神享受也不能完全脱离钱这个东西。要出本书要拍电视剧有了雄厚的资金还不是小菜一碟!根本不用理会那劳什子书号费,印刷费,自然也无须四处龟孙子似地伸手求援,资金到手才能立马拉摄制队伍开拍……
闲来无事或为钱所围时,我会傻乎乎地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做发财梦。诸如买回几千元股票,数月间行情看涨抛出去便有了十几万元;偶尔经过投注站,买了两张彩票一夜之间竟发现中了头彩,顿时号称百万元户;或是下海做生意一年半载就大发了起来,又是小车又是别墅,银行存折也一跃上了六位数,从此爬上岸来潜心创作……“梦”醒之后爬起来一切照旧,但也会很开心地独自笑出声来好像真已经过了发财瘾。再看看眼前有吃有穿可以买化妆品可以健身美容,偶然还能自掏腰包上小餐馆吃一顿,不跟大款比囊中还不算太羞涩,也就怡然自得不做非分之想。况且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贸然去做生意,大赚无门,小赚偷笑,血本无归都得认了,还不如不冒这个风险。加之有业余“半仙”者看过手相,说我衣食不愁,暴富难求,既然如此,我就更不想为了下海赚钱去绞尽脑汁,伤神费力了。于是摊开一桌子的稿纸,买一堆闲书,乐此不疲地爬格子,读文章。
每每得了几笔小稿费,我虽做出不骄不躁的样子,心里却还是颠儿颠儿地乐。可见钱的诱惑始终有的,只是不至于大到让我不自量力,弃文经商罢了。但如果有什么小生意或“炒更”的行当顺手便可以完成,我还是很想做一做赚点小钱的。老友们听了我的想法都嘿嘿直笑,说世上哪有这等又不费力又来钱的好事。我不理他们不屑的目光,振振有词地回答:“怎么啦,即使做不成,想一想说一说都不行吗!”这一招果然灵验,他们坦白地告诉我,有时也会这样傻想。
23.三十里路云和月
不知怎的,一听人说起工作单位在远郊,心里便涌起一股复杂之情。或许,这与我过去有4年多到郊区上班的体会有关吧。
记得调到广州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在黄埔新港。听说有30多公里路程,20大几的人,心里还是忐忑不安。但我怎么也想不到,上班的路途竟是那样的“坎坷”。
第一天上班,起了个大早,6时之前空着肚子摸黑出了门。先生把我送到电车站,嘱咐我在哪儿下车,如何两次转车。这话两天内我至少听过8遍,于是衷心感谢挥手拜拜,上了一辆空空的2路电车。那时没有普通话报站这一说,我压根儿不懂粤语,售票员小姐又睡眼惺忪,不肯答话。幸亏我一路数着,第三个站立即下车。一看站牌我就傻了,那上面分明写着“烈士陵园”,哪是什么“大东门”呢?究其原因大概是有个站没人上下,车就呼啸而过。我自叹倒霉急忙走回头路。
转入越秀中老远就有车声人声,声声入耳,走近33路车总站一看,哇!(当时非“哇”不可)一条“长龙”见头不见尾。正好开来部空车,“龙头”顷刻间乱了套。人们蜂涌而上,把个车挤得满满当当,好不容易才关上车门。眼看走了几部车,人还源源不断地来。长龙依旧,似乎全广州的人有一半要到黄埔上班。我何曾见过这个阵势?所以越靠近“龙头”,心里越紧张。只是由于那么多人推着拥着,才不由自主地向前。离车门一米左右时最见挤车功夫,两旁的人或迂回门边,或直钻人缝,我初试身手,反被挤得倒退几米。眼巴巴地瞅着通道车沙丁鱼罐头似地塞满了人,喘着气开走了。
这时天大亮了,看看表已是7时差10分。糟了!新港的交通车7时正从黄埔开出,赶不上就得再转两次车。可除了坐直升飞机,我根本无法按时赶到。
正在暗暗着急,旁边有位姑娘问我:“第一次去黄埔吗?”——是广味浓厚的普通话,我喜出望外,连忙点头道:“是的。我调到新港工作,第一天上班。”“我也是新港的,等下你跟着我。上33路车可不能斯文。”
“天天跑?”我轻轻地问,心里有些发慌。
“有什么办法!要不我能这么苗条。”姑娘笑了,她确实“苗条”得可以。
我紧紧跟着这位姑娘,全靠她勇猛灵活,连拉带扯把我弄上了车。两人挤在车尾,好歹有了立脚之地。
“交通车你是赶不到了,我带你去坐专线车,不过还得转一次。今天我要在黄埔办事,没法陪你了。要是平时,我出门更早,就碰不上你了。”她这么一说,我刚松弛的神经又绷紧了。
当我累饿交加、神情疲惫地出现在新港人事科时,已是10点20分。报了到,见过科里的同事,就到了午饭时间,下午4点半下班,又是一次远征。踏进家门时刚好6时30分。
第一天上班,路上来回耗费6个小时,工作4个小时。一算这个账我顿时头皮发麻叫苦不迭。
后来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我在黄埔新港工作了4年半,丢在路上的时间,合起来少说也有半年多。现在想起来,还心疼得很。听当年的同事说,如今路修好了,车也多了,不塞车的时候,两个钟头来回没问题。但如果塞车呢?我想:还是有好多好多人要心疼的。
24.夜幕降下来的时候
滨海小城的黄昏别有韵味。落日的余晖洒下一层柔柔的金光,使新楼旧屋都笼罩在童话般的色彩之中。沿海路更因为有西侧闪烁的粼粼海波,而显得虚幻迷离。素云斜倚在办公室临海的那扇窗前,呆呆地凝视着海天相连的尽头,就像是一座金色的雕像。
刚才下班铃响的一刹那,她下意识地拿起了那个精致的坤包,可她马上醒悟过来,能回哪儿呢?她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胖大姐看见了,走过来细声细气地问:“怎么啦?是不是不舒服?我打个电话叫阿强来接你吧?”素云鼻子一酸,没敢抬头,答非所问地说:“我有点事没做完,你先走吧!”对面桌的小吴是个直肠直肚的二楞子,接过素云的话就说:“咱们快走,别打扰素云。她天天下班都赶着买菜做饭,相夫教子,好不容易才腾出点时间自由活动,内容无可奉告。”小吴向来嘴上没遮没拦,大家也不当回事,一边笑一边鱼贯而出。办公室突然静得一点生气都没有了。
孤独和寂寞一下子压得素云喘不过气来,她无声地任泪水从脸颊滴落,只是迷茫地望着远处的大海……
早上离开家之前,她在桌面上留下了一张纸条:“阿强,我走了。这几年我一直觉得太累,我想你一定也不轻松。心灵的伤口最难愈合,但愿我和你都不要再折磨自己,折磨别人。珊珊让你多费心了,等有了固定的住处,我一定会继续尽母亲的职责。素云”这半年来,每回吵完架素云都想走,可一看见女儿的笑脸,她要走的勇气就消失了。想不到这回促使她离开的,仍然是那一类发生过无数次的事情……
前天是周末,素云早就跟阿强打了招呼,玉芬搬了三房一厅的新居,约一帮老同学聚餐相庆。玉芬是她的初中女友,去她那儿是阿强批准的为数极少的索云可单独行动的地方之一。可这回有一帮老同学,阿强当然不能不警觉。他详细询问玉芬的新居地址,聚会几点钟开始,有哪些人参加,晚餐后有什么活动……未了还是不满意,干脆直问:“那个陆志明去不去呀?”素云早已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只是不便点破,见他终于直说了,便压着火说:“听玉芬讲他出差去深圳了,赶不回来。怎么样,还有什么要问?”
原以为这下阿强该没话说了,没料想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我说呢,早打听好了。我就知道你心里没有我。既然那姓陆的不在,你还去凑什么热闹呀?”
“这是同学聚会。”索云回敬了一句。
“哦,那就是说,你要另外约时间见你的旧情人啦?”
天哪!还有完没完。素云扭头进了卫生间,不再答理阿强。一年到头,她倒有350天当家,上班下班,两点一线,阿强觉得理所当然。可只要素云有一回自由活动,起码十天半月不得安宁。不管她如何事前请示,事后汇报,阿强都没个满意的时候。弄得素云神经兮兮地,出门像是个假释的犯人,时时有阴影相随。唉,一个大男人,总为这些事操心,犯得着吗?素云虽说温顺,也有倔的时候:“周末我去定了。”她从卫生间出来时不轻不重地甩下这么一句话。阿强气得脸铁青,但还不至于动手。为了这,他从来标榜自己疼老婆。
周末下了班,索云便直奔玉芬家。一袭天蓝色的连衣裙使她更显得白皙、清秀,玉芬见了拍手笑道:“越发漂亮了!难怪你们家阿强紧张。”素云一听脸都白了,直说:“你这张嘴别那么利好不,让人听见了怎么办!”玉芬这才停了笑轻声说:“别害怕,就我自己在家,你是第一位客人。”
素云挽起袖子帮玉芬洗碗拿筷摆酒杯,心里却沉甸甸地提不起兴致。不知怎么地她想起了陆志明,上山下乡时他俩在一个生产队,上工下工砍柴煮饭,相处得挺好。有一年中秋节知青点就剩下他俩,素云的父母都在牛棚里无家可归,陆志明却是因为经济窘迫有家难回。那天晚上在队长家吃完饭他俩披着月光回去,素云默默地低头走路,深怕抬头看见明月勾起一腔思乡情。小陆突然冒冒失失地问:“素云,你愿意永远和我在一起吗?”十八岁的素云像受了惊的小兔冲进十几米外的知青点关上门喘大气,小陆在隔壁那间房苦苦求饶:“素云,你不喜欢听,我就再不说了。”从此小陆果然不提此事,素云心里反而空落落地不踏实。几个月后素云的爸爸官复原职她也跟着回了城,在海关财务科工作,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阿强。素云老老实实讲了这段“未遂”的恋爱,想不到竟成了阿强的心病。两年后陆志明招工回城,和几位同学一起登门探防,阿强脸黑得锅灰似的,结果不出十分钟客人们就夺门而去……
这以后阿强就不断地疑神疑鬼。大凡与素云交往多一点的男人,在阿强那里一律上了“黑名单”,不定什么时候拿出来口诛一番。和阿强吵了数不清多少回,有时声泪俱下有时言词恳切有时坦诚相劝有时歇斯底里……可阿强根本不为所动,依旧很坚决地按既定方针办。素云气极了说干脆离婚,阿强倒也爽快,回答是:“离就离,但女儿不能给你。是你提的你自私透顶你不为女儿着想!”女儿是素云的命,不给女儿素云绝不可能离婚。何况素云是个独女,父母已经去世,在这个城市里她连亲戚都没有,能蹦去哪儿!阿强是聪明人,他知道素云的脾性。
素云口里叫得响,真要离她还真有些舍不得阿强。十年了,她习惯了阿强的一切,他的亲吻他的拥抱甚至他身上特有的气味,还有他恼怒时那张青灰色的脸。平心而论,阿强也是个好人,看家看得重,又不打牌喝酒,连烟都不抽。吃穿不讲究每天有壶好茶就满足,在公司里大小是个工程师,技术不错人缘也好。外面的人看上去都夸素云小俩口般配。素云听了不置可否,只有玉芬问她,她才长长地叹气:“都是好人可好人不一定能过到一块儿去。”
素云一边忙一边漫无边际地想,就在这时闹哄哄地进来了几个人,一下子打破了宁静。都四十的人了一个个还像当年下乡知青似的声音大,笑声响,管你如今是经理还是书记,照例你一拳我一掌人人平等。素云也就顾不上别的投入了这个圈子。一帮人吃饱了喝足了就聊大天。几个能歌善唱的在客厅里一首接一首地卡拉OK。素云、玉芬一伙女伴躲进那新娘房一样漂亮的卧室里讲女人的话题。玉芬在人前疯疯颠颠大快活一个,其实素云知道她心里很苦。她先生是做生意的钱大把大把地赚,只是三天两头不在家回来了也冷冷地无话可说。
最近她先生买了这个三房一厅的套间交给玉芬装修、搬迁,自己又去了东北。有人说他在外面弄了个女人,玉芬一问他就大发脾气,屁股一拍拔腿就走说是老子住宾馆去,让你这娘们干吃醋!素云说:“要是我早离了,受这份罪!”可玉芬还傻傻地爱他,反过来劝素云:“你那个阿强也太气人了,对老婆像管劳改犯似的,我可受不了。”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诉完苦还是各自回家,将就着过。
几个女伴的话还没说够,唱歌的告一段落,跑进来死活要她们出去客厅跳交谊舞,说是不会跳的可以跳“忠”字舞代替。众人大笑,一起往外涌。素云看看表十一点了,赶紧说要回家。同学们都说怕什么,难得一聚,又是周末,还不兴玩个痛快!呆会儿饿了,去海边大排档吃完宵夜再回家。素云只好说先生出了差,孩子托隔壁老奶奶看着呢!大伙这才放过她,一出门她跨上单车就拼命踩。
推开家门素云发觉大事不妙。阿强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怒目相视。她避开那两道目光进了房间,心里直说别吵别吵,洗完澡就睡觉让他独自生气去。就在这时候阿强一阵风似地冲将进来,冷不防把她往床上一推,恶狠狠地咆哮:“你敢深更半夜回来,我就要好好检查你!”素云突然楞住了,血直往头上涌,说不出的羞辱充塞了她的心。她挣扎着跳下地直觉得恶心想吐。阿强被她的举动吓了一跳,大约觉得自己太过份,呆呆地站着好一阵终于上了床。那天晚上俩人都没再说一句话,素云却下了离开这个家的决心。
早上离开家之前,素云扫了地抹了桌椅又把洗好的衣服晾出去。她再次环顾着这熟悉的两房一厅,这不算大但却包含了她那么多甜酸苦辣的小窝……锁上门她茫然地向单位走去,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呢……
海和天相连的那一抹红渐渐暗淡了,消失了,沿海路很静,行人不多车也少了。往日这正是围桌开饭的时候,不知道阿强看了她留下的信会不会火冒三丈?女儿珊珊这会儿还不见妈妈回去准在哭了……素云泪眼模糊地收回了视钱。她真想找个人说说,真想倚在谁的肩头哭个痛快。“陆志明,找陆志明。玉芬说他星期天回来。对,他家不是有电话吗?上回在路上相遇,他说让我有事找他的。”素云立即翻开小电话本查了起来:“喔,是这个,223486。”不知怎么搞的,素云拨电话时,手竟有些颤颤地。
“你好,请问找谁呀?”是位女人的声音,柔柔地挺好听。陆志明说过,他夫人是儿科医生。
“我找陆志明。”素云犹犹豫豫地答。
“哦,你稍等。”那女人大约手上还抓着话筒就亲热地叫开了:“志明,你的电话。”
一会儿,话筒里响起了男人的声音:“我是陆志明,请问你是哪位呀?”当了几年供销科长,他的口才可是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