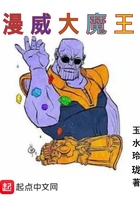六十里路,不算远也不算近,策马狂奔,只需要一天,但带着伤兵,跟着牛车慢悠悠往蒲坂走,就得要三天。
该死的牛车,一点减震都没有,该死的驰道,全是坑,谢云晕车了,这三天,他的五脏六腑都快颠吐了,即便身子底下铺着三张羊皮毯子,他屁股已经磨出水泡,跟火烧一样。
邓景这家伙骑着棕色的骏马,来回奔驰,一会检查队伍,一会前面探路,似有炫耀自己骑术的嫌疑。谢云看着刚刚驰骋而过的家伙,翻了一个白眼,他现在开始怀念起自己的国产越野车了。
“哥哥,我哥!”一个脏兮兮的姑娘一路小跑,麻利地爬上牛车说。
她是百夫长刘阿大妹妹王秭归,自从这丫头片子在自己睡袋睡了一夜,就开始理直气壮的跟自己要吃的,整个车队的人也开始接纳起这兄妹二人。
那是书记大人的人,以后的贵族妇人,反正二狗是这样宣传的。
谢云很想再揍这狗货一次,但他此刻已是自身难保,还有三个时辰就到蒲坂军营了。就地休息时,邓景将自己以前的甲胄取出,两妇人开始给谢云着甲。
很丑的黑甲,牛皮镶嵌着铁甲,虽然很重,但防御力还是有的,至少比起制式的铁甲好的多。谢云晃荡着自己大一圈的头盔,心里明白,自己现在肯定丑到爆。
这身盔甲就三十斤,加上制式的后背刀跟随身的行李,谢云感觉自己上了战场就是沙包,除了吸引力火力外,没有任何用。
邓景还一个劲道歉,说没给兄弟配把好武器,用制式刀,实在有损颜面,等到了蒲坂,一定找军中大将定制一把好刀。狗子跟陈成羡慕的流口水,他们做梦都想有这么一身盔甲。
邓景对两位妇人整理的盔甲很不满意,亲自动手,狠狠重洗束了一遍胸甲。完了,疼,谢云感觉自己断掉的肋骨好像被压移位了,拼命挣扎,脱掉胸甲,问:“行军书记不是文官吗?小弟为什么还要着甲?何况小弟还有伤在身?
“我父帅治军甚严,在军中,不管何人,都要着甲,何况现在正逢大战,你若想挨军棍,那就别穿了。”
“……”谢云无语。他也听过邓景讲挨军棍的事,十四岁,夜探敌营晚归,挨了二十下,硬生生躺了半个月才能下地。
自己兄弟不会害自己的,用薄木板护住胸口,重新束甲,自己已经有伤在身了,若是屁股再受伤挨军棍,那自己出什么仕,还不如回深山。
启程了,陈成让出自己的马给谢云,他的马是母马,比较温顺,至于他,肯定不会走路。小强现在还有伤在身,不能骑乘。
很奇怪,靠近蒲坂城时,离城墙不远的地方突兀的伫立着几个土包,按理说,城墙附近,不是越空旷越好吗?
谢云指着土包好奇的问邓景,得到一个他不想听到的回答,京观,汉家人的京观,都是十几年前建立的。城里的汉人奴隶发生暴动,结果全部被处死,死的人太多了,挖坑都来不起,只能把人拖出城,盖上一层黄土。
“呱呱呱!”车队惊起一群乌鸦,黑压压的鸟群盘旋在土包久久不愿离开。
看出兄弟心情不好,邓景催促车队,加快步伐,离开蒲坂城,前秦军军营在蒲坂城的北方。
大营就在前面,来回进出的军队,探马,信使,络绎不绝,不时有浑厚低沉的号角声从里面响起。
这座军营布置的很有特点,壕沟,据马,箭楼一样不缺,里面的军帐也是以队率为单位部署。帅帐前,一幅硕大的邓字帅旗高高飘扬,显得十分嚣张。
严明身份,陈成带着车队去了后勤营,邓景带着谢云直奔帅帐。
邓羌,前秦的第一名将,据说勇猛程度不下关羽张飞,号称万人敌,北方诸国均破国于他和王猛之手。可惜肥水之战前,他老人家跟王猛去世,不然中国可能真的就由此统一。
最妙的是他老人家深得苻坚信任,不光跟变法的王猛一派关系深厚,跟氏族元老也是生死之交,反正在前秦抱着他老人的大腿,绝对错不了。
谢云还在回忆百科里邓羌的资料,一阵豪气逼人的大笑就由帅帐内穿出,紧接着一个四十岁的大汉就出现门口。身高一米九,全是肌肉虬结,穿着盔甲都能看出,一双豹眼精光四射,直刺谢云双眼:“小子,你有何能,让我的不孝子奉你为神人?”
谢云低头,避过如刀锋般锋利的目光,单膝下拜:“下官谢云,参见征东将军。”
“大帅,从军书记有妙手回春只能,您随下官前往伤兵车队一看便知。”邓景连忙接话,他甚至他老子的脾气,下一步就该试探起谢云的身子底了。
“好,就就听那不孝子的!”邓羌眼睛稍微一眯,一甩大红的披风,直奔后勤营,两人紧随其后。
那些伤兵是幸运的,他们服用现代特效消炎药后,都保住了性命,没一个人因为伤口发炎去世。
现在他们中轻伤的,已经可以下地走路,甚至其中机灵的,已经开始帮忙照顾起重伤员了。
“张神医,听不孝子说您被羯族虏走,我可是担心了好几天。”邓羌隔着老远,就开始跟张玄明热切打招呼。
“弟子见过大帅,见过师尊。”张玄明恭敬行礼。
谢云一脸尴尬,虽然他已经无数次告诉自己徒弟,见面不必行礼,两人以平辈相交,但都被张玄明拒绝了。
嗯,这几天,吃的好,睡得好,有神医照顾,小兵都恢复的不错。
“伤损几何?”
“禀报大帅,伤兵队伤兵残疾者十二,其他正在恢复中,军户二十七人,折损十一人。”陈成出列,抱拳。
“唔?很好!平定姚襄后,本帅必定剿灭羯族余孽。”邓羌拍着手下的肩膀,安慰道。
“谢过大帅!”陈成跪下,眼含热泪,行大礼。
安抚伤兵后,邓羌当场下令,谢云为升为行军司马,立刻在蒲坂大营旁建立伤兵营,主管伤兵救治,张玄明就任行军副司马。
“好,我还以为我那不孝子跟老夫吹嘘,今日一见,当真不凡,我军中又添一俊才,可喜可贺。”
从小子到贤侄,升的真快,不够看着邓景面子上,他这伯伯,捏鼻子认了。
邓羌一手拉着谢云,一手拉着邓景回到帅帐,说:“我观贤侄不是等闲之辈,将来还指望你帮伯伯多指点这不孝子几下,你们兄弟二人,要相互帮扶,共同进益。”
“邓兄对小侄有救命之恩,更是小侄引路之人,我与他早已是莫逆之交。”
“好!”邓羌大喜,一巴掌拍在谢云肩上,疼的谢云直咧嘴。
近卫已经在帐中摆下案几,餐盘上两荤两素,外加一碗羊杂汤,咦,这时候就开始流行起工作餐了吗?
邓景看谢云痴呆的看着菜肴,还以为一路奔波,少年人饿的快,他倒不觉得谢云失礼,只觉得这小子有点胆色,视自己满身杀气若无物,心中好感大增。
“听不孝子说,你小子也精通易牙妙术,尝尝,军中饭菜还合胃口否?”
“长者赐,不敢赐。”谢云端起汤碗,开始跟盘子里的一块牛肉较劲,老邓可不是一股蛮劲的莽夫,他老人家还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在粗犷的外表下,是他文武双全的内心。
酒过三巡,饭过五味,邓羌放下手中筷子,问:“令师何人,我老邓就喜欢拜见高人名士,为难得见,甚憾。”
“师尊自称书山,但从未告诉小子他的名号,他常说,读了半生书,一肚子学问,却没能平定这乱世,无颜面对世人,师尊经常面南怒骂桓温误国,鼠辈,空有平乱世之资本,却纠结名利,也时常感叹,三国乃汉家之光荣,也是汉家之耻。”谢云哀叹,老邓终究还是忍不住提问了。
邓羌端酒沉思,半晌后,才拍案而起大叹,高人,高人,目光如炬,分析简直入骨!
邓羌乃汉氏混血,从军多年,才知道汉家的元气,是在三国消耗殆尽,然后才有后来的五胡内迁,司马家八王之乱后,五胡做大,北方战乱由此开始。
这么浅显的道理,当世读书人,能明白的,不过百人。不过,他为何怒骂威震东晋,权压朝野的大司马为何是鼠辈?
“高人所言,真令人费解,桓温也算一代豪雄,怎是鼠辈?”邓羌喝酒叹息,仍在揣摩。
谢云低头,他当然知道,桓温权势无双,三次北伐,本可击败北方诸国,重塑乾坤,统一诸国,但他却在北伐局势大好情况下,忧心朝廷猜疑,仓促撤退,如此行为,蛇鼠两端,不是鼠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