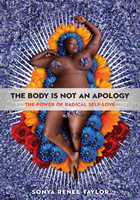“别胡闹。”徐满正抢过了她手中的帕子,顺手倒掉了盆中的脏水。
“哎。”苏省腿脚不便,险险躲过水的来袭,“你眼睛长……”
徐芽儿从徐满正身后冒出了半个头,苏省险而又险咽下了口中会带出市井气的下流话。
“齐夫人,这是伴蓝大夫新作的药方子,您看看。”伴蓝对徐芽儿尊敬有加,苏省自是不敢放肆,他没有走近,在和徐芽儿隔了不少距离的位置上停下,他伸出手,手上覆着一层布,与拿着的药方隔了开来。
伴蓝分身乏术,不好自己来与徐芽儿交涉,便拿了苏省充了数。
徐满正抢先一步将方子拿了,“你怎得管上了这种事,大哥呢?”
“锦绣坊里有堆缎子和茶叶遇上了大雨虫疫,还有今年小满的蚕茧被祸祸了不少,兄长去想办法了,“徐芽儿抽走了他手里的方子,“这是伴蓝大夫好不容易回想起的龙王爷给的方子,你别弄坏了。”
徐满正手里空荡荡,心里空落落,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多年,从没像现在这般手足无措过,几日不见,他是半句没听懂徐芽儿说的话。
徐芽儿拿了方子,去找别的大夫配药了,有小厮上前,不管徐满正有没有在听,不管徐满正知不知道,一股脑儿将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全讲了,在徐芽儿的示意下,他不止讲了虫疫的发病征兆,伴蓝愿以自身献祭的大义,还把前些日子姚大姑娘、叶姑娘和虞姒的事,与王氏死的事都吐了个干净。
知兄莫若妹,徐满正身在越州,魂在天外,人家姜太公钓鱼能晓天下事,他钓鱼那就真是钓个鱼,其他啥事也不做。
徐满正席地坐在角落里,看徐芽儿在忙碌,曾经他是万万不会这么做的,他讲得是魏晋风流人物的倜傥洒脱,衣衫脏了染上了尘埃,怎能显出飘渺遗世独之感。
徐家发生什么不好的事,瞒着家里最小的妹妹的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他把老太太气病过去两回,谢嬷嬷会不会与徐帷讲还难说,对徐芽儿更是不会讲了。
他们不讲,想她做一个无忧无虑的乖女子,徐芽儿就不问,对徐满正形容的巨大变化一如往常,好似她没有远嫁,没有离开越州七年之久,她的哥哥也没有消耗掉少时的灵气,变成一根直楞楞的竹竿。
“你真信吗?”徐满正问分完药汤,坐到他旁边歇息的徐芽儿。
天光将暗,残存的余晖挂在天边,为其世间披上了一层假装太平的薄纱。
药汤分完了,人陆续都走了,徐芽儿得以喘下一口气,她并肩与徐满正坐下,没人关心他们在做什么。
“信与不信重要吗?”徐满正朝着她视线的方向看去,街边有人似是发了病,哆哆嗦嗦地把药丸塞入自己的口中,吃完面色竟是舒展开来了。
不论这药是真有用还是假有用,起码能在这半月里给到一个寄托。
“折宁的仕途这几年算不上顺,”徐芽儿说,“越州不能乱,哪怕是整座城葬于虫疫,越州城也不能乱。”
不能乱…
徐满正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猛地扭头,“半月之内那个女大夫找不出药方来,你就要赔上你自己?”
越州水路四通八达,每年上交给朝廷的税收在富庶的江南东道里算是前头几位,越州因虫疫暴乱是当官的办事不力,齐桡的官途必绝无疑。
而越州因虫疫而亡,连同回娘家省亲的齐夫人一块死在里头,不会有人会对遭遇丧妻之痛的齐大人苛责太多。
齐大人与齐夫人伉俪情深,多年未纳过一妾。
徐满正想拉起她,“你跟我走,离开这儿,先离开……”他四面惶惶张望,想给他的妹妹找一个安身之所。
“哥哥,你确定我没有染上虫疫吗,你确定你没有染上虫疫吗?”徐芽儿没动,任他拉扯。
虫疫发病起初的红疹小小的几粒不疼不痒,没注意便略过去了,越州城里人人自危,没人敢说自己一定没染上。
徐满正停下了步伐。
“等虫疫平定,我将接她回府。”
“你是要毁了我的芽儿!”
“等虫疫平定……”
“我的芽儿……”
两句话像佛寺清晨准时响起的撞钟,在徐满正耳边反复回旋飘荡,他松开了抓着徐芽儿的手,头疼欲裂。
女子该嫁一个喜欢自己的人,还是自己喜欢的人,少年的徐满正和徐芽儿选择了嫁给自己喜欢的人,七年过后,徐芽儿初心不改,徐满正却认识到了老太太的苦心。
他不想他看着长大的妹妹受这种苦,即便他们不是一母同胞。
小满了,虫鸣声为何都不见了?
徐老太太的视线绕过了齐桡,在看杏树上长得鲜嫩欲滴的绿叶,心神恍惚地想。
“芽儿怎能受这种苦?”齐桡站在堂下,对上首的徐老太太说道,他说了好多话,虞姒只听见或只听懂了这一句,先前讲得那些关于越州,关于虫疫的事,虞姒觉得,她还是回头去问桑叶子好了。
虞姒和桑叶子这次没有去听墙角,她们被特允正大光明地跟在老太太的身边听,虞姒站在老太太的身侧,假装安静,桑叶子躲进了后面的抱厦,她不方便出现在人前。
老太太养了两天,气色好转了些,“芽儿给我娇养了多年,养得娇气了,是该去吃吃苦头。”
老太太打开茶盖,升腾起来的缈缈雾气模糊了她的脸,她不可置否的讲道:“道长治湿毒热症确是一把好手,但你要他去治什么虫疫想必是不行的,何况照泠的身体不好,下不了山的,你要道长抛下我们这一屋子的老弱妇孺,抛下他的夫人去治他不擅长的虫疫,要出了什么差错,凭照泠那个身子怕是会同他一起去喽。”
老太太的话带出了似是而非的哭腔,虞姒赶紧上前为老太太顺气,挡住了齐桡的视野。
虞姒笨了不少年岁,难得聪明了一回。
屋外葱茏绿叶下,照泠听着里头传来的话,手指作刃,一支木簪下去,贯穿了在地上蠕动的一只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