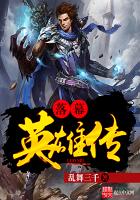眼见那老鳖爬得远了,雀官便道:“老丈,你为何把这老鳖放了?”
老者道:“天生万物,万物皆有灵性,似那寻常毛鳞卵虫,未生灵性之前,只不过是上天赐给人的口中食罢了,吃之无碍,但若是年岁久了,有通灵之意,便与我们一般,吃之便是罪孽了,故此我将它放了。”
雀官点头,道:“在我们庄子里,也是不吃老鳖的,我们那元仙湖,还出过鳖仙呢。”
老者笑道:“鼋与鳖看似一物,实是两物,鼋大而巨,鳖若长到方才那般大,便是罕见了。鼋待到长成时,可翻江倒海,鳖若长出灵性,年岁久了,却会长出一件稀世珍宝。”
雀官问道:“什么宝物?”老者道:“那物唤作鳖宝,长得便如一个一寸来长的小人一般,若自鳖中取出,可将人的手臂剖开一个口子,将那小人按将进去,那小人便钻进肉里去了,伤口自会愈合,只是隆起一块。那人若将这鳖宝埋入体内,那世上无论山中地底,凡有宝物,便可瞧得一清二楚,从此便可富贵了。”
雀官见他说得奇异,便道:“方才那老鳖有鳖宝么?老丈若将它取了,岂不是立即富贵了么?”
老者笑道:“我要这富贵作什么?再者,此宝在人体内乃吸人精血为生,时日久了,人便耗尽寿元精力,所谓得不偿失也。雀官,你要知晓,这世上的富贵取之不尽,若该你的,自然会来,若不该你的,切莫强取。为人最忌贪婪,此乃伤身亡命的本源。”雀官虽听得似懂非懂,却也把头点得鸡啄米也似。
在路上行得几日,离那州府渐渐近了,那路上死的人却越发多起来,多因饥饿而死。雀官却因葛洪每日捉了鳝鱼等物,吃得饱饱得,倒长得胖了些。
这一日,二人正杂于众人之中行走,忽听得一阵哭声,渐渐近了,却是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孩童号啕大哭,那孩童也只七八岁年纪,已瘦得骨瘦如柴,正昏死在母亲怀中,眼见出气多,进气少,不一刻便要命归黄泉。
众人每日生死见得多了,也不多在意,只是孩童的母亲哭得伤心,雀官见这孩童与自己年纪相仿,他的母亲也与自己母亲一般年岁,心中酸楚,也流下泪来。
葛洪却走上前去,翻开那孩童的眼睛看了一看,道:“此是中恶了,不妨不妨。”便要那妇人将孩童放于地上,又唤过雀官道:“雀官,你快快将尿撒在这小哥脸上。”
雀官已有八岁,又有众人在场,却有些害羞。那妇人也哭道:“你这老人好不晓事,我儿子已自将要死了,你还要用尿来辱他,这是什么道理?”
众人见葛洪说得古怪,也多有不忿,便有那男子要来打他,葛洪便道:“莫忙打莫忙打,我要用尿撒他脸上,乃是要来救他,你们岂不知那《肘后卒中方》中便有这用尿救人之法吗?如今这孩童已命在顷刻,倒不如死马作活马医,若是无效时,你们再来打我老汉不迟。”
众人听他如此说,都面面相觑,道:“什么《肘后卒中方》?他既如此说,不妨且信他一信,如不成时,再来算账。”
那孩童母亲本无什么主意,见众人如此说,也只是哭。葛洪便催促雀官,雀官究竟有些不好意思,那葛洪便道:“不要作此儿女之态,人命关天,莫再延误了。”
雀官无法,只得当众解开裤带,对着那孩童面上着实拉了一泡尿,把那孩童一脸一身都弄湿了。
不一会,便见那孩童眼皮微动,随即睁开眼来,四周望了望,又自己坐将起来,口里吐出一口浓痰来,便喊道:“娘、娘。”
那妇人见他果真醒了,连忙一把将他搂进怀里,又慌忙与那孩童都跪在地上,向葛洪与雀官道谢,那孩童睁眼看着二人,兀自迷惑不解。葛洪却只是笑笑,拱手而去。
雀官却十分惊奇,问道:“用尿也可以救人么?当真稀奇!那个《肘后卒中方》是什么方?”葛洪笑道:“天地之间万物,俱是相生相克,有那许多不起眼的物事,却可起大用呢?这《肘后卒中方》却是一个医书,里面多是记载一些急救的方子,方子里多是随手可得的东西,如此方能在急症发作时相救。”
雀官道:“老丈你真是博学多识呢,什么都晓得!”老者却笑道:“哪谈得上博学多识,不过多见多闻罢了,老汉在江湖上行走多年,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是学一些的。”
当晚,二人又离了众人,去寻吃食,渐渐离那大路远了,却见那前面有一座庙宇,不甚高大,走到近前时,已颇为破败,好在主殿屋宇俱是完好的,门前写着三个字“水神庙”。
葛洪便喜道:“今晚倒有个好住处,不用在外风餐露宿了,雀官,你且将这里面打扫一遍,我自去寻些吃的来。”便自走了。
雀官走进庙里,见那庙门外俱是淤泥,因那门坎高了,里面倒还干燥,只是久无人来,十分破败,处处蛛网丛生,灰尘遍地,雀官便将那地上收拾一块出来,好作晚上住宿之处,又见那庙内有些柴草,便在殿中用火石升起一堆火来,待老者回来烤食鱼鳝。
火光之中,雀官见那正殿之上有一座高台,台上却竖着一尊神像,约摸七八尺高,神像身上不知是金身剥落还是本就如此,黑黝黝的,身子是人的身子,头却是一个尖尖的,似鱼又似蛤蟆的样子,一双眼晴大大的,满生鳞片,却似个妖怪一般,狰狞可怖。
雀官便吃了一惊,他虽经历生死,胆子已然极大,却终究仍旧是个孩子,夜晚之中,独身一人在这妖异的庙里,仍不免心中惴惴。他便坐到门首,翘首等那葛洪回来,却见那庙门左侧,树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满了文字,左右无事,他便扎了根火把去看。
只见那碑上刻的却是这庙的由来,道是这庄子本是个风调雨顺,富足友睦之地,庄人们多也是靠水吃水,在水里讨生活,日常靠打鱼捕虾为生。有一年,不知怎的,庄子里的汉子外出打鱼却屡遭凶险,接连死了好几个人。
后来有一夜,庄子里便有许多人做了同一梦,梦里一个鱼头人身的神灵道是此地河神,要庄里人起一座庙宇供奉他,他便保佑风调雨顺,四季平安,如若不然,他便要降下灾祸,眼见得这梦做了几次,人也又死了几个,庄子里人也着实恐怖,便凑些银子,建了些水神庙,并依梦中所见铸了神像。
果然,庙宇建好之后事,庄子里太平了两年,出去打鱼时不再死人,众人便四时祭祀,香火不断;过得两年,庄里人又梦见那河神来道,需得每年供奉一名幼儿与他吃了,助他修炼,庄里人无法,只得每年在那庄里寻一名小儿,于中秋之夜奉于庙里,以保平安。
碑上的话便到此为止了,至于那幼儿如何,后来此庙又如何荒废了,便一无所知。那碑上大意是如此,却甚是隐晦,只道是“小儿有幸,得奉神灵,佑我河湖,波澜不兴”云云。
雀官上得几年学,却是看得懂的,不禁心中既惊又怒,想道这河神不知是何妖怪,假托神仙之名,却行此吃人害人之事,若此等怪物也称之为神仙,那还求什么道问什么仙?他见此地诡异,心中也自害怕,便不进庙,只坐在门坎之上,等葛洪回来。
方自坐得一会,忽听得庙外传来一声凄厉的婴儿啼哭之声,如泣似诉,又似夹杂着无尽怨恨,在这荒郊旷野,妖庙之前,显得尤其尖利诡异,把个雀官听得毛骨悚然。忙站起身来,朝外看去,但见月色昏暗,庙前一片俱是野草淤泥,哪里瞧得见什么东西。
他心知那碑上所言,所谓的选取小儿侍奉河神,却定是被那河神吃了,多半便是这些冤死的小儿鬼魂在此作祟。欲待不去管它,但那婴儿啼哭之声不止,一声比一声凄厉,竟渐渐向庙门靠近而来。
雀官心中害怕,伸手从怀里摸出刀来,握在手中,强自镇定,道:“冤有头债有主,你们要报仇只管找那妖怪报去,却在此哭什么?”那哭声骤然停了,一时万籁无声。
雀官便觉身上发寒,似乎起了阵阴风,便欲朝庙中退去,却陡然又闻得那婴儿哭声又响将起来,却已在距自己不足一丈的草丛之中,他心里吃惊,定睛看时。
只见那杂乱的草丛之中,正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头戴虎头帽,四肢着地爬在地上,一双眼晴绿荧荧的,正瞧着自己。
雀官只觉心已跳到喉头,便欲转头逃走,但想那庙里也是阴森可怖,不知还有多少小儿冤魂,还不如在这旷野之中有处可逃,便壮起胆朝那婴儿走去。
还未到得近前,便见白光一闪,那婴儿刹时之间没了踪影,雀官心里惊惧,朝后退去,还未回过神来,便听到那婴儿的啼哭之声自庙上传来,转头一瞧,那婴儿正趴在庙檐顶上,头戴虎头帽子,眼睛发出绿光,正死死盯着自己,一时便觉得心如擂鼓,汗毛直树。
眼见这婴儿鬼魂来去如电,阴森可怖,不知它要怎的,只是握紧了手中刀,把眼睛不敢眨得一眨,生怕这鬼婴便要扑下来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