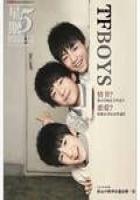查尔斯爵士把头伸出门外叫道:
“萨特思韦特,进来一会儿好吗?”
一个半小时已经过去。平静代替了混乱。玛丽夫人把哭哭啼啼的巴宾顿太太带出别墅,并与她一起到了牧师的住宅。米尔雷小姐一直在电话机前忙碌。
当地的医生赶来查看情况。大家简单地用过晚餐。相互寒喧几句之后,客人们都回到各自的房间。当查尔斯爵士从发生死亡事件的“船舱大厅”门边叫他时,萨特思韦特先生正准备回到他的房里。
萨特思韦特先生走进大厅时。拼命克制身体的颤抖。他已经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实在不能目睹死人的场面。也许,他自己也很快会……不过,想这个干什么呢?
“我很健康,还能再活二十年。”萨特思韦特先生自言自语地说,心里充满自信。
留在船舱大厅的另外一个人是巴塞罗缪·斯特兰奇。他一见到萨特思韦特先生就向他点头致意,还带有几分赞许。
“好人啊!”他说,“我们都能与萨特思韦特先生很好地相处。他懂得生活。”
萨特思韦特先生坐到医生旁边的扶手椅上,听了这话有点儿吃惊。查尔斯爵士在来回走动。他下意识地半握着拳头,但那神态绝对不像一个海军军官。
“查尔斯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发生。”巴塞罗缪爵士说,“我是指可怜的巴宾顿老人的死。”
萨特思韦特先生想,人的情绪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显然,谁都不会“喜欢”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意识到斯特兰奇医生表示的不是他话中所表达的一般含义,而是别有所指。
“真令人悲叹。”萨特思韦特先生小心翼翼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确实非常令人悲叹!”他以一种缅怀往事的心情颤栗地重复着。
“唉,是啊。这是相当悲痛的事。”医生说话时,声音里有一种职业化的腔调。
查尔斯·卡特赖特停下脚步。
“托利,曾经看见过有人这样死去吗?”
“没有。”巴塞罗缪若有所思地说,“可以说我没有见过。”“但是。”片刻之后,他又补充说,“我不像你想像的那样,看见过很多人的死亡。在一个精神病医生的手下,不会有多少人死掉。他要让病人生存下来,还要从他们那儿获得收入。毫无疑问,麦克杜格尔比我见过的死人多得多。”
麦克杜格尔是鲁茅斯镇的主治医师。米尔雷小姐请他看过病。
“麦克杜格尔并没有看见这个人死去。当他赶到这儿时,那人已经死了。
他只知道我们告诉他的情况。也只有你能告诉他具体情况。
他说,死亡是某种疾病突然发作引起的。还说巴宾顿先生已上了年纪,他的体质不太好。我对他的话并不满意。”“我也许同样不会使他满意。”另一位咕哝道,“但是,一个医生总得说点什么。突然发作,是一个很好的解释,但根本不说明什么,却能够让外行人满意。而且,巴宾顿毕竟上了年纪。他的妻子告诉我们,最近他的身体一直有毛病。可能是某个器官患有意想不到的疾病。”
“那就是典型的痉挛,或者突然发作吗?你随便叫它什么好了。”
“典型的什么?”“某种典型的疾病。”
“如果你学过医,”巴塞罗缪爵士说,“你就会明白,几乎没有所谓典型的病例。”
“你到底在暗示什么,查尔斯爵士?”萨特思韦特先生问道。卡特赖特没有回答。他只是做了一个不明确的手势。斯特兰奇轻轻笑出声来。
“查尔斯不了解他自己,”他说。“他的思路总有可能导致戏剧性的结果。”
查尔斯爵士做了一个责备的手势。他的脸上显出专注的样子,思绪万端。
他轻轻地摇摇头,茫然若失。
萨特思韦特先生正在苦苦思索。他跟谁有难以想像的相似之处?随后,他终于想起来了。那是情报部头目阿里斯蒂德·杜瓦尔。是他解开了“地下网络组织”错综复杂的疑团。过了片刻,他坚信不移。查尔斯爵士走路时步履蹒跚。而阿里斯蒂德·杜瓦尔……一直被称之为“步履蹒跚的男人”。巴塞罗缪爵士继续为查尔斯未成形的疑团提供常识性的解释。
“是的,你怀疑什么,查尔斯?自杀?他杀?谁会谋杀一个与世无争的老牧师?真是不可思议。自杀吗?这个,我想也有道理。人们也许不难想像巴宾顿要自寻短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巴塞罗缪爵士轻轻地摇摇头。
“我们怎么能说清人的内心秘密?我有个设想——假如有人告诉巴宾顿说他患了不治之症,比如说癌症。这样一类事情就会引发一个动机。他会希望妻子摆脱看见他长期遭受折磨的痛苦。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世界上没有什么会使巴宾顿愿意像这样去了结一生。”
“我对自杀没有想这么多。”查尔斯爵士开始说话了。巴塞罗缪·斯特兰奇又一次发出轻轻的笑声。
“确实。你要想方设法找出可能的线索。你需要有轰动效应的证据。如有人在鸡尾酒里放了一种很难查出的新型毒药。”
查尔斯爵士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怪相。
“我不敢说我想得到证据。真******够呛,托利,你还记得吧,是我调兑的鸡尾酒。”
“是杀人狂的突然袭击,是吗?我想,我们这个案子的征兆被拖迟了,否则,我们所有的人在天亮之前都会死去。”“该死,你在开玩笑,但是……”查尔斯爵士激动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医生说。
他的声音变了,显得很痛心,但没有反感的情绪。
“对于可怜的老巴宾顿的死,我怎么会开玩笑。我只是对你的设想说几句有趣的话,查尔斯。这是因为……直说吧,因为我不想让你轻率地加害于人。”
“加害于人?”查尔斯爵士大声问道。
“萨特思韦特先生,也许你明白我针对什么而言?”“我想,我也许猜得出来。”萨特思韦特先生说道。“查尔斯,难道你没有看见,”巴塞罗缪爵士继续说,“你毫无根据地猜疑,显然会伤害别人。事情总要传开。对案件完全没有根据的模糊不清的设想,可能会对巴宾顿太太带来严重的麻烦和痛苦。我知道这种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只要有几个加油添醋的家伙插手,关于突然死亡的流言就会满天飞,并且会愈演愈烈,最后谁也无法收拾。你真够呛,查尔斯,你难道没有看出其后果不堪设想吗?这完全是要避免的。你这是在放纵自己的想像力,完完全全在凭空猜测。”
演员的脸上露出不知所措的神情。
“我并不是那样去想问题。”他说。
“你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查尔斯,但是你却让你的想像漫无边际地奔驰。说说看,你真的相信有人会杀害一位绝对与世无争的老人吗?”
“我想不会,”查尔斯说,“不会的。正如你所说,那是荒谬的。对不起,托利。在我看来,这确实不是一个单纯的突发事件,我有一种预感,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头。”
萨特思韦特先生轻轻地咳了几声。
“我可以说说我的想法吗?巴宾顿先生走进屋里,刚刚喝了鸡尾酒之后不到几分钟就病倒了。那时,我碰巧注意到他喝酒时面有苦相。当时我猜想他不习惯鸡尾酒的昧道。假如巴塞罗缪爵士的推测是正确的话,巴宾顿先生是会因为某种缘故去自杀的。如果有这种可能。那确实让我感到震惊。然而,他杀的意见看起来却又十分荒唐可笑。”
“我感到巴宾顿先生有可能将什么东西放进杯里,而不让我们发现。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太大。”
“现在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没有被人动过。鸡尾酒杯都没有动过。仍摆在那儿。这就是巴宾顿先生的那一杯。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正坐在这儿跟他谈话。我建议请巴塞罗缪先生把这个杯子拿去检查。做这事要悄无声息,才不至于引起闲话。”
巴塞罗缪爵士站起来,拿了酒杯。
“对了。”他说,“我会遵命的,查尔斯。我敢拿出十英镑来跟谁打赌,杯里肯定什么也不会有。绝对只有杜松子酒和苦艾酒。”
“成交。”查尔斯爵士说。
随后他脸上又露出了懊侮的笑容。
“要知道,托利,我这样胡思乱想,你是有部分责任的。”“我?”
“是的,与你今天上午谈论的犯罪有关。你说,赫尔克里·波洛这位仁兄是暴风雨中的海燕。你还说他到哪里,案件就会跟到哪里。他刚刚到达,我们这儿就出现了可疑的突然死亡事件。于是我的思路当然一下子转到了谋杀上。”
“我不明白。”萨特思韦特先生说着又停了下来。
“是的。”查尔斯爵士说,“我是想到过谋杀的可能。你怎么想,托利?我们可以问问人家想到了什么?这是一种常规吗?”
“说得好。”萨特思韦特先生喃喃地说。
“我知道医学常规。要是我知道一点破案常规,我就该死。”“你不必要求一个职业歌手唱歌。”萨特思韦特先生咕哝着,“难道你有必要要求一个职业侦探去侦查吗?是的,查尔斯说得好。”
“只不过是个人的看法。”查尔斯爵士说。
有人在轻轻敲门,接着赫尔克里·波洛出现了,他抱歉地看着屋里的人。
“进来吧。”查尔斯爵士站起来叫道,“我们刚刚才谈到你。”“所以我想我来得太唐突了。”
“哪里哪里!喝一杯吧。”
“谢谢你,我不喝。我很少喝威士忌。来杯果汁吧。”可是,查尔斯爵士的饮料柜里不会有果汁。刚把客人安顿坐在椅子上,这位演员就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
“我不想转弯抹角。”他说,“我们刚刚谈到你,波洛先生。而且,而且也谈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说,你认为有什么不妥的吗?”
波洛眉头一扬,说道:
“不妥?你指的什么……不妥?”
巴塞罗缪·斯特兰奇说,“我的朋友脑子里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巴宾顿是被谋杀的。”
“你不这么想吗?”
“我们希望知道您的看法。”
波洛意味深长地说:
“他病倒了。当然,病得突然……确实非常突然。”“就是这些吗?”
萨特思韦特先生说明他对自杀的看法,以及他要求检查鸡尾酒杯的建议。
波洛点头同意。
“不管怎么说,这没有坏处。从人性的角度来判断。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有人竟企图除掉一个极好的、与世无争的老年人。在我看来,自杀的可能也很少。然而,鸡尾酒杯会告诉我们一点蛛丝马迹。”
“你认为检查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波洛耸耸肩头。
“我吗?我只是猜测。你问我检查的结果吗?”“对。”
“那么我猜他只会发现杯里有非常高级的鸡尾酒残余(他向查尔斯爵士点了点头)。为了在鸡尾酒里下毒谋害一个人,托盘里的酒杯经过这么多人的手要那个人得到,这在技术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如果是那个漂亮的老牧师想要自杀,我认为他是不会在一个晚宴中干这种事情的。那会表明他毫不顾及他人,而巴宾顿先生体谅他人的性格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停了一下又说,“既然你问到了我,这就是我的看法。”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查尔斯爵士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打开一扇窗子朝外看去。
“风随人意。”他说。
当查尔斯转身回来时,情报局的侦探已经无影无踪。对于观察敏锐的萨特思韦特先生来说,查尔斯爵士似乎在渴望着他毕竟不能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