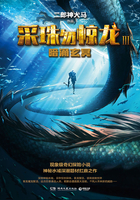余泽郁闷苦恼的是;他今年六年级,这个学期是升级班,小升初,说来这也是一件好事情,他老师晓得他家的情况,去家访一次,就晓得余泽在家就是一根草,于是就直接和余泽谈,让他去考个好的初中。
余泽去考了,但没考上,这让余泽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下子气虚,尽管没有人知道,他也感到脸上无光,这段时间也就抬不起头来,原本就不爱说话的人,就更不说话了。
他正在山上割草呢,就见小奴婢从山底摇摇摆摆的爬上来,一边爬一边叫他,余泽换了个灌木丛深得遮住身的地方割草,只作没看见。
“余泽!”
不过才一会儿,这小奴婢居然找到自己了,她从林子里窜到面前,吓了他好一跳。
“你在这里啊,我刚才叫你你也不应我一声!”
余晴来的时候也带了镰刀,她说完也不等余泽回答,蹲下身就“唰唰”地开始和余泽割草起来。
过了一会儿,余晴瞥见背篓里的草差不多了,她开口:“你是咋个回事咯这几天?”
见余泽并不打算理她的样子,余晴又问:“哇!不是吧?你不会是生我前几天的闷气儿吧?”
余晴口气十分讽刺惊怪,余泽这会儿想不理她都不行。“不是!”余泽过了半响,慢吞吞的回道。
“哦?那是咋个了嘛?”
“和你没关系。”
“哈!你以为我稀罕晓得啊?”余晴扯住余泽衣袖,瘪着嘴:“雯姨怕你有事,让我问哩!”
“嘶……啧啧……放,放手!”余泽龇牙咧嘴地倒抽气,连连躲开余晴的魔爪。
余晴一看,原来是她扯到了余泽手上的伤口,正淅淅沥沥的不断冒血,伤在他左手背上,口还挺大!大个人了,居然还不晓得好好包一下,余晴是鄙夷中怒火中烧!
“你就是个猪脑壳!”余晴拉起余泽的手,扯了把苦蒿,也不管苦不苦,撕开嘴往里面塞了,咀嚼几下吐在手心,“啪”地一下就敷在余泽口子上,不出片刻,血倒是好歹止了住。
这时候,余泽也没来得及反应,眼睁睁看着小奴婢把嘴里嚼的烂兮兮的苦蒿叶恶心巴巴地拍在他手背上来。
“啊呸!呸!苦死了,这鬼东西!”余晴连连吐口水,抱怨苦蒿太过苦。
见她这样,原本想把自己手背上的恶心东西扒拉下来的余泽,手上就不再动作了,嗯,苦蒿止血他自然晓得,不过他特别讨厌苦蒿的气味,若不然,哪里轮到这小奴婢假模假样假好心?
苦蒿本来就气味不讨喜,再有余晴这番恶心操作,可把余泽恶心坏了,不过,恶心归恶心了点,止血确实管用,他只能咬牙忍着手背上恶心巴拉的东西热辣辣地敷着口子。
草割够了一篓,余晴一跳一跳,歪歪扭扭地走在前边,余泽则黑沉沉着一张臭脸背着草走在后头。
余泽看着前面余晴忽跳忽闪的马尾,觉得那根讨人厌的马尾像个钩子,手上恶心人的苦蒿像条虫子,二者都在往他心尖尖里钻,刺痒痒,麻酥酥,这就是余泽在余晴对他好时的感觉,不难受但很奇怪,反正余泽就不是喜欢得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