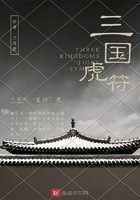中年人将手里的齐眉棍放置桌旁,也不含混敷衍,开门见山地道:“老夫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姓周,名侗。”
此话一出,不但令店家惊呼,就连两名衙役也顿时停住手里的碗筷,被他吸引,但看他们脸上却是提防警惕,隐有杀机,似乎对这个叫做周侗的人深恶痛绝,但又强忍不便发作,似乎又对此人大有忌惮,周侗见店家吓得面如土灰,双目涣散,哈哈大笑起来:“我知道老夫名字如实相告定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想不到这种地方还能见识到吕贤良的身影,真是不易啊。不过百无一用是书生,落得今天这般田地,真是可惜。”
吕敦儒大惊失色,他居然直呼自己名讳,似乎对自己非常熟悉,可是自己的印象之中没有这人的半点迹象,又说了句存心埋汰自己的话,让自己本就好胜的气势陡然火星迸发。
还未待自己问话,为什么要羞辱自己,周侗又道:“吕贤良也别先急着动怒,老夫问你,你就甘愿做朝廷钦犯,从此老死边疆,可真叫人心寒啊,以前血气方刚,嫉恶如仇,不惧皇帝老儿的吕贤良,今日变得懦夫无能,家中父母双亲尸骨未寒,你却甘心低头服罪,可悲,可怜的紧那。”
吕敦儒再也忍不住他的冷嘲热讥,这分明不是来歇脚庇荫,反而是冲着自己来找不痛快的,正好有气没处撒,这人倒好,没说半句安慰的话简直火上浇油,吕敦儒怒愤难泄地道:“你到底是何人?我是好是坏,是生是死,正直也好,屈辱也罢,与你何干?”
周侗一边倒了碗酒,一边不慌不忙,神情悠哉地答道:“我是来解救你的,老夫一生也是最爱多管闲事,替人出气,要是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咱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这句话当着吕敦儒说倒没觉得什么,可在两个朝廷当差面前公然藐视王法,目无章纪,好比在自己脸上扇了一个耳光还难受,一个年长的衙役甲忍不住站将起来,正面看着他,可还是双腿战战兢兢地假装坚强道:“周侗,我知你是枪棍天下无双,一生侠义之名,可你公然敢于朝廷作对,就不怕王法么?”
吕敦儒听衙役这么一说,这才有些印象了,难怪刚开始听到这个名字那么熟悉,原来此人正是当今大名府玉麒麟——卢俊义的授业恩师周侗。听闻他枪棍天下无匹,兵法入神,可惜一生不肯出仕做官,只图逍遥洒脱,又说此人最喜欢结交江湖义士,武艺超群,几乎无人能敌,义气有节,不向权势低头,是个不折不扣的真英雄,却不料中年授业不善,误传恶人史文恭,以至于很少在江湖露面,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此人,但此人来意不明,也不知是敌是友,吕敦儒先是赞忍一时,看看他到底是何居心,意欲何为?
周侗不理衙役的兴师问罪,反而一点衙役不在乎什么王法朝廷,对这些早已习惯,充耳不闻地道:“吕敦儒,你读圣贤之书,是为救自己还是救天下苍生?”
吕敦儒慷慨激昂地如实回答:“当然是黎民百姓,不然我何意上表万言之书。”“那好,可惜你现在连自己都救不了,怎么救别人,此话未免夸口。”
周侗轻蔑地笑意,让人感到他纯粹是来找自己麻烦的,要帮忙不需废话啰嗦,凭他的本事,就算千军万马,救人好比吃饭睡觉一般简单,何必这么损坏他人名声。
两名衙役知他本来高强,不是对手,不敢轻易对其下手,只期望能从他的眼前逃脱,好去通风报信,让大军来捉拿他。
吕二口无言以对,自己一直以来追求能饱读诗书,替国分忧解难,让天下黎民百姓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做个为民造福的好官,可惜朝纲不振,皇帝昏庸无能,弄得自己有志无处报,有力没处使,最后家破人亡,流放从军的局面真如他所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连自己性命不保,何谈什么鸿鹄大志?可是又想从军正好磨砺体肤心智,不一定非做官就能为天下解忧,“我到了边疆一样可以施展抱负,身还未修好,怎谈治国,平天下?”吕敦儒振振有词地说道。
周侗连声叫好,又反问道:“皇帝无能,奸佞小人弄权,国运颓势,你到了边疆就真能施展抱负?何必自欺欺人,既然不能从文,何不学我一样仗剑携酒江湖行,快意恩仇,斩尽天下不平事。何许苦恼,不过我看你也没这个胆量与勇气,心将既死,万念俱灰,活着也不过行尸走肉,我还以为你这样的人将来会成为我的对手,今日得蒙一面,一目了然。悲哀至极。”
周侗的话中充满了失望,这种失望无疑是对自己的藐视和轻贱,激起吕敦儒多年以来的激愤,双拳紧握,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有这么坚决和勇气面对一个不可能打败的对象,反激起了他的斗志,咬牙痛恨地道:“好,不怕你是成名已久的江湖前辈,手下能人贤士数之不尽,今日我就答应跟你比试一场,怎么较量,还望示下?”
周侗笑了,这笑中含义自然明了不过,没想到几句激他的话,果然凑效,不得不说他是老谋深算,自鸣得意的说道:“这才像话,这样也才有意思,不然都说你有血性我还到别人吹嘘,这样吧?我年纪也大了,不能跟你们年轻人比,有冲劲和野性了,不如我们各自重新开始,看谁能胜过谁,我再收一个弟子,正好此次前去汤阴也就为传功授业去的,你也重新习武读书,你如果在任何方面胜过我教导出来的弟子,周侗这颗项上人头任凭你处置,还向今日之事,公然向天下告知,向你道歉,你如是输了,我也不要你性命,从此不再正直做人,当乞丐怎样,受尽天下唾弃,毫无半分颜面,着期限么?就以二十年为期,我就算死了,也会向这个弟子交代,你意下如何?”
吕敦儒不怕麻烦找上自己,何况这是污蔑自己自尊的大事,不能不答应,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对手,心有不甘,却更增自己的斗志,毫不犹豫地道:“好,周老英雄这般抬举吕某人,在下岂有拒绝之理,就以二十年为期,谁若反悔,人神共诛!”
周侗志得意满地会意,然后站将起来,不管哪两个衙役如何地对他恨之入骨,又惧怕的全身颤抖,径直走将过去,距离吕敦儒只有不到三尺的地方,冷冷一笑。
吕敦儒不明他这一笑蕴含什么深意,令人难以琢磨,何况此人有悖于常理做事,很难让自己去预料,只见他左肩微微一动,来不及自己反应,手中已是多了一串钥匙,这出神入化的手法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变故,让吕敦儒都未看清他是怎么取到衙役身上的钥匙,可谓是技压全场,如闪电迅捷不及眨眼,生怕这一瞬稍纵即逝;又像清风拂面,给人一种不知不觉的阴冷,这种压抑与前所未有高峻,让自己望尘莫及,吕敦儒害怕地吞吞口水,想说些什么,却又什么也说不出声来,面前这个人不但技艺超群,而且智谋非常人能比,别说给自己二十年战胜他,就是一生或许比肩的愿望也变成了奢侈,难怪他会说与他所授的弟子比试,论年纪和见识来看,自己虽年轻,而时间的推移,他形瘦枯槁,走不动了,自己再找他比试,胜之不武。
他向自己展露着一手难道是想让自己知难而退?还是另有深意,到让自己难以揣摩不透,周侗又是一副谦逊的笑意,生怕给吕敦儒带来任何负面心理压抑,解释道:“我从这两名当差身上取来钥匙,不时卖弄什么本领,只是让你看清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不会受什么世俗格局,规矩限制,放任自流,狂傲不驯,那些狗屁王法在我眼中不过是浮云般时有非无,也给你点求胜欲望,不时任何人都不可战胜,关云长不也掉以轻心而丧命,我周侗也是肉体凡身的人,皇帝老儿也是,真正不屈不死的唯有一种精神,数十载之后,终归一撮黄土而已,真羡慕你还年轻,可百余年之后呢?但平庸地死和有鞭策、激越、带着信仰、无形追逐,是不是强上许多,至少到死之时无怨无悔。我知你跟我一样高傲,不会同意把你的枷锁打开,这不过是督促你好好活下去的理由罢了。我好不容易有个对手,也算是不寂寞了。”
吕敦儒还是没有说什么,因为知道自己在他面前根本藏不住什么心思,他什么都能看穿、看透、能直达自己心里,现在别说在武艺上是个门外汉,就连任何方面都有着天差地远的区别。但他一句话叫人越发深醒,彻底觉悟。现在自己虽只能望其项背,有朝一日能并驾齐驱恐怕也是痴人做梦的奢望,但这种奢望正是自己好好活下去的理由。
周侗转身欲走,也没有出手伤了两名衙役,反而将钥匙原封不动地还了回去,只见他回到原来座位旁取过齐眉棍,走出丈许的地方,暮地猛以转身,整个人曲弯成弓箭步,右手臂在转身一瞬息之际伸直,劲力所到之处,抓住棍端,棍与肩平,连接一直线,而棍末端所指竟是放在桌上的一顶毡帽,毡帽上的系带距离他足足有一丈五六尺之远,他人不回去拿取,反而以敦代手,使将出一招耐人寻味,奇招迭出的——回马枪。
此招惊若天人,一气呵成,毫无破绽,恐怕在周侗手下练了不知成年累月,千遍万遍才能有这般炉火纯青、登堂入室的地步,连店家都看得目瞪口呆,忘记喊出声来,立即被其震吓呆住;两名衙役也是惊犹未定,不知所措,为刚才悄无声息取走腰间钥匙和这招扬名立万的江湖绝学而震惊失色,不由面面相觑,深深吸了口凉气,都暗叹刚才要是他出手,自己两个的性命早已不在,又摸摸全身上下有无异样,生怕死得不明不白,还被当作戏看一样凑着热闹,侥幸自己全身完好无损,这才常常舒了口气,但情不自禁的拍手叫绝,为之惊叹不已。
吕敦儒也是为之震慑,他这转身取帽,只是大展身手还是故意卖弄?简直疯疯癫癫,一点大家之风也看不到,不过这记不动声色,出乎意料,难以预料的回马枪却是深得其髓,出类拔萃。
只怕当今那个什么玉麒麟卢俊义在这招面前也会黯然失色,此招一出,不管对手有多么厉害,多么高强,只要毫不知情被其诱惑,立即疏忽,哪有命在?
周侗右手轻轻一弹,棍上劲力转移,改变方向,那顶毡帽如长了眼睛一般飞落左手之中,平平稳稳地接过,戴在头顶,转身即走,头也不回地喊道:“贤良之士,我辈敬仰,切记一句,是人都有弱点,任你是权高位重也好,人微低下也罢,只要心诚之至,没有办不到的。给你指条明路,天下之大,我不是独一无二的,天外有天,少林心如止水鉴常明,丐帮势众藏龙卧虎,好之为之。”话音已毕,盈久不绝,而他的人影也早已消失在一片飘渺的光天化日之下,留下的只是那句令人难以捉摸的谜语。
吕敦儒不明白他到底为何煞费苦心地要来见自己,给自己一种无形压力,到底出自什么目的?真是匪夷所思这个周侗的举止,难怪对于他的传说却是纷纭,不足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