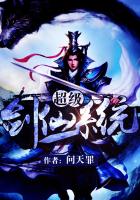一进刘李村,恍如进到了人间炼狱,无不触目惊心,惨不忍睹,就连呼吸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种浓郁的血腥气味,烦郁不安,闻则欲呕。
村口,纵横交错的阡陌小道两旁,或是正在自家田地里劳作,或是大凡李姓与自己有血脉联系,或是堂族李姓旁亲的自家院子里,都七零八落地倒着死相惨烈的尸体,上至祖辈的耄耋老者,下至刚呱呱落地的婴孩,男女老少无一幸免。就算李吟风久经沙场,每次浴血奋勇地与残暴的金人对峙,所见的惨烈情景亦不过如此。自己从小生活的家乡像是遭遇了一场血劫,每到一处,所看到的景象深深震撼、触动、重创着自己的心,惨凄得不敢多看。
这到底究竟是谁?如此狠毒无情,做出这等惨绝人寰的恶行,就连妇孺、小孩也不放过,难道不怕遭到天谴么?途经一座奢华雍容的豪宅,尸体遍地,鲜血四溅,原本这里张灯结彩,一片欢天喜地,高朋满座,热闹非凡,看着散落在院子的尸身似乎自己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原来这正是自己堂叔李法华一家,没想他趾高气扬一生,最终落得不凄惨烈,无不令人感到扼腕悲叹。
更能想象来者不请自来,将唯一出路堵死,谁也预料不到他竟不是来道喜祝贺的,突然发难,院子里的人们正在杯觥交错,尽情欢畅痛饮,不想一声惨叫,有人倒地,鲜血溅起,恐惧顿然将满怀欣喜驱赶,充斥占据了神智,开始朝院子外仓惶逃生,但门口还有强人看守,寻常百姓想要逃生必然奋力一拼,那是心狠手辣的恶徒对手,最后血流成河,尸体充塞整个院子,无一幸免。
胡虏残暴,禽兽不如,所到之处鸡犬不留,洗劫一空,其手段与狠毒无不令人恨之入骨,不想远离金人肆掠的江南也遭遇这样的灭顶之灾,心中实在不敢想象,更无法猜测,甚至还担忧金人大军已经占据了江南,见人就杀?决计不会想到这是谁所为?
以死者身上的致命伤口以及血凝程度来判断,也不过最近两三日之前的事,李吟风猛地醒觉,暗自焦灼道:“沈姑娘和她母亲曾说过爹娘不在人世,难道……”愈想愈害怕,不敢再为所见情景夙夜忧叹,悲伤感怀了,将“昆吾石”紧紧地握在手中,开始朝着记忆中自家的方向飞奔过去。
当李吟风开始踏入自己老家那片树林时,心情如泰山般沉重,既怕见到最为不忍目睹,惨凄恐怖的一幕,又怕自己的优柔寡断,拖泥带水不能及时见到爹妈最后一面。沉迈地一步一步踏上那条阔别已久,熟悉而又生疏的山路,静谧而幽深,遮天蔽日的树木下杂草葱郁,那条唯一通往自家的小路早已面目全非了,而且山林中没有人走过的迹象,李吟风惶急爹妈的安危,来不及清理道路两旁的杂草,腾身跃起,纵跳至一棵树干,然后提气于后脑勺“玉枕穴”,朝着林子深处施展轻功。
当自己到达那间不大的小木屋时,心神俱震,既熟悉又凄凉的感觉油然而生,篱笆东倒西歪,还有些已经腐烂,倒是篱笆外的长满了荆棘,形成了新的篱笆,蜿蜒延生,就像一条条张牙舞爪的灵蛇长龙。
十一年没有踏入家门一步,今日故地重游,有种不尽的悲凉,仿佛一家人在这处远离家族骚扰,与世无争的小屋子里嬉戏欢笑的情景还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情不自禁地一笑,又像自己完全被疏远,与眼前这家人格格不入,近同一个外人。
鼓足勇气朝院子里走进去,以前还记得与小龙在院子里追逐嬉戏,而母亲范乙芬坐在中间摘菜,不时让自己多多让着弟弟,耳畔还不时萦绕着她的教诲,“虎子,不能欺负小龙,从今以后你们兄弟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要团结,千万不能向你爹与你那些叔叔一样。”一想起这些话,李吟风的热泪盈眶,而现在院子中杂草密集,几乎没有落脚立足的地方,也不知这里多少年没有人打扫了,一种凄凉迅速占据了整个胸臆。
几间屋子的墙壁也是坍塌了好几处,上面的所盖的茅草、瓦片陷了大洞,抬头就能看得树枝与天空白云,残垣断壁,瓦砾土块堆积满屋,家已经不成一个家了,却不见自己日思夜想的爹妈身影,在屋子中翻找了几遍,无任何气息,毫无人迹,惶惑不安地大喊着:“爹!娘!孩儿吟风不孝,回来探望您二老。”
声音震得屋檐沙沙作响,原本就没人修葺的破屋子,已是残破不堪,稍微发出一丝声响,都会掉落灰尘瓦砾,有的墙壁摇摇欲坠,随时会倒下来将人活活掩埋。
李吟风不管这些,不见爹娘人影,他不会甘心罢休的,这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这里有自己最纯真、快乐的记忆,还有许许多多的难以割舍的情节。
足足在破屋中站了不知多久,连鼻息都能闻见长期未经人修葺,被雨水侵泡过的潮湿霉臭味,许多没有坍塌的地方,蛛网罗织,还有随时可能倒向自己,将自己一并掩埋的墙壁,可惜未见爹妈半丝身影,李吟风的心也跟着悬而未决。
“风哥,风哥!”凄婉熟悉的声音传入李吟风的耳中,将自己从徜徉中惊醒回来,为了不让心爱的人担忧自己,害得她为自己感到伤心,脸上尽量地掩饰悲痛,转身迈着沉凝的步子走了出去。
毕雅涵站在院子外,一脸担忧愁容,无不令人心软怜悯。而她焦惶不安地看着李吟风,他面无表情,呆滞木讷,虽不像让自己为他担心记挂,但仍掩饰不了心里的悲痛,含情脉脉地喊道:“风哥,你……”
“涵儿,你实话告诉我,是不是你早就知道我爹妈不在人世的消息,一直瞒着我,怕我接受不了……你几时知道的?”李吟风语无伦次地问道。
毕雅涵心怀愧仄,脸上的悲伤似乎随时都要流下眼泪,呜咽地道:“我……早在五年前就知道了,还是……你弟弟李啸云亲口告诉我的,当时……我……”她也不知如何去安慰,变得语调不畅,含混不清。
“哈哈哈……五年前,当时小龙与我,义父,义母刚好团聚,那时你就从他口中得知我爹妈不幸的消息,是怕我难以接受这个噩耗,身心俱丧,一蹶不振,才一直隐瞒,我好傻,恐怕全天下人都知道,我却偏偏被蒙在鼓里,两年前与你回到苏州,竟然没有折道顺路探望自己爹妈,李吟风啊李吟风,真是一个不忠不义,忘恩负义的不孝之人。”
毕雅涵不忍看到他伤心欲绝,想上前去安慰他,尽力地与他一同度过难关,谁想他失望至极,以他的性情定是难以承受这一惨痛的事实,惨然倒下,心想他定是伤心至极,所以才变得神志不清,看似浑不在意,其实最为撕心裂肺。“是涵儿不对,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生怕你倒下,谁料我的天真妄想,却令事情变得如此不堪,我……实在罪衍难恕。”脸上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凄凄凌凌地哭出声来。
李吟风没想到她比自己还伤心,还要难过,甚至一直都在为自己着想,要说饱受煎熬与痛苦的折磨,这位真心爱自己的女子所承受的心酸比自己多得多,心里不禁抱愧地道:“涵儿,不怪你,是我这个人做事太过于粗心,而且迟钝颟顸,只想一心报国,谁却想到头来,投国无门,家人离散,我……我……哎,这一路走来,经历这么多,让我真真正正地发觉什么是世事伦常,什么人才是一生的依靠。不过……”
毕雅涵喜出望外地露出欣喜的笑容,忍不住问道:“不过什么?风哥,从今以后我都会在你身边,无论生死病痛,无论患难幸福,我们一并携手共度,永不分离。”
“嗯,大事未了,我还不能倒下,小龙所做的一切已经人神共愤,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错再错,他人在哪里?”李吟风似乎一下子清醒,变得异常敏感,再也不像什么事都糊涂颟顸,迟钝木讷的呆傻模样。
毕雅涵也不知如何跟他说明一切,但事已至此,李吟风只怕也看见了满目不凄的惨象,然而自己却力有未逮,未能制止住李啸云的暴戾恣睢,痛心不已地说道:“他再也不是你心目中那个天性纯良的弟弟,而是一个泯灭人性、无恶不作、丧尽天良的恶魔,他……”
“你们是在找我吗?哈哈哈,不用大费周章了,我正好也在找你们,我的傻大哥,还有聪颖过人的好大嫂。”一声衣袂声响,一团白影兀自出现在院子之中,与李吟风相距不过丈许,随后还有跟着一人。
李吟风双眼呈现暴怒忿恨,将手中的兵刃握得更紧了,见他一袭锦华高贵的白衣星星点点地沾满了血渍,几乎映染了全身,无不令人感到惊惧恐怖,切齿地恨道:“小龙,村子中发生的事都是你做得?这到底是为什么?”
毕雅涵也目露敌意,一眨不眨地警惕着这二人,一个是屡次斗智斗力,虽有不可分割的亲情,但却是最可怕的对手,还有一位则是妖言惑众,祸国殃民的败类,他们在一起倒不觉有什么惊奇与疑问了。
李啸云狞笑道:“不错,都是我做的,我做错了吗?相比你这位不顾家仇、日理万机、一心只有这个风雨飘摇的大宋,蹉跎一生的好大哥,我只不过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而已?”
李吟风哀叹不已,可惜引咎自责,凄楚地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变得作恶多端,你的本性善良都到哪里去了?”
“小王爷想不到这位傻小子竟然是你的大哥,此人坏我好事,而今处处与你为敌,不如就由我……”李啸云身后那人尽力地向在主子面前好好表现一把,溜须逢迎,令人恶心。
毕雅涵痛斥道:“郭京狗贼,想不到你还没死,竟然跟大金胡虏混在一起,风哥的家事不容任何人插手,你这无耻奸邪小人,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
原来尾随李啸云身边的不是别人,正是妖道郭京,想当年他贪图觊觎毕雅涵与沈琳君的美貌,乔装易容成大名府官驿道上的烧茶伙计,差点得逞,若不是李吟风碰巧经过,相救两位绝代风华的仙子,只怕她们的清白都会被这个猥亵卑鄙的小人所玷污。当年他侥幸逃脱,一直音信杳无,如今竟然成为李啸云身边的走狗,摇尾乞怜,献媚逢迎,令人厌憎。“这位不就是妙玉仙子么?怎么不见你师姐与你同路,竟然跟这个傻傻愣愣、呆头呆脑的家伙在一起,真是宁滥勿缺,不如跟随我,绝不会亏待你,说不定得到小王爷的赏识,到了燕京,过着逍遥快活,人人羡慕的日子,岂不快哉?”
“住口!你这等奸邪之徒也配与我风哥相提并论,他一个脚趾头都远胜你千倍万倍,你就算跟他提鞋也不够格!瞧你的模样,不过一只落难乞怜的狗而已!”毕雅涵勃然大怒地破口痛骂,似乎又恢复以往她刁蛮泼辣的风发之气。
李吟风与李啸云怒目对峙,对二人的争辩没有任何表情,兄弟二人彼此仇视,是多么的无奈与苦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