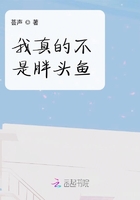“大家自己看下有哪些不懂的,”裴老师看到了教室后方的紫框大石英钟,表盘显示课间操只有两分钟,“有哪块儿不明白可以叫我过去。”
裴老师管得太松。明明她只是让同学们看下卷子,大家却渐渐地开始说话,先是交头接耳,后来干脆就放开了声量随便说。
“哎,这周末南岭有家冰场有花滑表演,”郭冰舞现在是只马上要脱缰的小鸟,等间操音乐一响就要从教室窗户飞出去,“我有张票,可我周末有小课去不了,你们谁要?咱学姐安娜回来了,还有中岛馨花噢。”
“中岛馨花?”言道明对本校学姐提不起兴趣,听到中岛馨花的名字却有点高兴,“是不是cos成北小鸟滑冰的那个?”
“对呀,”郭冰舞点点头,“超绝可爱开心花。”
“超绝可爱北小鸟,北小鸟最可爱了。”
看言道明这样,贝程橙确认他也喜欢自己喜欢的动漫。可听他说北小鸟最可爱,贝程橙就气打不过一处来——虽然西木野真希并不走可爱路线,但她在贝程橙心中才是最可爱的,她永远是最可爱的。对此贝程橙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反驳。
裴老师当然没去管学生们说话。取而代之地,她注意到,今天的余正夏居然趴在桌子上,跟周围嘻嘻哈哈的同学们格格不入,跟往日认真学习的余正夏本人也大相径庭。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花了十几天,全校师生可算习惯了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招呼全体学生上操场做操的歌,原本并非这首,而是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一首六个大男孩唱的轻快的歌。高考百日誓师过后,杨培安激情万分的嗓音就成了雷打不动的课间操信号,给高三学长学姐们加油的时候,也试图向其他的学弟学妹们去传递信念与希望——大多数以为高考还早的学弟学妹们并不愿接受且认为纯属洗脑的东西。
歌声像一道明媚的阳光,直入余正夏充满纷纷扰扰的脑袋。不管他父亲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管他和母亲要怎样带着过去面对今后的时光,现在他都必须伪装成一个身上什么都没发生过的人。间操时间到了,他照常要被物理老师拉过去到他的办公室训。
“余正夏,”裴老师来到他身旁,像蝴蝶扑扇着翅膀飞来再缓缓停到他眼前一朵小花的花瓣上,“帮老师改下上周三的古诗默写,好吗?”
“不好意思,老师,我没法去,”余正夏礼貌但不愉快地说,“我要去物理老师办公室……”
裴老师想,准是他在物理课上答不上来题,引起了宋老师的气愤和忧虑。她只是个初来乍到的小老师,不是荣誉加身的资深教师,更不是十六班的班主任,不然就能拿帮改卷子这个理由,把余正夏从宋老师那儿拉过来了。现在,她无疑失去了一个有力的小帮手。而二十班的金妍尔又是钦定好的广播室播音员,她现在正坐在广播室,裴老师同样也没法拐她归来给自己帮忙,。
“好的,那拜拜了,下次再找你。”
裴老师说着,收拾一张大卷子和一沓教案到帆布包里。
“老师再见。”
余正夏一直郁闷地想着待会儿宋老师的训话,无知无觉地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前,门边竖着块木质的门牌,上面刻着“高二第一教研室”七个不大不小的字。
“咚咚咚!咚咚咚!”他又长又粗的手指敲着木门。
“请进!”回应他的是教数学的林老师,声音兼具响亮与爽朗。
余正夏应声推门进去。眼前是副再平常不过的景象:教研室里放着六个圆桌,每个圆桌都被隔板分成了五个扇形,十几位老师或是对着自己电脑打字、翻网页,或是对着学生作业批改。他们间耐不住寂寞的几位,时不时讲上几句话。除了圆桌,教研室里还有几个大大的灰色铁柜。不用想,里面都是全年级一千多名学生的噩梦:寒假作业,练习题,小测卷子,应有尽有。
“是你啊,余正夏,”林老师见到了还算熟悉的身影,冲着他一笑,“裴老师在隔壁,这都高二了还走错呢?”
“是宋老师找我,”余正夏巴不得自己真的是找裴老师找错了教研室,“他——”
“——明白了,我才想起来,我听你们班主任说了。”林老师生生让余正夏咽下了剩下的话,“他现在没在。祝你好运啊。”
“谢谢老师。”
余正夏把身子挪到另张桌上宋老师的位置附近,准备好了挨训。
“余正夏,全年级文科的物理,就没有像你这么差的……”宋老师正式开始语重心长的训话。
“各位同学请注意,各位同学请注意,”金妍尔的声音由广播室传出,又被风吹到操场上空,“有哪位同学拾到了高二一班冯昌磨的白色钱包,内有饭卡一张,请速送到广播室。有哪位同学拾到了高二一班冯昌磨的白色钱包,内有饭卡一张,请速送到广播室。”
“……你忘了上学期期末物理你考倒数第三了?”此时此刻,教研室里的宋老师则脸色铁青。
“好,现在开始做操。”
金妍尔话音落下五秒过后,包围操场的几个大扬声器就齐刷刷地喊道:
“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青春的活力》!”
秋常市各中学的广播体操一直都是统一的。这套统一的广播体操,以前是《时代在召唤》,过了几年就换成了《青春的活力》,没过几年又换回了《时代在召唤》,到五年前,又变成了《青春的活力》——全新编曲的版本。
“预备,起!”
操场上,学生们大都无精打采,勉勉强强跟着节拍,原地踏步。
“……你说你,到时候会考都及不了格,领不到毕业证,就算清华美院真给你发证了,又有啥用?”宋老师还在用他厚重的男音说教着。
“危安她又在快乐做操吧。”
余正夏眼神迷离。他低着头,貌似是俯首认罪,其实是在随便想些跟训话无关的,想什么都好。
“三二三四……”
大家一凑在一起做课间操,危安就显得特别醒目和突出,很少有人能把广播体操做到她那种境界:用尽了力气,旁人却不知她是在认真做操还是在敷衍行事。说是在认真做操,一套操从头到尾,哪个动作都做不到位;说是在敷衍行事,所有这些做不到位的动作,却都透出一种作不了假的力度,跳操结束,她的两颊也常常微微泛红,像个闷实的大红苹果。每回做完操,她都一副乐在其中的模样,不像绝大多数同学,会纷纷摆出仿佛刚上完坟的面孔。因此,言道明管这叫快乐做操。
“你就是太把自己那点所谓的特长当回事……”宋老师一个劲地说,就是说不厌。
“稻子是不是又要累趴在操场上,提前给他叫个120吧。”
余正夏眼前浮现出言道明每天间操后的样子:明明整套操下来都没怎么动,音乐结束了,却一个劲地说自己多么多么累,逮到谁跟谁讲。讲完自己累,还要接着讲间操多么多么没人性,躲查间操的多么多么辛苦,仿佛间操可以夺人命。翻来覆去,句式会改,可内容总是这么几句花样,余正夏他们三个听都听烦了,比宋老师说话还烦。
“……你们这种特长生进来的我见多了,”宋老师的喋喋不休是停不了了,“我进学校,就没见过什么艺术生啊、体育生啊,有正儿八经上个好学校的,上旁边秋常工大的都少……”
余正夏想,宋老师要是真的认识到,这两年的特长生都是经过学校严格筛选的,肯定会为自己的无知惭愧到无地自容。余正夏本人就是个好例子,他考省实验特长生的时候,学校设置了静物色彩、半身像素描、照片速写、文化课划线等重重关卡,九十几个学生报名,被放进来的就他一个。这么招进来,就算三年间画画得再怎么一塌糊涂,也不至于只能凭艺术生身份走个省里一般般的普通二本。
不过,余正夏自己却觉得,被这么招进来并没有任何好夸耀的。臧晓宇是省内短道速滑的青年翘楚,还获得过全运会奖牌;据道听途说,郭冰舞报的表演特长生,是三百里挑一;鞠家三姐妹拿到的艺术体操奖杯、奖状、奖牌,更是加起来能满满摆上一屋了,还不算上小妹纱来的花样游泳奖项。余正夏搜过三姐妹的名字,一点进百科网,他就被长长的奖项列表吓到了。比起来,自己只有相对来说不难拿到的全国小学生儿童画比赛二等奖、全国素描比赛少年组银奖,以及一些市内的画作展出经历,简直可怜得要死。
“宋老师,外面有人找您!”间操落幕时,林老师的声音再次响起。
“今天先放过你。”
扔下这句话,宋老师便大步流星迈出教研室。
“老师再见。”
余正夏对宋老师说完这四个字,又对林老师说完,便轻快地离去了。解脱竟来得如此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