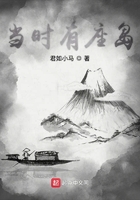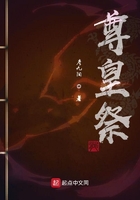第六回红梅楼英雄试剑,忘乡阁孔雀归心
不说那大汉出门离去,这楚江寒听了那大汉之言,正沉思间,任公子却张口了:“平日拜会姑娘不得,今日沾我楚兄之光幸得一见,怎奈不才无福,没能为姑娘奉茶,特为姑娘送些点心,还望姑娘赏脸!”言罢折扇一挥,竟将桌上一盘点心连同盘子,抛向那红衣姑娘。楚江寒兀自怒起,这任兄怎么一再向这位女子过不去?
只见那姑娘一个转身,分明使了个身法让过,那盘子竟有半边插入红柱,却是半点没碎,点心四溅,早把那些个吹拉伴奏之人,惊个屁滚尿流,抢入后堂。
那姑娘身子晃过处,手中竟多了一条软鞭,亮蹭蹭如手指般粗细,早向任公子飞来,“啊,是了,前翻分明见过这姑娘身手”未及多想,早见那任公子抽出腰间宝剑,纵身一跳,向那女子刺去,那女子挥鞭就打,出手间却是招招狠毒,招招凌厉。
楚公子吃了一惊,真不想如此狠毒的女子,也有方才那般美妙的歌喉。但见二人一个舞剑,一个挥鞭,一来二往已过了十几招。楚江寒心道:这女子鞭法如此狠毒,若是教我遇上了倒是得仔细应付了,不过,凭我使出丹阳剑法来,倒也不难破她。再看那任公子剑法丝毫不乱,闪跳转挪出剑忽上忽下忽左忽右,若非日日苦练,哪里能有这般功夫?
那女子眼见一时不能取胜,手腕一抖,那软鞭好似银针一般向着任公子心口飞来,只见任疆不慌不忙,把个手中宝剑望胸前一挺,手腕也是一抖,那软鞭便缠在上面,任公子深吸一口气,身体微微下沉,气走丹田,臂上使力,那女子也是后腿微曲,把水蛇腰向后为沉,二人各自使劲,比起内功来。
一时胜负难解,楚江寒但听得那女子身后淅淅嗖嗖,暗叫不好,果然人影攒动处虹光一闪,紧接着便是一声剑吟,一把宝剑向任疆刺来,任公子正屏住呼吸全力比拼内功,高手过招,哪里还有余力应付,若有半点分心,稍有差池登时便败,轻则重伤,重则落个终身残废。任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心道:想我宏图大志未得施展,不想却要在此间受挫,时也命也!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又是噌的一声剑吟,一道白光闪过,任公子是觉得臂上千钧之力顿时化为乌有,身子竟向后飞去,正欲再使个千斤坠的功夫定住,早已来不及了,立时向后,倒在地上,再看女子,也是跟自己一样,向后飞出一丈有余,倒在地上。紧接着,半截金钢剑坠地,一颗人头连着半个肩头,飞过来落在场地中间。
任疆惊魂未定,向上看时只见那楚江寒,手提一把宝剑,早就跳了下来,原来是楚江寒出剑,不但分开自己与那贱人的缠斗,而且也杀了背后偷袭之人。
任有为暗想:我这配件也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好剑,如何就被他轻易砍断?看来这宝剑,果然名不虚传!却连忙翻起身来丢了手中残剑,双手抱拳说道:“亏了楚兄解围!”未及楚江寒开口搭话,人群中早惊出几个大汉:“看!镇岳剑!”
“怕他奶奶个鸟!我看大家齐上,各使刀剑剁了他狗日的,把宝剑抢过来!”
“不错,今日他休想活着踏出此门”
再看那女子也翻起身来,丢了半截银鞭,只是轻轻一挥手,早跳出四个大汉,各自提剑,将楚江寒围了起来,这四人却是一样衣着,左腿微微向后一迈,连起势连同手中宝剑,都是一样。那楚江寒却将宝剑入鞘,双手抱拳,说道:“在下实在不想伤人性命,就此别过!”
那四人那容得他走,竟是同时大喝一声,四道剑芒从四面袭来,但见得寒光一闪,“叮”地一声,四把宝剑应声而断,紧接着四人轰然倒地,众人看时,那楚江寒复又提剑在手,宝剑之上,却无半点血丝。这样一来,众人却是惊了:这少年剑法却是到了惊世憾俗的地步了。一时间鸦雀无声,哪个还敢近前来?
却说出剑寒提剑在手,初始没觉得什么,等到这里安静了,又看到地上那一片红流,不由得慌了神,他自幼在山中学艺,师门中人教他武功之时,就告诫他上天有好生之德,万万不可滥杀无辜,不想今日两次出手,就连伤五命,且这五人与自己无冤无仇,更无从得知他们有何劣行恶迹。想到这里,不由得后背发麻,手心冒汗,那提剑的右臂,竟然不听使唤,抖了起来!
这么一抖,可就吓坏了众人,都认为已经惹怒了这位宝剑在手的高人,照他的身手,再加上宝剑在手,如若杀将起来,在场的恐怕没几个能活命!众人都是各自按剑在手,却又没人敢上前来。
突然从后面蹿出个人来,任楚二人看时似个跑趟的,对那女子附耳言语了几句,楚江寒正要用功听时早已经说完,那女子略一停顿,随即又说道:“二位,今日之事,咱们日后再算,二位请自便吧!”人群中随即分出个口子,任疆双手抱拳淡淡的道一声:“告辞!”便迈大步要走,楚江寒心下疑惑,却又一想,如若再待下去,真不之如何是好,也不多想,手中宝剑归了剑鞘,跟着出来了。
二人出了楼来,走了有一会,楚江寒实在忍不住了,开口问道:“那女子究竟是何人?”
任疆开口道:“这女子江湖人称‘玄衣孔雀’,却是白莲教中的人物,轻功极顶,心狠手辣,任某手下有好几个兄弟,都被她斩手的斩手,挖眼的挖眼。”
楚江寒听了一震,那任疆又道:“此楼楼名为红梅楼,平日卖酒唱曲,却是白莲教的秘密联络点之一,我暗中观察已久。白莲教在蜀中杀官造反,百姓苦于战火,流离失所,凡我英雄之辈,在当为武林,为苍生,杀尽这干恶魔!”
楚江寒方才还为杀人之事介怀,此刻听闻这一伙具是白莲教妖人,杀他几个,算是为天下除害,遂不复多想。
任疆又道:“楚兄可有胆量回去?”楚江寒心下纳闷“回去?”
“正是,楚兄不必多问,要有胆量,跟来便是!”出完纵身一跃使开轻功便往回赶,楚江寒哪来的及多问,也使开轻功跟了上来,二人何等身手,没有多时,表早已来到原地,这回二人却是没有进去,而是趴在屋顶通风窗口,向下望去。
只瞧见地上又多了七八个死尸,有四个大汉站在他二人方才所站之处。四人也是一样打扮,其中一人张口道:“爷再说一遍,爷们四个都是锦衣卫办案,识相的交出‘玄衣孔雀’,爷四个只管拿人,别的一概不过问,如若有人作对,爷调来人马,后果怎样,你们自家掂量!”
“锦衣卫?”楚江寒心下疑惑,“这锦衣卫是皇帝直属,具由高手组成,怎么也会朝廷插手江之事?看来这女子定时白莲教无疑了”正自疑惑间,又一个粗狂的声音道:“废他娘什么话?老十九,放响箭叫人!灭了他狗日的!”
一声“且慢”,正是那女子“我跟你们走!”只见她又丢了手中一条金色长鞭,走上前来,早有二人拿了锁链,将那女子手上脚上拷了个结实,那链子足有手指粗细。那女子又是一挥手,人群中又让开一条路来,四人各手持一端,哗啦啦走了出来。
任疆一个翻身下楼,楚江寒也跟着跃下,楚江寒疑惑道:“此楼既然是白莲教的地盘,这魔头怎会束手就擒?”任疆哈哈一下,说道:“楚兄外行了不是,如若那四人当真叫来帮手,这楼里诸人如何逃脱,即便逃了数人,这白莲教岂不损失大了?这妮子假意束手,待锦衣卫离开,这干人立马撤离,回去找来高手,再行营救,我敢打赌,这妮子一路之上定然要伺机逃跑”。楚江寒点头称是。
任疆转过身来,对楚江寒说道:“楚兄,兄弟认为,你我应该紧随其后,如若她要逃跑,或者有高人来救,你我好趁机除掉一二妖魔,也算是除害,楚兄意下如何?”楚江寒听完大喜,自己一身本事,不就该用来行侠仗义,为民除害吗?若当真遇到几个白莲教魔头,倒要他们尝尝小爷手段。于是允了任疆,二人不近不远,不慢不快,是尾随其后。
转眼行了四五日,一路之上这几人却是白天赶路,夜间投宿,专门往那气派处进出。沿路只见四个大汉,各执铁链,锁住一个女子,路人无不私下议论。这天晌午,这几人来到一处地方,前不着村,是后不着店,唯有官道旁边,缺却赫然耸立一栋楼来,眼见几人登楼,任、楚二人早是腹中饥渴,左右没有去处,只得近前来。
只见一块金匾浩然三个大字“忘乡阁”两边一副对联映入眼幕,上联曰“路通南北,东西客门前下马停步”下联曰“楼锁往来,今古人阁上举杯忘乡”。
二人也不迟疑,入得店来,这店倒也奇怪,楼下都是客房,唯有楼上却是空出来,为客人饮食之处。
二人只得上楼来,只见那四个官差早就要了酒饭胡吃起来,那女子却是坐在地上,四条铁索各捆了手脚,另一头却拴在四个官差腰间。
地上乱丢有七八个馒头,旁边放个坛子,里面不知是酒还是还是水,那女子胡乱抓起地上的馒头,就往嘴里送,楚江寒这回可瞧清楚了,一双丹凤眼汪汪欲滴,一张白皙的脸蛋儿上虽然早有污渍,却也美的实在使人舒服。
楚江寒怎么也不相信,这样标致的人儿,却是响当当的魔头,初见时的玄衣虽然换成红衣,叫她“玄衣孔雀”,但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二人也要了酒菜,楚江寒再看周围,具是一干江湖中人,各个佩刀携剑,有俗有僧有男有女,楚江寒用心一听,这帮人虽然各自吃喝,却是呼吸沉稳,一看就是江湖中的高手。不一时酒饭来了,二人早已饥渴,也不管这干人,胡乱吃喝起来。
忽然听一个结巴说道:“七哥,要......要不,咱们赏......赏这骚娘们点吃的,回头饿......瘦了,咱们几个,面上也......也挂不住。”说完端起桌上的一只烧鸡,向那女子扔去,那女子随手接过,丢了手中的馒头,啃了起来。一个粗狂的声音说道:“老十七,快吃,吃完接着赶路!”四人不再说话。
正在此时,楚江寒听得两个人上来,脚步轻盈无比,只怕是座上诸人没几个听出来,回头忘楼梯口瞧时果然有两个汉子走上来,打头走的一个手里竟然提把金灿灿的大刀,下颚留了胡须身材略胖,身上衣着干净华美,径向那女子看去。后面跟着一人较前面胖些,后背个木盒子,一掌见宽,四指来厚,盒子上方有一个木质的剑柄升了出来,一看就是把不知名的宝剑,二人红光面面,向着座中打量,径直二人走向右角落唯一的一张空桌子上坐下。
未及小二上茶,提刀的汉子走到那几个锦衣卫面前,开口说话:“各位兄弟请了,我二人乃是京城的捕快,承蒙各方朋友抬爱,唤作个‘金刀’‘木剑’。”
此言一出,座中立马炸开锅了,这楚江寒却当真没听说过,没等开口来问,任疆说道:“这二人原来是名震京华的捕快,近十年间,这二人捉拿盗贼处理大案,总是手到擒来”。
一言未毕,那提刀的又说道:“今日我二人向四位兄弟讨个人情,放了她如何?”
那四人登时发作,“笑话,我们锦衣卫办案,哪容得别人插手!”此语一出,座中诸人登时倒吸一口冷气,江湖中人,对于锦衣卫,向来避之唯恐不及,此刻有胆子稍小的竟看也不敢看一看,只顾埋头吃喝,生怕招惹了这帮瘟神。
只见一个粗狂的声音说道:“二位总捕头,你们办你们的案子,兄弟四人也各自有任务,再者说了,这镣铐唤作‘缚妖索’,刀枪不惧,钥匙在我们老大手上,只怕我们有心放,二位捕头也打不开,啊,哈哈,哈哈哈!”紧接着是其他三人附和的笑声,教人听了好不舒服。
笑声未毕,那身后的汉子却从后背缓缓抽出一物,三指见宽一指来厚,这哪里是什么剑,分明是把木制的戒尺!只听得一阵噌噌声响处,那女子手腕脚腕上的镣铐啪啪落地,再看那人,手中之物,早已放回匣中!不单是座中诸人吃了一惊,楚江寒更是大骇:“凭我手中旷世宝剑使出丹阳剑法,或许可以办到,这位捕头竟然用这样一把木制的没有锋刃的‘剑’,轻描淡写间,居然做得到,但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众人还为缓过神来,“玄衣孔雀”眼见脱得镣铐,双脚点低使了身法拔腿就跑。
那“木剑”说声“我去!”,赶后就追,楚江寒看的出来,这“木剑”剑法虽好,轻功可就照这魔头差远了,以自己的“须弥三引”若要追上,也得废些功夫!
那几名锦衣卫只气得大跳,拔刀便要打杀,忽见那“金刀”左臂一伸,立在原地不动了。那几名锦衣卫面上先是一惊,又是各自收刀,转而面面相觑,各自摇头,继而齐齐抱拳,道了声“后会有期!”竟然下楼去了。那“金刀”也是纵身一跃,追着二人而去。
楚江寒来了个丈二的头脑,一时摸不着头脑,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任疆却道:“楚兄,江湖上有种武功叫作‘传音入密’?这种功夫能以内功传音,而不被人发现,想来刚刚那位捕头,定然是用了这种功夫,对四人说了什么。”楚江寒心下随有疑惑,却也无从得解,只得埋头吃喝。
坐上复又归于平静,各个虽然相安无事,却是心中疑惑。转眼间饭吧,二人正要起身,楚江寒却对任有为说道:“且慢,那位魔头又回来了,是三个人,嗯,还有两个娃娃,奇怪了,她怎么和两个娃娃一起,又回来了?”任疆知道对方功力远胜自己,心中大大不悦,也没多言。
只见楼梯口奔奔跳跳上来一个孩子,七八岁左右,口里念道:“爹,你们快点,我都饿了”,紧接着上来一个汉子,粗布烂衣,手里抱个女娃娃,跟前面那个男娃娃一模一样,那汉子却道了声:“上来!”
人群中立时骚动起来,“玄衣孔雀”竟然跟在后面,走了上来。
那小男娃早就走到右边干净的空桌上,手里拿双筷子,在自己袖子上擦了又擦,摆在中间,那汉子过来坐下,没等张口,那小娃娃早就说道:“小二,拿二斤肉来,再要一盘烧鸡,二十个馒头,再来十斤酒,我爹要喝酒!”那小女娃在那汉子怀里接了一句:“还有三个碗,不对,是四个碗!”小二在一旁也不搭理这俩娃娃说啥,这汉子张口道:“上吧!”小二依言而去。
那汉子转过身来,对“玄衣孔雀”说了句“你也过来坐下吃饭!”
众人看时,那“玄衣孔雀”只是呆呆地站在一旁,哪敢坐下!
楚江寒正字诧异:凭我的功力,又离得这么近,怎么会听错呢?
再细看那汉子虎背熊腰四生方脸,虽然不高却是雄壮异常,宽下巴大耳垂,额上竟有一道一指来宽的疤,也看不出是被什么兵器所伤,那疤不偏不倚,映在额心,活像庙里的二郎真君!这汉子不是别人,正是当年登丰楼题词的张继张承文。
楚江寒心下疑惑:这汉子到底是谁?这“玄衣孔雀”刚刚逃走,怎么又会跟此人一起回来?
任疆说道:“楚兄,还记得当日一同听曲的那汉子吗?”
“是他?”楚江寒惊道。
任疆道:“楚兄莫要多言,看着便是!”
楚江寒依言看时,只见那女娃娃说道:“姊姊坐下来,我们一起吃好不好?”那魔头闻言先是一震,继而又缓缓坐下。
不一时小二端上来酒饭,那小孩先是吃了几口,紧接着只是不住地给倒酒,那张继也不说话,满了就喝,再看那女娃娃,不住地往那女魔头碗里夹牛肉,那女魔头,把个头低的就像刚过门的村妇,使人看来倒也想笑。
突然那男孩一阵咳嗽,原来是被呛到了,张继手起就打了一下,只是重也不重响也没响,转头训斥道:“小娃娃家,喝的什么酒!”
正在这时,那“玄衣孔雀”突然使了身法,离弦的箭一般轻轻弹起,飞向栏杆之外,楚江寒心下暗暗叫好:这一身轻功我是见识过的,可若是没有深厚的内功,倒是很难使出来,这“玄衣孔雀”也当真了得。
只见那张继回过头来,不慌不忙,伸出右手来,缓缓推去,细看之下原来那汉子右手竟然没有无名指和小指,只见他把个残掌向外一翻,往回一拖,三丈之外,“玄衣孔雀”竟如咬钩的死鱼一样,轻飘飘的回来了,不偏不倚,正好到坐在原来的凳子上。
座中鸦雀无声,惟有张继缓缓说道:“杨姑娘,今后就留在我身边,照顾我这两个义子义女。”那男娃娃却张口抢道:“不对!不是义子义女,就是子女!”那张继闻言,原来一本正经的脸上,扬起了笑容,又哈哈大笑,端起碗来一饮而尽!饮完张口说道:“转过来吃饭!”
那“玄衣孔雀”转过身来,一个跺脚,然后将面前的碗摔个稀碎,紧接着挽起袖子来,坐着不动!只把诸人看了个目瞪口呆,稀里糊涂。
真是:世上从今无孔雀,
鸳鸯侠侣始初成。
何出此言呢?后文自有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