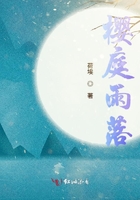“地皇十五年七月十二日,晴。”
“无需我过多劝说,弈默默地踏下山顶,走回山洞。”
“听到明日将要前往都城这个本属于他曾经梦想之地的消息,他并未表现出任何惊喜,只是轻轻的‘哦’了一声。”
“但我知道已经无需再为他担忧半分。”
“因为此刻洞内传来他熟睡的鼾声,十日来,他终于再次睡得如以往般香甜。”
“而这应该也是我在邙山的最后一次日记。”
“我想,自明日离去之后,我将不再归来,如果一定需要,那我也必须是以另一种身份。”
“是的!必须是另一种身份!”
“有些经历,无需太多,就能让人刻骨铭心。”
“在这将近一月的日子里,我熬过了生不如死的病痛,我体会了胜似亲情的友情,我经历了仿若炼狱的劳作,我明白了更为深刻的道理……”
“奴隶的悲惨命运,并不在于身体的疲惫,而在于内心的煎熬。”
“他们也有思想,但他们并不会归纳思想,处理情绪,他们只会将所有的情绪深埋心底,直至生命的终结,就比如卞,再比如菱……”
秦萧费力地刻到此处,停下手中的动作,望向洞外。
两轮皎月相伴而出,跃于东方,对初次得见的他来说,呈现出一种至美至奇令人深感震撼的独特景观。
淮南子星有两颗天然卫星,这在他前世看过的报道中早已知晓,但真正亲眼目睹,还是不免让他一时沉陷其中,难以自拔。
就此好一会欣赏,他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接着先前的思绪继续刻画。
今夜的他,实在没有更多时间去留恋美景。
“因此他们需要的是情绪的发泄,因此看到弈今日的转变,我感到莫名欣慰。”
“但并非每个奴隶都会如弈这般幸或不幸,他们脆弱的生命也未必能承受如此大的打击,他们需要一种正常的方式,循序渐进的慢慢引导,直至最后情绪释放。”
“加缪说:奴隶开始要求正义,但最终则要求王国!”
“今日,我终于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
“于这个时空的奴隶来说,他们此刻需要的并非是围棋,五子棋,麻将,再或其余的任何开发智力的游戏。”
“他们的思想远未达到富贵之人般的那种登高望远的境界。”
“他们的要求很简单,情绪的宣泄,只有当他们慢慢懂得了情绪究竟为何物,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想法,更高的追求。”
“挣扎于温饱之人,又何谈精神享受?”
“可笑的是,身为一个后世之人,我居然直至此刻才完全想明。”
“跨越性的发展总会有其弊端,就比如菱,她无疑属于采石场难得的与众不同而玲珑剔透的女子,但她还是死了,在她去到那个充满魑魅魍魉的都城的第二日,再或第三日,她选择了死亡!”
“她经历了什么?这些已经不再重要。”
“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奴隶,该如何在看似繁华,实则复杂的闹市夹缝求生?”
“菱选择了高尚的死去,那我呢?”
“该委屈求全的苟且偷生,还是如菱那般摆出自己的至高尊严,无言的反抗中静默死去?”
“我……”
今日的刻画可以说是秦萧近月以来的所有总结,字迹的过多,让他完全无法再如以前般深深刻印,而当他潦草简洁地刻到这时,他忽然停下手指,屏息凝气地倾耳听去。
洞内弈的鼾声越来越响。
洞外——
此时应该已到子时,洞口的两轮明月已经往上攀升,消失不见,就连先前此起彼伏欢唱不断的夏虫夜鸟,也已经沉寂下去,四下里静悄悄的一片。
而在这种四下的寂静以及弈的鼾声中,他又似乎听到了洞外脚步与碎石摩擦的窸窣之声。
是谁?
秦萧睁大眼睛瞧着洞外皎洁月色下的一方天地,静待来人,心脏却不争气的陡然“砰砰砰”加速跳动,一种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
“谁?”伴随着窸窣的步音突然停下,沈雄的轻喝立即传入洞中!
原来是他!
秦萧心中疑惑得解之际,再听到一声轻嗤响起,接着另一把懒散的声音飘入耳内:“沈老弟何必如此惊慌?”
“是你?!”沈雄惊讶的失声低呼,接着松了口气的轻呵一声,询问道:“封兄何以在此?”
听到问话,秦萧忽地莫名心悸,对方究竟何时到来,自己竟然丝毫不觉。
那人发出淡淡的笑声,懒洋洋的话中带着几许嘲弄,“沈老弟竟然问出此话,可见来此并非与我心意相通,而是另有目的。”
这话乍一出口,不只沈雄,就连洞内的秦萧刹时也是听得满头雾水,不知他所谓的心意相通究竟所指何事。
而在这短暂的疑惑片刻,那人已是啧啧有声的转而感叹道:“沈老弟难道不觉得这邙山的夜景与雍都大为不同?”
说着呵呵一笑,也不等对方作答,自顾自的再道:“封某见今夜月色怡人,更是难得的双月同辉之景,便起意来这山际好好欣赏一番,却不知沈老弟又是所为何事?竟大半夜的不顾险阻,爬至此处。”
“原来如此。”沈雄恍然大悟的干笑几声,解释道:“其实我亦如封兄这般所想,故而有心登山一览。”
“哦?”
那人诧异的轻哦一声,旋即语含欣喜的邀道:“既如此,沈老弟不妨过来与封某共赏美景。”
对他的盛情邀请,洞外静默片刻,然后沈雄忽地发出极为勉强的笑声,似乎很怕靠近对方般的明显推拒道:“我忽然想起明早临走在即,却仍有一事尚未办妥,唉……”
叹了口气,惋惜的续道:“看来我实在与这美景无缘。”
“是否?那真是可惜。”对方替他满是遗憾的言罢,又叮嘱道:“月色虽明,下山路滑,沈老弟还需多加小心。”
“多谢提醒!”秦萧能明显感觉到沈雄那几乎是咬牙切齿勉强迸出的道谢,接着再听到他反唇道:“封兄稍后下山亦务必多加小心。”
那人淡淡一笑,散漫道:“沈老弟不必挂怀,封某今晚准备歇在此处。”
此后洞外再无话音。
片刻,沈雄那显然心情不佳的“唰唰”步音再次响起,渐渐远去,直至不闻。
秦萧松了一口大气,知道今晚可谓是躲过一次大劫。
沈雄深夜前来,其意不言自明,而从傍晚的对话来看,恐怕更有那什么表少君私下授予之意,如此,他的处境就陷入了刚才所思考的那种局面,到达都城,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
思索间,一个身影悄无声息的出现洞口,遮住洞外皎白的月色。
秦萧收回心绪。
“你可知沈雄方才为何而来?”对方就似知道他没睡般朝洞内踏了进来。
秦萧暗自一叹,坐起身道:“不知!”
对方来到他身前不远处停下脚步,黑暗中眼睛犹自闪闪发亮的将他注目顷刻,不无讥讽道:“大丈夫处身立世,若连最基本的危险都察觉不到,死亡对你来说,不过是早晚之事。”
“我并非什么大丈夫,我不过是一个奴隶。”秦萧回答得果断而极其光棍,又令人无可辩驳。
“奴隶?”那人似有似无的哂笑一声,似乎并未将这个身份放在心上,只是诘问道:“就算身为奴隶,难道便无需安身立命之法?”
对于这个问题,秦萧自然选择闭口不答。
眼前之人或许对自己并无恶意,但他只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奴隶,容不得半点错误,因此他绝不能对旁人轻易表露自己的心迹。
见他默然以对,那人无可奈何的微微一叹:“我能护你一时,又能保你一世?”
“多谢封……”
秦萧想起方才之事说着顿了一顿,接口道:“多谢封执事维护,不过我只是一个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奴隶,封执事若觉厌烦,大可视若无睹,无需如此烦恼。”
那人显然拿他的这种态度毫无半分,却也竟未气恼的拂袖而去,闻言只是无语片刻,没好气道:“我叫封不寒,并不拘泥于任何称呼,你尽管随心便是!”
封不寒!
秦萧默念一遍记下名字,想到明日之后将要面对的或许就是龙潭虎穴,若是将他之话当真,完全不知尊卑,那才是真正的不知死活。
封不寒对他的态度与沈雄截然不同,见他再度默然,反过来像个话痨般的没话找话,询问道:“那首诗歌真是由你所作?诗名为何?”
“《蒹葭》。”
秦萧收拢思绪回答后强调道:“那并非由我所作,我也不过是从别处听来。”
封不寒静了顷刻,悠叹道:“我倒真希望是由你所作。”
言罢在他难明其意的错愕中转身离去,边走边道:“时辰不早,明日还需赶路,你也早点歇息。”
瞧着对方消失的身影,秦萧陷入思索。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人!他对自己的态度实在有点令人难以捉摸。
不过这似乎又很好理解,对方应该是位极有使命感之人,为了主君的托付,对自己多用上点心思亦无可厚非,更何况最初他还认为自己会作诗。
在这个时代,作诗代表什么?
代表着一个人的素养、品质、甚至地位至少位列于阶层的中上端,对待这样的人,难道不该表现出稍微的亲近?
这从对方得知自己不过是听来的诗歌之后便再无谈兴,亦可窥见一斑。
秦萧很为他的这个解释感到合情合理,而就在他想通此事之际,洞内忽然传来弈的沉声低语:
“萧!我要杀了他!”
专心关注洞外的秦萧压根没有注意到他究竟什么时候醒来,又到底听到什么,甚至被他这突兀的一声吓了一跳,直至回过神来,立即明白他所指的“他”究竟是谁。
对弈来说,带走菱的沈雄无疑是罪魁祸首。
而十日以来从未开口的弈,甫一开口就说出这样几可说是惊天骇地的话语,秦萧微感诧异之余,剩下的尽是欢喜,因为这才是一个“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情绪。
是的,弈的脑海里此时同样没有什么大是大非的观念,但他至少有了明确的爱憎,这就够了,因为这就是人的最基本情绪。
秦萧不能不为对方的这种转变感到欣慰,于是他在短暂的惊诧过后,坚定的回了三字:“我帮你!”
“萧!谢谢你!”
印象中,这似乎是弈对他首次郑重言谢。
在以前,那个每次提到“谢”字就腼腆的弈,那个就算当初帮他追求于菱也觉得理所当然的弈,第一次道谢,竟是为了杀戮之事,这不免让秦萧暗生感慨。
而弈说完过了小会,情绪似乎有点亢奋却不知如何表达般的投桃报李道:“萧!你是否有想杀之人?我也帮你!”
“我?”秦萧闻言顿了顿,接着说出这个时空或许无人能够听懂的话语——
“我想杀了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