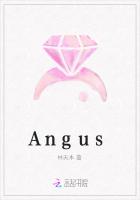要搅和进去,并搅得一团乱,连睿智如凤承天都无法看出且无力改变,着实是件难事。
风裳想着,第一步需得找到严华才可。
但她如今腿脚不便,身边又无照料之人。
西内苑中尽是些魁伟男儿,皆不宜来照料她,她该如何取得与严华的联络?
眸光穿过简陋木窗,绕过随风扬起的落英,是院里一小池塘,塘里飘着几片略小的荷叶,如扬州雨下撑起的油纸伞。
风裳想到了苏荷。
今日凤承天之所以提到应惊鸿,不过是因严华精神恍惚,误会了人。
但严华精神恍惚的缘由却是那位家中爱妻。
想来昨日苏荷归府后状态依旧不好。
风裳决定想法子见一面苏荷,拿下那位,便是拿下了严华。
她秉着凤承天大抵不会饿死她的念头一直等到了傍晚时分,塘里响起青蛙的咕咕声,一身着宫装的太监走了进来。
他一手提着一雕镂精致的竹制食盒,两三层模样;另一手提着几贴似是装好的药草,朝风裳走来。
待走近,太监恭敬行了礼,把食盒与药放到了风裳床边位置。
“禀大人,唐总管命奴才将食物与需煎的药给您带来,唐总管道,您若还有何需求,便告诉奴才,奴才回去禀报给唐总管。”
风裳打开食盒看了看,皆是些清淡小食,无甚昂贵菜肴,倒是符合那位送油菜花煮面的帝王性子。
她摆摆手,道:“无需你传话于唐总管,只消帮我做件小事即可。”
小太监愣了愣,畏缩着看向风裳。
———
三壮牵着西内苑马厩中刚产出几月的小马驹在长安街头走着,心里还着实郁闷。
他军龄几年,怎么就能被一个刚入百骑的黄毛应尚几句话给忽悠了呢。
他又望了眼闲适坐在小马驹上的伤残人员,便更加郁闷。
都只怪他鬼迷心窍。
因着报效国家的愿望,早年便入了兵籍,辗转于各个战场,前年离了应将军,自凉州来了长安,便在北衙百骑中留了下来。
家中多年一直催促归家成婚,他却未当个回事。
如今年纪渐长,仍无所建树,心中孤寂下便是生了成家之念。
只惜家处穷山僻壤,与繁华都城相比实在所差甚远。
人都道过惯了好日子,那穷苦便是万分再受不得。
见得了锦绣繁华,茅屋粗茶便入不得眼。
他想着不若就在长安找个媳妇儿,在城角处房屋卖价便宜的普宁坊买所小屋,过个小日子,不也惬意?
只可惜大都城,繁华之下,物价也极贵,城中女子又多是嫌贫爱富,都道你无房便不跟。
拖着拖着,他到现在便也还是没娶个媳妇。
直到昨日应尚不知从哪里差了个小太监找他,说让他去马厩中偷匹小马驹,带他去严大人家转悠一圈,他定能给他忽悠个俊俏媳妇儿。
他当时一乐呵,头脑发热便应了。
但如今反应过来,三壮觉着自己还不如把偷来的马驹卖掉换钱比较划算。
应尚这厮军龄没他高,在北衙中常受欺负,如今更是成了大长公主的眼中钉,更别说他自个儿不也没娶媳妇呢吗?
又怎来替他忽悠一媳妇儿?
三壮越想越不是滋味儿,所幸走到一家酒肆前便停下不走了。
风裳本端坐在小马驹背上,认真想着如何才能安抚苏荷,进一步让她放下防备,帮她劝服严华。
不料三壮倒先罢了工。
“怎般?三壮老兄难不成不要媳妇了?”
三壮一屁股坐到酒肆檐下的青石台阶上,哼哼嗤嗤着对她翻白眼。
鉴于三壮白眼翻得太过吓人,风裳索性指指酒肆,道:“不若老兄进去沽两杯,应尚请客?”
三壮抬头望了风裳一眼,又继续对她翻白眼:“且不说你半年的月供方被罚,就论之前数次你往西市沽酒的银两哪次不是从我这里借的?前几次酒钱你都未还我!”
风裳嘴角微抖了抖,扬手一指,豪气道:“‘解我紫衣裘,且换金陵酒。’三壮你进去,斗酒十千应尚我亦请的起。”
说完,她便将自己百骑军中象征身份的青铜鱼符解了下来,丢给了三壮。
三壮丝毫不顾忌风裳窘境,捡起那鱼符便朝酒肆中走了进去。
风裳朝那急遽步入酒肆的欢快背影心痛大喊:“三壮兄且记得帮我捎两壶蛤蟆陵的郎官清与阿婆清,我好带去予苏夫人!”
三壮不耐烦地招招手,背影已完全没入酒肆中。
酒肆外顷刻便只余了乘于小马驹上的伤残人士风裳,她望了望长安西市一条街,酒肆林立,青旗高悬。
各酒家青白相间的旗望随风拂扬,她忽然极想啜饮扬州纪叟酿的梨花春。
时季已过,且是难再回去。
小马驹停在酒肆外,踢踢踏踏着候着三壮。
风裳无聊,便听起了过往行人的闲聊。
不知是巧合还是因国祭此事确然引起了长安众民的注意怎样,周遭皆是对于此的热论。
三两过往行人沽了一较价廉的歇马杯,与友人坐在廊檐下议了起来。
“听闻此次国祭是应大将军负责皇亲国戚与众大臣的安保之事,前些日子归京他都未现身,此次国祭想来仍是要拒绝。”
“老兄说的确然有理,我听坊间传闻,应惊鸿恃功为傲,那日回都陛下与大长公主等一众尊位者俱要相迎,他竟是未出现。此回国祭安保虽听上去也颇为中听,但到底依旧是为皇家守卫的苦差事,无何面子,打了数次胜仗的应惊鸿怎会屈尊去干此事!”
“听兄台这般说,倒确然如此,应将军归都数日,一直闭府不出,不与人相交走动,实在过于倨傲无礼了...”
说话之人一顿,随即向四周看了看,接着作以手掩口状,垂了头,凑近友人,悄声道:“我甚而听闻,前些日子太尉安常傅亲自登门拜访,竟都被他的家仆请了回去,如今长安市民都道应惊鸿此人性乖张,不好处呢。”
风裳骑在小马驹上,手里已经掂着随身携带的小巧弹弓,思度着应该先打哪个欠嘴小厮。
当是先打说应惊鸿不好处的第三人,应惊鸿是怎般性格,他们连了解都未曾了解,竟敢在街头做如此私议!
且那以手掩口状做的无丝毫隐蔽性,她离如此远,都能听到。
这不是诋毁惊鸿么?
一、二、三...
待风裳将小荷包中的炒黄豆打出半包,这才收了手,安静等待着那三位酒客怒目圆睁、抡拳攘臂朝她快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