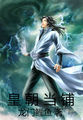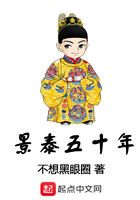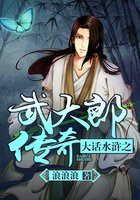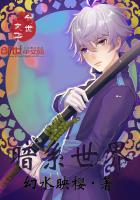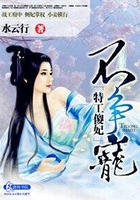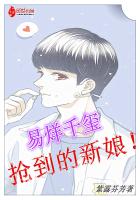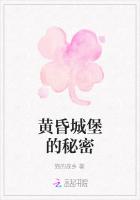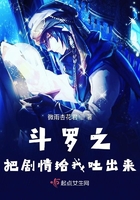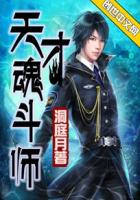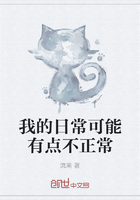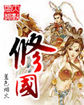此联嵌着“曾国藩”三个字。曾国藩一听,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哈哈,这个左季高,真不是吃素的。我不懂军事,缺乏经世济民的学问,你还不是纸上谈兵!还想反击一下,转念一想,酒席上的话当不得真。我堂堂一个侍郎,与他斤斤计较,倒显得我没有肚量了。
野史的含义,无妨见仁见智,各得其旨。左宗棠在务实人才奇缺的年代,对曾国藩才干的评价不高,其实是因两人之间知识结构的差异。这个段子,准确地表达了知识结构不同导致的认同障碍。
左宗棠和曾国藩在四十岁之前,由于经历和爱好不同,曾国藩务虚多一些,左宗棠则务实多一点。曾国藩以性理之学而闻名,潜心研究宇宙观、人性论和道德学,对于经世济用之学,他虽寄予关心,但比起痴迷此道的左宗棠,还是小巫见大巫。
左宗棠的知识结构比较新进。作为积极的务实派,他热衷于钻研应用科学,为此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他与曾国藩的学问有许多无法重合之处。而曾国藩作为清廷的二品大员,以文章道德享誉朝野,但在实用知识方面,不及一介布衣左宗棠,也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此刻曾国藩正在谋划建立一支新军,由于缺乏经验,非常谦谨地听取各方意见。左宗棠不仅劝说张亮基放手让曾国藩主持团练,还非常热心地为他参谋。
把湖南的团练交给曾国藩来主持,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决断。对于团练一事,曾国藩早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谋划。抵达长沙的第二天,他就拜发了一道奏折,陈述他关于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的设想。
曾国藩自从决定出任帮办团练大臣之后,便在考虑如何为团练乡勇闯出一条新路子。他一直揣摩圣意,发现当今圣上热衷于团练,是想照搬祖宗的办法,走半个世纪以前嘉庆爷的老路。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陕西与河南四省交界的地区,白莲教造反此起彼伏,声势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1799),清廷的绿营正规军已经招架不住白莲军。嘉庆皇帝启用古老的保甲制度管理城乡居民,并在此基础上团练乡民,组建民间武装。
嘉庆下旨之后,团练广泛兴起,民间武装竟然把白莲教打得无处藏身。三年时间内,白莲教基本肃清,大清帝国的国内政局,此后总算稳定了差不多五十年。
咸丰皇帝现在想起了嘉庆爷的法宝,想把各地乡民武装起来,在本地保卫桑梓,对付太平军的进攻。他认为,只要全民皆兵,太平军便会举步维艰,而且会失去兵员补充。为了这个目的,咸丰打算任命一批团练大臣,下令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和《坚壁清野议》,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
然而,曾国藩认为,嘉庆的做法已经过时了,若想打败太平军,照搬老黄历是行不通的。
嘉庆时代团练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官军野战部队,防止城乡士民与造反军勾结呼应,让官军作战部队没有后顾之忧,此外还能断绝造反军的粮食供应,给造反军攻城制造障碍。
当初的白莲教和如今的太平军一样,擅长流动作战。但白莲教在野战中不是官军的对手,全靠游击得胜。因此,各地乡勇只要完成了那个八字任务,白莲教就变得寸步难行。各地乡勇配合官军,把白莲教困死在战场上了。
咸丰时代则完全不同。如今的正规军大势已去,不堪一击。太平军经过各地,官军当即溃散,乡勇成为抗击造反军的主力。但是各地乡勇通常不能出境作战,缺乏野战能力和统一的指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各地乡勇组织起来,经过训练,改良武器装备,组建成强大的兵团,才能取代绿营部队,为朝廷剿灭太平军。
曾国藩明知咸丰的想法落伍了,但他不好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子的谬误,同时担心把话说白了,会让咸丰看出他在军事上的野心而对他心生顾忌。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想靠各地的老式团勇来扑灭太平军,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这个钦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其实对团练乡民毫无兴趣。咸丰既然要他从事军武,他就要组建一支新式的军队,取代现存的朝廷正规军,挽狂澜于既倒。不过,一切还得谨慎从事。
曾国藩一天都没有办过团练,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得到皇帝的授权之后,把已经团练好的乡勇部队,召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进一步加强训练,补充装备,改革军制,扩展为清末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他从一开始就借鉴江忠源的经验,试图组建一支正规军,以对抗全国的太平军为己任。他的设想规模宏大,是罗泽南、王珍和李续宾这些元老级的团练专家不敢去想的。那些人没有曾国藩这么高的级别,也没得到皇帝的授权,就是想办也办不到。
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所谈的设想,是在省城长沙成立一个大团。他心中设想的大团,就是一个军的兵力。他要把各地已经办好的乡勇部队集结到长沙,由他统一指挥,根据需要到各处作战。这实际上就是一支新的野战部队。为了隐藏真实的目的,他为这个想法找了一个恰当的理由。他说省城长沙兵力单薄,行伍空虚,不足以担任城防。有了这个乡勇大团,进行扎实的训练,既可以用来剿捕土匪,也对省城防御不无裨益。
曾国藩还从财政入手,阐述了在省城办大团的好处。皇上号召团练乡民,确实是当务之急。但团练的难处,不在于操习武艺,而在于难以募集资金。
朝廷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清廷为鸦片战争陆续支付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纹银。道光二十三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两,清廉的骆秉章也因此受到连累。全国税款欠缴几近五千万两。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两。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曾国藩说,国库空虚,朝廷无法像嘉庆年间那样资助团练,而民间捐款,指望虽大,却是画饼望梅,当不得真。他提出把各地团练集中起来,编组更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可以为朝廷节省军费。把壮健朴实的乡民招募到长沙,训练一个人,就收一个人的成效。这种做法比各地一哄而起操办团练,也能减少许多团练经费。
官军进剿太平军以来,时间已有两年多,消耗的军饷不可谓不多,调集的军队不可谓不众,但是将士们遇敌即逃,很少迎斗。官军只是从远处开火,不敢短兵相接。原因在于士兵没有经过训练,既缺乏胆量,又没有武艺在身。他要改弦更张,注重练兵,吸取明朝戚继光和近人傅鼐的经验,练兵只求其精,不求其多。不指望马上见效,只指望能够接济前方作战的兵力。
曾国藩使用这样一番说辞,从本质上改变了团练的性质。按照清朝的惯例,团练只是在各州各县就地兴办,省城和重镇的防务还是由绿营担任。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大大提高了团练的地位,增强了团练的职能。
曾国藩为了表明自己不愿违背人伦,在奏折中写了一个附片,说他在京供职十四年,今年回家,祖父祖母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野草,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办完,不忍心突然离家担任公务,请求等到战事顺利之后,团防之事办得有了头绪之时,仍然回籍守制,以遂乌私。
事实上,曾国藩也知道,官军的战事不可能很快逆转,他回家继续守制的可能性不大。只要皇上允许,他可以在团练一事上大有作为。
咸丰正处在病急乱投医的时候,不管曾国藩是不是违背了祖宗留下的团练原则,也不管曾国藩是否有心当一位军事首领,只要能够有助于打败洪秀全,他都会同意。所以这份奏折奉到朱批:“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关于团练的新思维和新实践,使他成为咸丰时代最成功的团练大臣。咸丰任命的第一位团练大臣是前任刑部尚书陈孚恩,第二位就是曾国藩。此后三个月里,咸丰一口气任命了四十九位团练大臣。这些人当中,只有曾国藩真正把团练办成了气候,这是因为他勇于改革旧的团练体制,让乡勇走出了家乡,集结起来,组成了强大的野战部队。
曾国藩有了现成的部队
在曾国藩奉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的同时,张亮基命令湘乡知县朱孙贻推举可以担任将领的人才,朱孙贻提名王珍。张亮基命令王珍、罗泽南和罗信南分别率领团练的乡勇到长沙设防。王珍率领三百人进入长沙;罗泽南和罗信南率领七百人开入省会。
从湘乡出山的团练大臣,以及来自湘乡的团练乡勇,在咸丰二年的最后一个月聚首于长沙。王珍将所部称为“湘勇”。湖南已有楚勇、南勇、宝勇、浏勇等勇队,王珍采用“湘勇”的番号,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勇军。
第一批来到长沙的湘乡勇,包括了罗泽南的中里湘乡勇和王珍的下里湘乡勇,但不包括李续宾的上里湘乡勇。一千人分为三营,王珍指挥左营,罗泽南指挥中营,罗信南指挥右营。
曾国藩决定按照明朝戚继光管理军队的办法,每天操练湘乡勇,并且为之酌定训练章程。曾国荃佐理兄长,为他拟写了治兵三十二策。王珍也十分积极地与曾国藩兄弟探讨训练方法,
王珍此年二十九岁,比曾国藩小了一轮,但在团练湘勇方面,足以做曾国藩的老师。他曾跟随罗泽南在湘乡山中学习,领悟自我修养的道理。罗泽南手下有几十个门生,空闲时教授战术,练习技击、剑术、跳远,排列战阵,经常演习。那时候,很多老乡认为罗泽南精神异常,罗泽南则说:“你们错了,过不了几年,天下必将大乱,不可不先修武备。”
王珍年少,性情最为刚猛,习武最为勤勉。罗泽南说:“我门下唯有王珍有望成为名将!”
王珍的练勇开到,曾国藩兄弟和郭嵩焘观摩阵法。校场之中,湘勇列队而入,王珍登上将台,挥旗擂鼓。左右每队各有一百人。第一通鼓声响起,队伍鱼贯而行,列为两行,左侧的队伍奔向右侧,右侧的队伍奔向左侧,行走三轮以后,围成圆圈,都持武器对外。第二通鼓声响起,队伍向左右奔走,回复原来的队列,相对格斗,左起则右伏,右起则左伏,三起三伏。军士们再次奔走,圆阵变为方阵。于是,后军分别从左右出场,蛇行绕攻,前军三合而退,前方的左右两军也互为进退。王珍擂鼓鸣角,旗帜成圆周挥舞,士卒便奔走一圈,聚为城郭。城有三道门,先聚集的士卒分左右行走,先从门口奔出,其余也按次序再起成队。士卒的行动只听从旗鼓的指挥,疾奔犹如风雨,听不到任何声息。
看罢演习,郭嵩焘和曾国荃大为喝彩,曾国藩频频点头。他已经看出,王珍是一位将才。
王珍给观摩者讲解他为湘勇制定的营制。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队由十四人组成,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六个队合成一哨,每哨八十五人,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四个哨合成一个营,营的长官叫营官。因此,一营人数为三百四十人。加上由营部统一调配的整容师、缝衣师、医生、药师、铜工和木工,共有三百六十人。
曾国藩问道:“勇队的武器都有哪些?”
王珍回答:“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曾国藩步下看台,走到队伍前面,仔细打量湘乡勇的号衣。他们的制服都是蓝色镶边,仿造旗人服装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王珍跟在曾国藩的身后,解说道:“营部有一本花名册,注明本营所有士卒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新勇入营,必经人担保。”
曾国藩微笑着点点头。王珍又说:“湘乡练勇,原则是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营官三百四十人的编制,他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挑选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以我之见,什长和伍长,以沉默寡言的人为上选。”
接着,王珍向曾国藩等人介绍了湘乡勇独特的管理办法。营官管理部属,有一定的民主程序。每月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饮茶,商议军务,了解什长是否称职,散勇是否勤操听令。每月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公开赏罚升降。每定一桩赏罚,必邀集哨长和什长共同参加,说明赏罚的原因。
营官还要做思想工作。在作战时间以外,要经常召集大家训话,灌输做人的准则,激发听者的天良,鼓舞他们的斗志。营官要常检阅操练,教习阵法,同时要关心勇员的疾苦。
在部队里做思想工作,是湘勇指挥官的一个重要发明。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罗泽南说,军人从事着风险极大的职业,很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对于军士,必须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部队才可能不畏艰苦,百折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