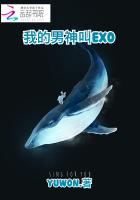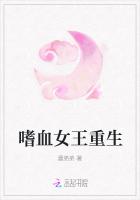其六描写天伦之乐。我把老婆孩子寄在湘潭岳母家,已经长达九年。入赘的女婿久久不能独立,满心羞惭。大女儿孝瑜都七岁了,已经开始学写字;小桑树也开始长叶,可以喂蚕。多亏妻子不嫌我又穷又笨,自得其乐,小老婆也懂得安分随缘。一家人争论历史,唱和诗词,生趣盎然。盼望有一天能在昭山买下一块小地,盖几间茅屋,就有属于自己的家了。
其七寄怀于友人。朋友啊,身在旅途,更想见到你。禽鸟尚且要成群结队,而我们隔着千山万水,只能书信往来。我们在洞庭湖的凉风中吟诗道别,在京城的夕阳下依依分手。但愿我的梦能飞越四千里,在茫茫人海中见到你!
其八写怀才不遇。唐玄宗为了得到杨玉环,不拘翁媳之礼;小矮人在汉代宫廷里诙谐逗趣,也能填饱肚子。想要当官何必心急,真正的人才不必如此。灯前的身影,孤独如点缀秋山的黄石;下巴上的胡子,如听到惊雷的春笋一般嗖嗖冒出。等到年老衰迈的时候,打开画卷一看,还能依稀找出当年的雄姿。
湘潭的朋友罗汝怀读了他的《自题小像诗》,与之唱和,有心安慰一番:
捂地九州归指掌,匡时五亩树蚕桑。
罗汝怀还特意做了注解:左君啊,你两手就把地球捂住了,天下大势,尽在掌握之中。虽然暂时未能登上军政大舞台,可是你在五亩地上栽桑养蚕,不同样是为了解救百姓的困难吗?
贻端夫人读了丈夫的《自题小像诗》,也写诗唱和,以慰夫心:
清时贤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
相公啊,像你这样的才俊,是不可能被社会埋没的。在溪水清凉的山间隐居一阵,照样能有一番作为。栽树养蚕都是长远的规划,自古以来的帝王,岂不是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
其实何须别人安慰?左宗棠一直未能摆脱贫贱的社会地位,难道这个倔傲的汉子认输了吗?没有。只要心中还有匡时济世的热情,他就不会向命运低头。
从道光二十年至道光二十七年,他投入八年的青春,隐居安化小淹村,在陶家宅邸任塾师。山庄僻静,日子如出家人一般寂寞。好在陶家藏书颇丰,还有官宦生涯的公私档案、清朝宪章,为左宗棠提供了一个从事研究的资料室。
八年教书生涯,左宗棠博观纵览,知识精进。他研读陶澍与林则徐等人的书信往来,对军政要务了如指掌。陶家的藏书还为他提供了新的地理资料,他与夫人一起,对以前绘出的地图及时补充修改,完成了第二期工程。周贻端把地图描绘下来,用湘绣工艺绣在绢布上。遗憾的是,这些地图竟没有流传下来。
这时的左宗棠,只要给他一个舞台,他就能差遣百官千僚,指挥万马千军,治理一方疆土。虽然暂且报国无门,但他通过有偿服务,毕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他在陶家坐馆教书,每年有二百两银子的年薪。他省吃俭用,攒起银子,指望建立一份家业。
左宗棠几经查勘,在老家左家塅以西十多里处的柳家冲,买了七十亩田土。此地现称湘阴县樟树乡巡山村。他预感到乱世即将来临,选地时侧重考虑治安条件,是否利于躲避兵祸。
左宗棠买地,不是为了开发房地产,只为起码的生存。新房只盖一所,其余的田土用于耕种。设计规划是自己做的,一座小型的庄园很快建成。园内有稻田,有坡地,还有水塘。
哈哈,我左宗棠总算有个家了!
秋收季节,左宗棠携带妻小从湘潭周宅移居湘阴柳庄。他唯恐别人误会他是暴发户,在屋前的门楣上亲笔题写“柳庄”二字,让大家知道,他以五柳先生陶渊明自比,要隐居山野了。
左宗棠家住湘阴,上班却在安化,两地相距三四百里,乘车坐船,单程跑一趟都要一两天。这样的上班族是敬业的典范,那时真是罕见。他回家休假也不闲着,监督农庄的工作,用平时钻研的农业技术进行实验。他每天都在田地上巡视,又给自己取了一个外号,叫做“湘上农人”。
农民有什么不好?至少一家人的温饱有了着落。从此就做个规规矩矩的老百姓吧。
但愿长为太平有道之民,则幸甚耳。
边耕田边读书,是一种非常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既有田园乐趣,又有诗书馨香。当岳母想念女儿和外孙女时,时常带着孙儿来到柳庄,抽空教孙辈念书。夜晚,孩子们坐成一排,朗朗读书声,传到户外很远的地方。村民们经过这里,听到读书声,肃然起敬:柳庄就是柳庄,这里住的,不是纯粹的泥腿子。
乔迁新居的一年很快过去,左宗棠在安化陶家授馆进入第六年。农业虽然成了人生的第一要务,但他一年里仍然浏览新书上万卷,然后摇摇头说:近时佳作不多,仅得几篇。算了,还是写点农业书籍,向人们传授园圃技术。分门别类写了十几篇,题为《朴存阁农书》
安化是著名的茶乡,左宗棠想到一个问题:湘阴人为什么不懂得种茶呢?一转念,他把茶树种植引入家乡,在柳庄种茶植树。
秋天,胡林翼来到小淹,参加陶澍夫人的葬礼。两个好友晤谈十天,友谊更加巩固。他告诫左宗棠,考虑事情不宜过于周密,论述问题不宜毫无遗漏。左宗棠说:“谢谢,你一针见血,指出了我的毛病。”
道光二十六年(1846),左宗棠从古代农业技术中采取当时便于操作的办法,试行耕种柳庄的农田,充分发挥地利,扩种茶树、桑树和竹子。茶园产生的收入就足以付清国家的税收。《朴存阁农书》编撰一年,已经完工,对湘阴农业和林业的革新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三儿子左孝同后来在《先考事略》中回忆道:
府君于柳庄栽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茶产,实府君为之倡。
左宗棠研究问题总是从大处着眼。他说,现在的种田人和读书人一样,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急功近利,抓小放大,误了自己,也误了别人,对国家的负面影响不小。
炎热的八月,天气久旱不雨。这时左宗棠身在安化,一天夜间,忽然梦见雷电绕身,大雨如注。过了几天,接到柳庄来信,才知他做梦的那天,周夫人为他生下了长子。左宗棠欣喜之余,忆起梦境,将儿子取名叫“霖生”,后来改名“孝威”。
这一年,湖南宁远有胡有禄造反,东安有王宗献造反。左宗棠感到乱世真的要来了。他开始钻研筑墙掘壕和修建碉堡的办法。他认为,住在乡下,学会自保和学习农业与畜牧业同样重要。
道光二十七年(1847),农人左宗棠家里又有两件喜事。一妻一妾连生男丁,次子左孝宽在四月出生。此年八月,左宗棠兑现了与陶澍的盟约,将长女孝瑜嫁给了陶桄。完成了这件大事,他于秋后结束在陶氏家馆七年多的塾师生活,返回柳庄。
动乱的局面越来越明显,湖南又有新宁瑶民雷再浩揭竿造反。江忠源组织乡勇,会同官军镇压反军,保升知县,赴浙江补用。这件事令左宗棠颇有感触。书生带兵打仗,因功踏入仕途,也是一种出路。战事如此频繁,军事学似乎大有用武之地。左宗棠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军事研究。他又给自己想到了另一个人生定位:
古人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
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良将。”
第二年,湘阴在连年大旱后忽然大水成灾,柳庄也不例外。人闹饥荒,庄稼被淹,家人皆病。左宗棠度过了一生最困难的时光。
老天没日没夜地浇下雨水,稻田被淹,谷子都发芽了,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进了当铺。一家十二口都成了病号。光是发愁也没用,左宗棠跟同乡开个玩笑:“我要把杜老的诗句‘男呻女吟四壁静’改一个字,变成‘男呻女吟四壁空’。”
左宗棠开设了家庭病床,无照行医。他还给自己封了个赈灾领导小组组长的职位,有空就往外面跑,办理赈灾事务,劝富有人家捐赈。他信奉孔子儒学,认为行善是第一要义。他对捐赈行为给予极高的评价,向富人们反复灌输一个理念:捐赈是传统的美德。据他统计,经过大家的劝说,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和宁乡各地,捐献的银钱谷米,折合银子,不下五十万两。
光靠救济也不是办法,左宗棠劝左氏家族的人们储备粮谷,以备饥荒。各家拿出一些粮食,存放在一个粮仓里,遇到灾荒,便开仓自救。这个粮仓需要管理,于是就有了仁风团。
这是一个具有预见性的备荒措施。官府无心过问,民间由左宗棠发起。经过了两年的苦旱,又碰上一年的大水,谁敢说明年就一定没有天灾?在他的劝说下,左氏一族纷纷响应,一个救灾基金就这样形成了。
左宗棠一边救灾,一边还得关心军事。灾荒往往是战乱的前奏。种种迹象表明,政局不稳,民心混乱。当一个名将,定国安邦,或许是一条必行的道路。他给身在北京的二哥写信,自称在军事上的造诣决不是纸上谈兵。
文韬武略在胸,还得为生计操劳。天灾严重,“湘上农人”种田都吃不饱肚子,为了养家活口,只得进城发展。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来到长沙,继承父业,在朱文公祠开馆授徒。第一个学生就是女婿陶桄。其他学生无不是今后的干才。益阳少年周开锡,长沙少年黄瑜、黄上达和黄济兄弟,都是左宗棠的高徒。黄家三兄弟的父亲就是长沙保卫战中大出风头的黄冕(见第一章)。此人也是林则徐的旧交,他信得过左宗棠,把三个儿子都交给他培养。
这一年,湘阴果然又遭大水。左宗棠身在长沙城,也没有忘记水灾作孽多么可怕。他给二哥写信,忧心忡忡。
弟一家不足忧,惟如此奇荒,邻里之颠连者必多。倘不急筹赈济,则大乱即在目前,其可忧又不但贫也,其受害又不止一家也。
水灾刚有迹象,左宗棠便向学生家长预支学费,回到乡下,买下一些谷粮,一半接济左家塅的族人,另一半接济柳家冲的同乡。可是需要救济的灾民远远不止这些,逃难的灾民源源不断地经过柳庄。
柳庄距湘江只有十里,又靠近湖滨,处在重灾区的边缘。每一天,成百上千的饥民取道门径口,前往高乡求食,柳庄是必经之地。路边到处是饿死鬼,满眼都是可怜人。左宗棠不忍心看着不管。和周夫人一合计,把粮仓里的谷子全部搬出来,煮成稀饭,散发给饥民。
家里的粮食很快就送完了。大水不仅为害湖南,也把东南各省变成了汪洋泽国。大米奇缺,每斗卖到六七百文钱,道路上都是逃荒的饥民。他们营养不良,缺乏抵抗力,疾病迅速传播。左宗棠和家人组成医疗队,救助病倒的灾民。他掌握了一些单方,买来药草,做成药丸。他对医治流行病颇有心得,妙手回春,保全了许多人的性命。
左家人是一个团结的救灾集体。左宗棠在灶边熬药,周夫人和张氏率领仆妇站在门口指挥护理。没钱买药了,就把发簪和耳环当掉。当铺成了左宗棠经常光顾的取款机。他们缩减家里的粮食供应,省下口粮,尽可能救活更多的灾民。小小柳庄,为救灾尽了全部的力量。
灾荒把大批孤儿抛向人间。左宗棠凑了二千两银子,捐给家乡的育婴会。希望工程也要操办。实在没钱了,卖掉田产,来办义务教学。孤寡老人只能靠敬老院,他又兴办了养老会。如此一来,和谐社会已有雏形。
那一段时间,左宗棠累坏了。长沙的学生要读书,课不能不上。课业一完,马上和湘阴同乡一起,四处奔波,劝富裕人家捐赈。赈灾好不容易告一段落,左宗棠松了一口气,在柳庄过了一段短暂的宁静生活。回想所做的公益事业,他感到十分满足。
卧龙即将腾空
道光三十年(1850),天下将要大乱,湘阴建立了仁风团义仓。左宗棠身为表率,一家节衣缩食,捐出所有值钱的物品,筹备积粮。他亲手制订章程,报官府备案。先与周夫人惨淡经营,后来选择公正人士主持。此后很久,乡民们受惠于这个粮食基金。
局势越来越乱,广西无处不在造反。冬天的一个深夜,左宗棠忽闻林则徐奉旨前往广西指挥作战,在途中去世。他手捂胸口,目瞪口呆。
回想去年,正是在这个日子,他来到湘江边,上船拜见林公。为了找个清静的所在,他们解缆开船,乘着乱流,渡到河西,停泊在岳麓山下。他与林公的儿子林汝舟兄弟一起陪侍林公左右,把酒而谈。林公说,带兵的统帅贪得无厌,是军政的蠹虫;总督这个官位最容易产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