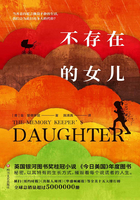三更刚过,金牛岭、白石山上陡起秋雾。雾越来越大,越来越浓,霎时间,从金牛镇到三河城,方圆三四十里地面上的山水房屋,全部消失在一片夜雾之中。此时,陈玉成、李秀成将布置多日的大网开始收拢了。
陈玉成率本部七万人从金牛镇大道向三河推进,李秀成指挥五万人从白石山翻过来,吴定规统领三河城上一万人马踏过护城河,吴如孝、张乐行带一万人由西向东。四路人马十四万人,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将七千湘勇团团包围在三河城郊。当震耳欲聋的鼓角声,把李续宾和湘勇们从睡梦中惊醒时,他们面临着的,已是无可挽回的灭顶之灾了。湘勇们惊慌失措,心胆俱裂,成百上千的人,稀里糊涂地顷刻间便做了无头鬼。浓雾中,即便打起灯笼,十几步外的人和物也看不见,李续宾又急又恨。周国虞命令手下人齐声高喊:
“活捉李续宾!”
“抓住李妖头,抽筋剥皮,报仇雪恨!”
李续宾慌乱之中顾不得找曾国华,提着一把剑仓皇而逃。
曾国华睡在寡妇温暖的被窝里,忽然被一阵粗暴的打门声惊醒:“快开门,快开门!老子们要砸了!”
原来,这是几个太平军。前几天,他们还是德兴阿手下的绿营士兵,乌衣镇兵败后投降了太平天国,他们想趁混乱之机打家劫舍,发点财。曾国华猛地从被窝里爬出,赶紧穿衣,寡妇吓得脸色惨白,紧紧抱住他。曾国华推开寡妇,抽出佩剑。门被冲开了。火把之中,士兵们一眼看见放在床头的曾国华的官服,惊叫道:“这是一个清妖!”
“还是一个官儿哩!”
“抓活的!”
说话间,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曾国华毕竟是一介书生,如何是他们的对手。交手不过两三下,剑便被击落,立即被活捉了。士兵们狂呼乱叫起来,拿麻绳将曾国华绑得死死的,吆喝着推出门外。一个士兵盯着寡妇,舍不得走,有人在门外吼:“色鬼!想打水炮了?你若不去,赏银没你的份儿。”
那人走到寡妇身边,在她的脸上重重地掐了一下:“小娘们儿,待会儿再跟你痛快玩一阵。”
曾国华垂头丧气地走出门,听见四面八方的喊杀声,方知太平军已展开了全面进攻,后悔不迭,心中寻思着如何逃走。
太阳出来后,雾消散了。李续宾带着百余名亲兵,慌乱之中逃到一个小山包上。只见山包周围,太平军人山人海,无数面红、黄、蓝、白、黑旗帜迎风招展,李续宾知今日已难逃厄运,懊丧地靠在一棵树边低头长叹。他后悔不该听信曾国华的无知妄见,后悔没有采纳赵烈文的建议,恨官文不出兵救援,更恨自己麻痹轻敌,没有料到敌人在雾夜中偷营,现在他面临着的毫无疑问是全军覆没。从咸丰三年来,大大小小百十个战役所赢得的三湘名将的声誉将扫地以尽,涤师进军皖中的用兵计划也全盘打破了。这时,周国虞带着一支人马冲上山来,大喊:“树下的那个清妖便是李续宾!活捉的,赏银一千两!”
话音未落,几百名士兵呐喊着冲上山来。内中有几个野人山的人,更是痛恨已极,高叫:“抓住李续宾这个狗娘养的!”“把这条恶狗碎尸万段!”
李续宾身边的亲兵慌忙迎敌。李续宾双脚都已受伤,他刚一迈步,便痛得锥心般难受。眼看太平军就要冲上山顶,李续宾咬咬牙,解下腰带,向北跪下三叩头,然后将腰带挂在树杈上,踩着一块石板,将头伸进带圈中,追随他的老师罗泽南去了。
正午时分,陈玉成、李秀成胜利地结束了对太平天国后期起着重大作用的三河战役,七千湘勇除两三百名侥幸逃走者外,全部葬身三河城。
曾国华死而复生,不得已投奔大哥给他指引的归宿
当李续宾、曾国华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江西建昌府时,曾国藩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吓得几乎晕死过去。他对李续宾寄托极大的期望,也相信李能不负重托。谁知恰恰就是这个老成可靠的李续宾坏了大事,不仅经营皖中、谋夺攻克江宁首功的如意算盘被打得粉碎,就连让六弟依附李续宾成名的想法也破灭了。他知道李续宾、曾国华在这种情况下定然难以生还,良将顿失,骨肉永别,心中伤悼不已。
这是湘勇出师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建昌军营上自将官,下至勇丁,几乎人人都与三河阵亡的人员有联系:或为亲戚,或为朋友,或为乡邻,或为熟人。消息传来,不待吩咐,各营各哨便自动地焚纸燃香,挂起招魂幡,军营上下,蒙着一片阴霾。一连几天,曾国藩看到的都是这种情景,心里难受至极。他想到此刻的湘乡县,不知有多少人家正在举办丧仪,有多少寡妇孤儿在哀哀欲绝。湘乡县的悲痛,将十倍百倍地超过建昌军营。湘勇的元气如何恢复?进军皖中的用兵方略改不改变?曾国藩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几天后,他从痛苦中清醒过来。“好汉打掉牙和血吞”,重振军威,报仇雪恨,才是大丈夫之所为。他甚至还怀着一线希望,李续宾、曾国华也可能死里逃生了,说不定哪天会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那时再把皖中的事交给他们。他相信,受此大挫后,李续宾和曾国华会更加成熟。曾国藩想通后,下令军营中所有招魂幡一律烧掉,不准再谈三河失败的事,一切都按原计划去做。
十天过后,派到三河阵地上查访尸体的勇丁回来报告,李续宾的遗体已找到,将由安徽巡抚翁同书出面隆重礼葬,曾国华的遗体一直未见。阵地上的无头尸身成百上千,估计曾国华是被砍头致死。又过了十多天,武昌、湘乡、长沙、寿州,各处信件先后来到,均未见曾国华的踪迹,曾国藩认定六弟已死无疑。
这一天,他郑重其事地给朝廷上折,详奏曾国华自咸丰四年带勇以来所立下的桩桩功劳,以及这次殉国的悲壮。拜折之后,又给在家的四弟、满弟写了一封信,要他们安慰叔父及温甫妻妾;并再三指出,这种时候,全家务必要比往日更和睦亲热,又检讨自己在家时脾气不好,兄弟不和,今后要引以为戒。又叫他们去查看父母坟茔,是不是被人挖动了,泄漏了气运。半个月后,朝廷发来上谕,追赠候选同知曾国华为道员,从优议恤,加恩赏给其父曾骥云从二品封典,咸丰帝还亲书“一门忠义”四字,以示格外褒奖。
曾国藩接到这道上谕,甚感宽慰,立即派专人将皇上御笔送回荷叶塘,要家中把“一门忠义”四字制成金匾,高悬在黄金堂上,以此旷代之荣上慰父母在天之灵,下励儿孙忠君之心。至于赏给叔父从二品封典一事,却把曾国藩弄得哭笑不得。早在道光三十年,曾国藩在侍郎任内曾邀封叔父从一品封典,不想八年后反倒来个从二品封典。曾国藩心中暗暗埋怨礼部官员糊涂马虎,连随手查查的事都懒得一为,现在弄得他左右为难,受亦不是,不受亦不是。曾国藩为此很费了一番思考。他在仔细斟酌之后,给皇上上了一道谢恩折,先将历次封典之事的过程叙说一通,然后写上:“诰轴则祗领新纶,谨拜此日九重之命;顶戴则仍从旧秩,不忘昔年两次之恩。唯是降挹稠迭,报称尤难。臣唯有竭尽愚忠,代臣弟弥未竟之憾,代臣叔抒向日之忱,以期仰答高厚于万一。”
不久,满弟国葆受叔父之命来到建昌,代兄带勇。曾国藩着实勉励一番,拨五百勇丁让他统领,又给他改名贞干,字子恒,意为吸取靖港之败的教训,为人办事,忠贞有恒。
这天半夜,曾国藩在灯下再次修改近日写成的《母弟温甫哀词》。他哀悯六弟满腹才华,却功名不遂,正要凭借军功出人头地之时,却又兵败身死,真可谓命运乖舛;又怜悯风烛残年的叔父,叔父因无子才过继六弟,谁料继子又不得永年,老而丧子,是人生的大不幸;继而又怜悯已成孤儿的侄子。小小年纪,便从此永远失去了父亲,心灵要承受多大的痛苦!作为大伯,曾国藩决定,今后将由自己承担起对这个侄子的抚养教育之责,让他如同纪泽、纪鸿一样地得到慈爱温暖,长大成人,继承叔父一房的香火。曾国藩就这样边想边改,时常停笔凝思,望着跳跃着的烛火出神。
“大哥,快开门!”急促的声音,惊得曾国藩回过神来。这是贞干在外面喊。
曾国藩打开门,贞干急忙闪进屋,身后还跟了一个人。
“大哥,你看谁来了?”贞干有意轻声地说,但语气中的兴奋之情显然压抑不住。
昏暗的烛光中,曾国藩见来人衣衫破损、面容憔悴。看着看着,他不觉惊呆了:这不是自己刻骨思念的六弟温甫吗?他不敢相信,温甫失踪一个多月了,宾字营、华字营全军覆没,统领李续宾已死,高级将领无一人生还,全军副统领、华字营营官今夜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曾国藩拿起蜡烛,走到那人身边。他把烛火举高,照着那人的面孔,仔仔细细地审看着。不错,这人的确是他的胞弟曾国华!
“你是温甫?”尽管这样,他仍带着怀疑的口气问。
“大哥,是我呀!”曾国华见大哥终于认出了他,不禁悲喜交集,双手抱着大哥的肩膀,眼泪大把大把地流了下来。
千真万确是自己的亲兄弟活生生地站在面前,一刹那间,曾国藩心里充满着巨大的喜悦:六弟没有死!叔父抹去了丧子之痛,侄儿免去了孤儿之悲,这真是曾氏一门中的大喜大庆!
“快坐,快坐下,温甫,你受苦了。”
曾国藩双手扶着弟弟坐下,两眼湿润润的。死里逃生的曾国华见大哥这种手足真情,心里感动极了:“大哥,这一个多月来,我想死了你和老满!”
“我们也很想念你!”曾国藩真诚地说,并亲手给弟弟端来一杯热茶,又转脸问满弟,“贞干,你是在哪里找到温甫的?”
贞干高兴地回答:“今日黄昏时,我从镇上回营,路过一座作废的砖窑,忽然听见有人轻轻地叫我的名字。进去一看,原来是六哥在那里。我又惊又喜。六哥当即要我带他来见大哥,我说现在不能去,半夜时我再带你去。”
“做得对。”对满弟的老成,曾国藩甚是满意,他转问六弟,“温甫,三河之战已经一个多月了,你为何这时才露面,害得全家着急,都以为你死了。你这一个多月来在哪些地方?”
“那天半夜,大雾弥漫,长毛前来劫营,我寡不敌众,正拟自裁殉国,突然被一长毛从背后打掉手中的刀,给他们捉住了。”曾国华不敢讲出在寡妇家被抓的真相,编造了这套谎言,“长毛不知我的身份,把我关进一家农户的厨房里,又去忙着抓别的人,不再管我了。我靠着磨盘上下用力擦,将绳子擦断,偷偷地逃了出来。沿途打听到大哥在江西建昌府,就径直向这里奔来,途中又不幸病倒。就这样边走边停,挨过了一个多月。”这几句倒是实情。他说罢,将一杯茶一饮而尽,那样子,的确是病羸饥渴。曾国藩听完六弟的叙说,心中凄然。
“温甫,你们为什么要去打庐州?我是要你们与春霆一起去围安庆。”给六弟添了一杯茶后,曾国藩问。
“大哥,这是我的失策,迪庵也是主张南下围安庆的,我想打下庐州后再南下。”温甫并不掩饰自己的过错,使曾国藩感到六弟的坦诚。
“打三河一事,军中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吗?”一向留心人才的曾国藩,想以此来发现有真知灼见的人才。
“军中没有谁提过,倒是有一个来三河做客的读书人闯营进谏,说不能打三河,要转而打庐江。”
“这人叫什么名字?”曾国藩带有几分惊喜地问。
“此人自称赵烈文,字惠甫,江苏阳湖人,寓居全椒,年纪不大,二三十岁。”
“难得,难得。”曾国藩轻轻地拍打着桌面,感慨地说,说得曾国华脸红起来,大声叫道:“大哥,你让我回湘乡去招募五千勇丁吧,我曾国华若不报此仇,枉为世间一男子!”
“小声点!”曾国藩如同被吓了一跳似的,忙挥手制止。六弟这一句气概雄壮的话,不仅没有引来大哥的赞赏,反而使得见面时的浓烈亲情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满腔的恼怒:正是因为违背了原定的作战方案,才招致这一场空前的惨败。精锐被消灭,进军皖中的大计彻底破产,前途困难重重,作为全军的统帅,他所承受的压力有多巨大呀!他真想把六弟大骂一顿,甚至抽他两耳光,以发泄心头的这股郁闷之气。但他没有这样,只是呆滞地望着温甫,也不作声。曾国华见大哥对他的话没有反应,又再说了一遍:“大哥,过几天我就回湘乡招勇如何?”
“温甫,你太不争气了!”望了很久之后,曾国藩终于忍不住慢慢地吐出一句话。
“大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迪庵和死去的兄弟们,我有罪,罪孽深重。我要重上战场,杀贼赎罪呀!”曾国华从心底里发出自己的呼喊。他深知自己的过失太大了,大哥的这句轻轻的责备,不足以惩罚,他倒是希望被狠狠地杖责一百棍。
“唉!”曾国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六弟的痛悔冲淡了他心中的怨怒,一股怜悯之情油然而生。眼下的处境,温甫自己是一点不明白呀!他能出现在大家面前吗?全军覆没,唯独自己的弟弟、负有直接责任的副统领生还,曾国藩怎么向世人交代?怎么向皇上交代?没有温甫的阵亡,哪来的“一门忠义”褒奖!温甫虽破坏了进军皖中的大计,却又为曾氏家族挣来了天家的旷代隆恩。带兵打仗的曾国藩,是多么需要这种抵御来自各方猜忌的荣耀身份啊!它的作用,要远远超过温甫再募的五千湘勇!如何处置这个意外生还的弟弟呢?既要不负圣恩,又要让他继续活在世界上,曾国藩的脑子在苦苦地盘算着。
见大哥久久不语,贞干劝六哥:“莫这样急,你现在身体很差,无法带兵,回家休息两三个月后再说。”
“不!”曾国华蓦地站起来,坚决地再次请缨,“大哥,你就答应我吧!”
曾国藩苦笑了一下,将桌上那页《母弟温甫哀词》文稿拿起,递给曾国华说:“温甫,可惜你早在一个多月前便死在三河了。”
曾国华接过哀词,看了一眼,一把扯碎,笑着说:“那是讹传,我不是好好地在这里吗?”
“不,你早死了。”曾国藩重复了一句。看着大哥那张变得严峻冷酷的脸孔,分明不是在说笑话,曾国华顿时心凉起来,冒出一股莫名的恐惧。
“大哥,你为何要说这话呢?我没有死,没有死呀!”曾国华凄惨地喊起来。
“不要喊!”曾国藩威严地止住,口气中明显地含着鄙夷,曾国华立时闭了嘴。
“哀词你可以撕掉,皇上的谕旨你能撕掉吗?”曾国藩从柜子里将内阁转抄的上谕找出来。曾国华一看,脸刷地白了。
“三河战败之后,迪庵的遗体很快找到,我等你等了二十多天,一直没有消息,派人查访也未找到,只能断定你已死。全军覆没,你身为迪庵的副手,也只有战死沙场,才能说得过去。我因此上奏皇上,说你已壮烈殉国。”曾国藩缓慢而沉重地说着。曾国华看得出,大哥在压抑着心中的巨大痛苦,听到最后一句话,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大哥继续说:“天恩格外褒奖,从优议恤,不仅追赠你为道员,还赏叔父从二品封典。我日前已申明,叔父大人早蒙赏从一品,请求加恩纪寿及岁引见,想必会蒙俯允。尤其是因你之殉国,皇上御笔亲书‘一门忠义’四字,我已命家里制匾悬挂黄金堂上。这是旷代殊荣,足使我曾氏门第大放光辉。你现在要生还回家,我将如何向皇上交代,我们曾氏一家如何向皇上交代?”
“请大哥再向皇上拜折,叙说我生还缘由,请收回一切赏赐,行吗?”曾国华试探着问。
“你说得好轻巧!”曾国藩瞟了六弟一眼,不悦地说,“欺君之罪,谁受得了?”
“这不是有意的。”曾国华分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