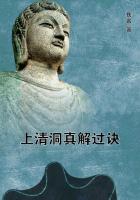在布罗代尔的努力下,总体史的史学范式日趋成熟。同时,年鉴学派也加强了在体制层面的跑马圈地,由杂志、学术研究、教学、机构创建到进入大众媒体,迅速完成向体制内身份的转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年鉴学派已确立了它在法国史学界的主流地位,达到了鼎盛时期。然而,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强调,除了新史学的学术理想之外,也是为了取代实证史学的策略性需要。作为代价,事件、个人和政治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被大大忽略,日趋边缘化。
20世纪60年代末,年鉴学派进入第三阶段。第三代年鉴学派的思想谱系尽管更趋发散而难以勾勒,但共同特征是倡导以计量史学和系列史为代表的史学研究精确化、计量化与电脑化,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系列重复出现、有延续性的现象,从观念、方法到实践都加剧了对偶然性和事件史的排斥。大量分析性语言和图表损害了作品的可读性,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大为削弱。越来越多的史家开始质疑年鉴学派,他们相信,包括个人意志在内的人类文化和上层意识形态,至少也像物产或人口增长等非个人力量一样,在作为促使社会变动的诱因上同样重要。在此背景下,年鉴学派内外开始出现三股具有反拨意义的暗流,分别是政治史[政治史的新潮流有三个既相区别又相结合的发展方向:从社会、经济角度研究政治;从人类学角度来看待政治;以社会学、政治学角度来分析政治。参见姚蒙:《当代法国史学主流》,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05页。]、叙述史[这里的叙述史与传统范型已有很大差异,“这种叙述并不是单纯的嗜古癖者或编年史家所写的东西,而是受到‘有内涵的原则’所指导下的叙述”。这种“有内涵的原则”即:(1)眼光向下,关注底层民众而非大人物或有权者的生活、感情以及行为;(2)分析与叙述并重;(3)使用大量新的边缘史料,诸如刑庭纪录;(4)讲故事的方式受到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深刻影响;(5)所选择的人物、事件均是为了对于一种过去的文化或社会有所启示。[参见劳伦斯·斯通:《历史叙述的复兴:对一种新的老历史的反省》,《新史学》(第四辑),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和微观史学[这种史学范式不把注意力集中在涵盖辽阔的地域、长时段和大量民众的宏观过程,而是注意个别的、具体的事实,强调历史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强调回到具体的人的生活经验上来。其目的是抢救那些“被事件后来的发展挤到了历史过程的边缘,没有进入获胜主流的发展大道”的个体。虽然微观史学这种局部的,甚至是细节式研究的结论不具推广到全局的价值,但是它却有可能通过微观现象的研究来折射其他方面的现象,从而为深入研究整体提供帮助。]。三股暗流并非传统实证史学的死灰复燃,而是在更高基础上的回归。它们从观照视野、观察角度和书写方式上纠正和补充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的偏颇之处。1994年,《年鉴》撤销从战后时期一直沿用至今的副标题“经济、社会、文明”,代之以“历史学、社会科学”。新的题名旨在再一次把政治包括在内,希望对当下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
将近80年前,布洛赫和费弗尔以经济史、社会史为突破口,向政治事件史的垄断地位发起暴动,开始追逐新史学的梦想;半个世纪前,布罗代尔构建基于时空整合的总体史,试图以更宏观的视野和多层次的架构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内在脉动;此后,第三代年鉴学派史家努力推动基于大规模数据统计的计量史学和系列史,期冀建立真正的“科学历史”;今天,《年鉴》再次发现政治与叙述的重要性。与其说年鉴学派回到了旧的兴趣和关注,倒不如说是拓展了历史的视阈。在一次次提出创见、矫枉过正、重新调整的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年鉴学派不断地构建、完善和修正与时代脉动紧密契合的史学范式。“这一群体已将史学家的领域,拓展至出人意表的人类活动领域及传统史学家忽视的社会群体。”[〔英〕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时至今日,用“年鉴”或“范式”已难以概括发生在法国的史学转向,因为20世纪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史学流派都受到这一过程的启发、震动,乃至直接参与其中,它更像是一场运动和革命。然而,南桔北枳的道理提醒我们,对年鉴学派的思想只能辩证、批判地吸收。它能适合中国的土壤吗?
回望中国史学的百年流变,如同20世纪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一样,充满着此消彼长的明潮暗涌。各种史学流派先后粉墨登场,或重方法、或贵材料、或尊理论,差异如此之大,甚至于冰炭难容、势同水火。然而追根溯源,它们无不聚拢在“科学历史学”的旗帜下,只是出于对“科学”的不同理解而选择了迥异的前行路向。不过,透过政治与学术复杂纠葛的重重迷障,我们依然不难发现掩映于其间的清晰脉络,即百年演进过程始终徘徊于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可以说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王学典:《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兼论历史学的性质问题》,《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这种趋向到了新世纪之初依旧如此清晰,集中表现为日趋边缘化的唯物史观史学、主张回到考据传统的“国学热”,以及试图会通两者的社会史三足鼎立的情势。
中国内地史学界对年鉴学派的真正引介是在“文革”之后。1983年,“历史科学规划小组史学理论组”成立,开始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和流派,其中“最多的是年鉴学派”。[姜凡:《十年来我国对年鉴学派——新史学的研究》,《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1期。]年鉴学派经典著作被陆续翻译出版,学者开始成体系地研究年鉴学派。显然,对一个西方史学流派如此大规模的介绍和研究,并非偶然。这一方面是史家试图从这一当代影响最大的西方史学流派中寻找改造中国史学的启示;另一方面,如果将年鉴学派史学范式与当前中国内地史学的三个发展路向逐一对照的话,不难发现,年鉴学派与后三者大多存在或多或少相近的学术渊源与内在勾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与成长,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中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唯物史观一度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其作为一种史学新范式的学术意义被遮蔽了。但如果将唯物史观与法国年鉴学派范式,以及鲜明的社会史取向稍加对照,两者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如出一辙。多位年鉴学派史家坦承,马克思理论是年鉴学派重要的思想来源。费弗尔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2版,第335页。]布罗代尔则认为,“马克思的天才之处、他那延续不断的吸引力的秘密之处,就在于他是第一个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而建立起真正的社会模式。”[姚蒙:《当代法国史学主流》,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61页。]不同的是,年鉴学派并不认同唯物史观教条化、公式化的一面,摒弃了它的哲学层次。正是这种细微的差异,使年鉴学派与中国唯物史观派走向两个不同的发展路向。
中国社会史范式数十年的成长历程,同样与年鉴学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至少选择了相近的道路。早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史论战,特别是《食货》杂志的史学实践,就已初步奠定中国社会史范式的早期雏形。有学者在对《食货》的旨趣与年鉴学派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两者存在诸多神似的地方,并认为中国“社会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是一种研究范式,大概出现于本世纪20年代末,与法国年鉴学派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至少在30至40年代,曾一度辉煌”。[郭松义:《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赵世瑜也指出,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是在大量引进西方20世纪新史学,尤其是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理念和西方新兴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完成的”。[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至于史料学派与年鉴学派,它们之间似乎毫无关联,甚至是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事实上,作为史料学派的两大学术渊源,不管是中国传统考据学,还是西方兰克史学,它们所倡导的史料批判,以及从最原始档案资料中去研究历史的大方向,至今在史学研究中仍不可动摇,在年鉴学派的作品中同样如此。当人们盛赞《地中海》时,更多的只看到三种时段的总体史架构,而忽略了布罗代尔为此用了近20年的时间出入于各个档案馆。他夫人回忆,“令他动情的,而这也是他漫长一生中所培育出来的,甚至到年老为止一直都没改变的,还是在直接阅读档案……档案对他而言是一件事,是一种活生生的广博知识,是一种适合他想象力运作的好对象。”[《布劳代尔夫人的见证》,《年鉴学派管窥》,赖建诚编译,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222页。]多年后著名的《蒙塔尤》甚至完全建立在一份审问记录上。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前言中写道:“任何历史研究都应当从分析原始资料开始。简要地说,我们这本书也将遵照这一原则。”[〔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页。]这些细节均证明,年鉴学派与实证史学并非毫无联系,只是其史料视野远比后者宽广得多。诚如姚蒙所分析的,“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主流始终为这样两个基本目标而努力: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和史学学科的完整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鉴——新史学并未割裂传统,也并未从本质上推翻、否定十九世纪的实证史学,而代表了自十九世纪或更早就开始的史学研究科学化、学科化历程在二十世纪的继续。”[姚蒙:《当代法国史学主流》,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214页。]
年鉴学派与中国史学百年演进脉络,以及内地史坛当下三股主要史学潮流之间的学术渊源,无疑为中国史学借鉴年鉴学派,或者年鉴学派的本土化,提供了扎实的现实环境与学术土壤。
至于在年鉴学派史学范式与影视创作的结合方面,两者的互动同样不绝如缕。在法国,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年鉴学派史家频繁参与历史影片的制作。布罗代尔曾主持制作《地中海》,迪马耶(P.Dumayet)推出明显反映新史学观点的《人们的历史》,杜比(Duby)则制作了《教堂的欧洲》,越来越多有关历史的电视节目也或多或少带上新史学的烙印。在中国,影像工作者陈晓卿完成文献片《朱德》、《刘少奇》后,开始接触到年鉴学派的思想,“哦,敢情对历史的看法,其实有很多种通道。我们过去就在一个特别狭窄的通道里走,其实它可以有更开阔的视野。”年鉴学派的开拓性影响了这位影像工作者在文献片《百年中国》中的创作思路,以及此后更多向度的影像试验。在回顾《见证·影像志》七年的发展历程时他说,“这种做法其实也是受到了年鉴学派,或者是新史学的直接影响,知道什么东西让人看了更真实一点。”[陈晓卿,《百年中国》总导演,《见证·影像志》制片人,2007年2月1日在栏目组接受笔者采访。]来自史学家和影像工作者两个方向的富有成效的尝试让笔者坚信,或许可以在年鉴学派与历史影像书写之间,做更广阔的勾连。
年鉴学派视野下的影像记录
不管是成为战时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战时纪录电影,还是庸俗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形象化政论”;不管是彰显精英主义色彩的文化专题片时代,还是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屏幕上的革命”,直至进入新世纪之后在政治、市场、公共意识等多重诉求下的纪录片多元化场景,回望中国内地纪录片近百年的行进轨迹,虽然其观察视野不断拓展,然而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价值判断等时代主潮还是在这批影像上留下了过于浓重的烙印,每个阶段总是以相对偏颇,甚至极端的方式呈现出与所处时代的某种内在勾连。尽管我们同样可以从中解读出特定时代的历史氛围与精神气质,然而这种偏颇也导致了这批影像缺乏以一种均衡、全局和长远的目光来观察和记录那些具有关口意义的时代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