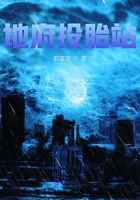她有家、有亲人,却被隔绝在那种生活之外。直到十六岁那年,养祖母告别人世,她才回到自己的家,有了父亲、姐姐、弟弟。骨肉亲缘或许是时光不能阻断的,可是,空白了的那些年里,总是填充着许多无意识的陌生和疏离。张充和从没说过什么,可是,直到十六岁才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一定是要花费时间去克服那些说不出来的隔阂的。
正是因为尝过孤寂的滋味,张充和更加需要一种让她感觉安心的安全感。在感情上,她有理智的一面。
这种理智告诉她,卞之琳绝不是那个合适的人。
这一点,卞之琳自己体认不到。可作为旁观者,作为一个走过相似心路历程的女人,卞之琳的好朋友林徽因是能明白的。
所以,她替她的朋友感到惋惜。
这也许是我心里最郑重的秘密
“从文,你家四小姐怎么样了?医生怎么说?”
话题越扯越远,终于扯到了卞之琳最感兴趣的人身上。
沈从文叹了口气,脸上也挂上了一层薄薄的哀愁:“不太好。三三为了这件事情,都急得上火了。徽因,你知道的,这个病……有点儿麻烦。医生建议静养。岳父已经来信了,要把她接回去养病。”
林徽因了解地点点头:“这是再好不过的法子了。充和在病中,要好好照顾休养。你的三三要照顾孩子,还要理家,实在没有精力再照顾一个病人。充和精神怎么样?”
“还不错。这丫头一直挺省心的。看完医生也没说什么,就是惦记她的功课。”
“功课不是最打紧的,得先把身子养好。什么时候动身?”
卞之琳沉默地听着,什么也不说,可眉宇间的忧郁还是泄露了他的焦躁。
张充和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肺结核,又是肺结核!
这种残酷的病症,似乎格外“偏爱”那些敏感多思的艺术家和文学家,拜伦、济慈、肖邦、卡夫卡……都曾被肺结核所苦,包括林徽因。狄更斯曾经颇有浪漫情怀地描述过肺结核:“灵魂与肉体间搏斗是如此的缓慢、安静而庄严,结局又是如此的确定,日复一日,点点滴滴肉身逐渐枯萎销蚀,以至于精神也变得轻盈,而在它轻飘飘的负荷中焕发出异样的血色。”它的残忍,伴随着偏执的优雅,夺去了无数人的健康与生命。
上天曾经厚待于某些人。可是,却又常在某个瞬间突然心生不甘,非得用一种血色的浪漫来考验与试炼。
卞之琳觉得心疼,也有些疲惫的无能为力感。在她这样虚弱的时候,他能做些什么呢?他不是医生,也不是神灵,他能给的好像只有徒劳的安慰与祝祷。
张充和接到了更多的信。像从前一样,看过就扔了,回都不回。不是绝情,更不是冷心,他们本就是两条平行不相交的线,无论怎么试图靠近,她都不能从他身上嗅到同类的气息。他固执地跟随着她的目光,再温软、再多情,也终究不是她想要的。
她辍学回到苏州,安静地在家里养病。被文人墨客钟爱了数千年的苏州城里,没有北平那样高远的天空和干燥的空气,却有她熟悉、喜爱的一切。她已经是一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大姑娘了,有很多种消遣病中枯燥生活的法子。看书,写字,练练昆曲,日子倒也过得蛮惬意的。
可是,她走了,却把卞之琳的一颗心也带走了。没有了她的北平,像是空了一样,让他很不习惯。他很想过去看看,听她说说话,确认她一切安好。这样,他就……可以放心了。至于那些涌到嘴边却始终不敢出口的想念,还是留给自己吧。她在病中,不宜劳神啊!
讽刺的是,回去的“契机”来得很悲情。
卞之琳的母亲去世了,他要回去奔丧。
命运有时候像个喜欢恶作剧的孩子,非要把人折腾得束手无策才罢休。痛苦的对岸是什么?谁也不知道,只有熬过去了,才会明白。
到苏州的时候,也是一个秋天。天高云淡,风清气朗,处处都透着一股闲适的味道。卞之琳漫步在这个被辞赋盛赞过无数次的古城里,觉得心情舒朗了许多。就连郁结在心里的丧母之痛,也减轻了一点儿。
这样好的风景,是不应该辜负的。他没有能力阻止每一次痛苦难当的失去,却可以享受眼前的这一切。
哦,也只有这样的风景,才能养出那样灵秀的女孩儿。他想,传说这方水土养人,看来是真的。
许久未见,张充和略微清瘦了些,可是精神依然很好。她如同所有好客而尽职的朋友一样,礼貌、周到却又不过分亲热地招待了这位自远方而来的朋友。她带他游览了苏州城,恪尽地主之谊,表现出的欢迎恰如其分,不多,也不少。即使他千里迢迢赶来探望,她的立场也依然没有变。
卞之琳肯定是有些失望的。可是,如同那些不愿说出口的情愫一样,他这些失落同样无处言说。
最终,他黯然地离开苏州,回到他从前的生活。回头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充和那带着疏离的微笑,他觉得“刺眼”,却终究不能决绝地离开。许是太钟爱这处的风光明媚,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抽身了。
那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与人无尤。
也许,这是他心底最郑重的秘密。他无法制止别人来窥探,却能要求自己一生珍惜。
时间久了,旁人都看不下去了。卞之琳除了内向一点儿,还有什么问题?才华横溢,又对充和情根深种,实在没有坚决不允的理由。
于是,有热心的朋友就帮卞之琳说和,特意安排一些饭局让他们见面,以期能交流感情,最终成就一对佳偶。当年的沈从文,不就是靠痴心一片打动美人心的吗?保不齐这又是一段良缘!
卞之琳自然是求之不得。可这些好心对充和来说,却是一种“负担”。因为卞之琳从来不说,她也没办法明确地拒绝,她决定用另外一种方式“抗议”。
张家四小姐离家出走了。这桩“新闻”一出,相熟的每个人心里都各有一番滋味:
这位小姐也太犟了!为什么就不肯给别人一个机会呢?
四小姐虽然人才出众,可眼光也忒高了些!她到底想嫁个什么样的郎君?
眼瞅着岁数也不小了,再这么拖下去,可不见得能碰上这么痴心的。
……
在别人那些堪称“同情”的目光里,卞之琳似乎更沉默了。她这种无声却强烈的拒绝,已经完全表明了态度:做朋友,欢迎;做男女朋友,绝不可能。
卞之琳苦涩地扯了扯嘴角,依旧什么都不说。这段苦恋,是他只想一个人独享的珍藏。她不愿分享,别人也没必要知道。
只是,等待她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他戒不掉,也不想戒。或许,在他心里始终残存着一点点微弱的希望:总有一天,她愿意回过头来看看,给他一丝默许的、鼓励的微笑。
追着看她背影的那些年,他也很累吧?可他同样没有办法去彻底结束这“劳累”。情字恼人,也醉人。
许多许多年以后,卞之琳不无怅惘地说道:“在一般的儿女交往中,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初次结识,显然彼此有相通的‘一点’。由于我的矜持,由于对方的洒脱,看来一纵即逝的这一点,我以为值得珍惜而只能任其消失的一颗朝露……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不会开花结果……”
如果他肯大胆一点儿,结局会不会不一样呢?也许吧!可这毕竟只是一种善意的假设,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什么。人生不像数学公式,可以推倒了重来。
因为一直围着张充和打转,张家的人对这位痴情的追求者都很熟悉了。他沉默的追随,也成了张家的一道风景,每每见到他,都不免唏嘘感慨。可是,也就止于此了。他们只是这场爱情角逐的旁观者,不能决定什么,能作决定的只有张充和一个人。
他一次又一次奔赴在接送张充和的路上。千里奔波,只为了短暂的、没有任何旖旎暧昧的会面。许是走的路太多了,一路的风尘都染白了他的鬂角。而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女子,也不再年轻了。岁月带走了她的青春与娇美,却在眼角那些细微的纹路里填充了更多的风韵。她写诗、画画、教昆曲,过得优雅而与世无争。
卞之琳每次见到她,都会习惯性地愣怔一会儿。她好像永远都能让他瞬间欢喜起来,即便时光冷酷,也带不走他心底深处那份一如往昔的悸动。
若是不能相爱,做个常来常往的朋友也是好的。他们已经相识十多年了,在彼此的生命中已成了不可磨灭的存在。世界如此之大,可是,谁能有福气陪伴别人或被别人陪伴十多年呢?人不可贪心太过,只要还可以像现在这样相见,只要还能有这种细水长流的羁绊,就足以补偿那些寂寂的等待。
然而,上天似乎连这个卑微的小心愿都不愿成全。卞之琳十几年的等待,等来的却是张充和的婚礼。她成了别人的新娘,并且跟着夫君离开了中国,连决绝的背影都不肯给了。
年近四十的卞之琳哀伤地站在阴暗的风口里,连叹息都能揪扯出疼痛。他,毕竟不像她那样洒脱啊!从此以后,他要靠什么来凭吊心里那份无望的恋情?
他还是像从前那样,有空就去张家看看,住在张充和从前住的房间里,遥遥地想念她。她剥夺了他的爱情,却不能剥夺他想念的权利。这,也许是他唯一得到的慈悲。
“之琳,你怎么比我还瘦?”再一次踏进梁家的客厅,已经是1949年了。他们都老了,都有太多说不动的心事。
林徽因的笑容里带着一点儿心疼。她知道,充和刚出国,这个寡言少语的朋友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很难过的。她亲热地握着他的手,用一种温暖到让人落泪的声音说道:“走了这么久的路,是不是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