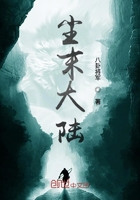“讲讲你的故事把。”我们在调情。
“你确定你想听?”许娟说。
“恩。”
“我当时和妹妹一起在城里上学。有段时间我们迷上了上网,就天天逃课。有天在网吧认识了个帅哥。他以后老来学校找我,天天带我逛街,吃饭。那次他约我和妹妹一起出去玩。我们在城里玩了一整天。天快黑的时候我们坐他们的车来到市郊的一个饭馆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感觉很困,妹妹也说困。于是他让我们上楼睡觉。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在****。但却无力反抗。他们在饮料下了很多药。
第二天清早,我们身边放了很多照片。估计有三四个人****我和我妹妹。
我们随即被他们用一辆车弄到了上海,分别被弄到了两个舞厅被强迫**,我反抗他们就把我关进一间屋子毒打。我的一根肋骨都被达断了。我不是什么烈性女子,就开始**了。”
“我不想做了。”
“怎么了?”
“我心里有罪恶感。”
她嫣然一笑,沉默了。那时我断然相信,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笑。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控制不住地吻她。在带避孕套的时候她见我如此生疏问:
“你是第一次?”
“如假包换!”
返校只之后我立即与女朋友分了手。非要讲个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我喜欢那个妓女更多些。
物理课上黑板在吵粉笔在闹,我却一点困意也没有。窗外天色阴暗,陡然刮起了大风。我被一个飞舞的垃圾袋迷住了。我感觉她在和我跳舞,但不久便离我而去了。
下一节课我没上,跑到寝室等大雨降落。大雨很听话,一会儿便下了起来。于是抱起吉他在雨中写歌。顺便说一下,我喜欢在雨中写歌,往往有如神助。不幸的是我写的这首歌在学校流传开了,并一次次惹得我羞愧万分。
容容不知怎么找到了我,在我面前湿淋淋地声泪俱下:“你不要我了么?”我走过去整理她的头发:“恩。”
“为什么?”
“容容,记住我的话,以后不要再相信男人。”
我吻了她一下便下了楼,在雨中可恨地扬长而去。
两个月以后我为弄清生命的真相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我想离开这里可以靠近它一点。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像他们那样地生活不是生命的真相。
我在朝阳区的一个老四合院住下,每天去附近的地铁通道里唱歌,每当通道里空旷的歌声响起,我便失去了整个世界。我总是闭着眼睛唱自己的歌,偶尔有人驻足我会睁开眼睛冲他微笑一下,然后继续闭上眼睛。
晚上在屋子里练琴的时候突然门响了,一开门两个仙女站在我面前。
“你好,我叫吴丽,这是我女朋友孙培。”
“你们好,有什么事么?”
“我们住在对面,听见琴声来和你打个招呼。”
“哦,进来坐吧。”
“你是哪里人啊?”吴丽说。
“我是河南的。”
“巧了,我们也是河南的,我见你每天背着个吉他出去,你在哪里演出?”
“地铁通道。”
“你怎么不找个酒吧呢?我听你弹得还行。”还是吴丽说,事实上一直都是吴丽说,孙培一直沉默着。
“我怀孕了”我说。
“啊?”吴丽张了张嘴看看孙培,孙培终于迷惑地说话了:
“怎么讲?”
“我怀上了一颗自由的灵魂,我必须把它养大。”
孙培笑了,这一笑竟让我想起了许鹃,吴丽说我真恶心,我们便都笑了。接着我们说了一堆废话就算认识了。
孙培和吴丽是女同志,都在一个叫东北丰的酒店打工,酒店有寝室,但她们不住。吴丽很开朗,孙培眼里却总有抹不去的忧伤。顺便说一下,我不讨厌同性恋,有时他们会让我十分好奇。我时常想,如果中国有50%的人是同性恋,那么人口问题不就解决了?
两天以后的晚上,孙陪自己来找我,我问她吴丽呢?她说吴丽回老家了她还告诉我他们分手了,原因是吴丽怀孕了。
孙陪在笔记本上看我的博客,我在床上练琴。
“你想****么?”孙陪看着我的博客说。
我没有说话,如你所料,孙陪成功地诱奸了我。我感觉它很久没有和男人zuo爱了,她没命地乱叫,我几分钟就败下阵来,而她还意犹未尽的样子。
我得谈一下诱奸。首先诱奸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达到目的,对方是同意了,你不用像那些笨蛋强奸者一样日夜担心被判上几年。成功之后如果对方愿意你还可以继续与之保持关系。那么你就可以省去大笔钱财,以及额外的恋爱。
我穿好衣服准备出去,孙配叫住我:“你去哪?”
“河边。”附近有条穿城河,我每天晚上去哪里抽烟
“去干嘛?”
“抽烟。”
“要不我陪你去吧。”
“不用了。”我关上了门
我坐在河边看水里的月亮,想着一个女人的生日--8。15。月亮圆得让我讨厌,它让我想起了轮回。圆,没有开始没有终结,只是不断地重复。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可怕,跟轮奸一样一样的。
“姜琳。你还记得我么?”我自言自语。
五年级时她喜欢我,我却一直不知道。六年级我喜欢她她也不知道。为了改变这种混账情况我我开始给她写情书,写诗,写歌,尽我所能。我当时特爱写诗,我写了一大堆诗发表在了校刊上。为的是能让她看见。我想在我情书的暗示下她能知道这是写给她的。不怕你笑掉大牙,我现在就列出其中的一首:
最后
最后
我还是在漫长中丢了你
像八月里刚长出的满月
清风一掠
掉在地上碎了一地
无意
捡起一块放在嘴里
无奈
满是心酸与泪水
于是我懂了
一个人快乐
不如两个人伤悲
我怀念过去小米加步枪的幸福
最是那轻浅一笑
给了我推翻一切的无限动力
我不要谁的妖艳妩媚
更不稀罕谁给我荣华富贵
因为我有灵动的一双手
支撑着你我将越过的所有重围
如果你还能承受那么我要说句更酸的话:
“真爱过才会懂。”
我一直想不通她为什么她再而三地拒绝我,唯一让我怀疑的是五年级她喜欢我的时候,我老向她借钱。有一次向她借她不给我问为什么,她撅起小嘴说:
“你都不还。”
你猜我怎么说?我说:“不借****你!借不借?”
她哭了,却没告诉任何人。
“给我来支烟吧。”孙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我身边。
她抽烟的样子美极了。我一直看着她不说话。突然她纵身一跃,把月亮砸得粉碎!我赶紧跳进去把她捞了出来。
“干嘛呀!”我朝她大吼。她立刻趴在我身上大哭起来。我赶紧抱紧她。我可不想再救她一次。
我带她来到一个叫胖丫的夜摊吃东西,巧的是我们都不顾旁人的眼光,一副准备把一副暖干的样子。
“说吧,你为什么要跳河?”
“你知道一个同性恋活在这个世界上都要面对些什么么?”她眼里闪着泪花。
“可你现在不是了。”我坚定地说。
“不,我不喜欢你。”她比我更坚定。
“听着,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为了爱情,没有什么值得你为了它而放弃生命。生命太美了。”
“美?我怎么看不到?”她有些亢奋。
“因为你看到的是人,而不是这个世界。小时候你觉得星星很美,可你现在不觉得,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她埋头吃了起来,我抬头看北京的夜空。来往的飞机遮住了星星。
回到四合院孙陪说要和我一起睡,她说她害怕。
“你想再****一次么?”孙陪上chuang脱了衣服说。
“不想。”我说。
“真的?”
“来吧。”
晚上我又做了些奇怪的梦。要是把我的梦和那些恐怖片变态片比,我准能拿到奥斯卡提名。我记得当时我梦见一群美丽的人头悬在半空排着队给我**。或哭着或笑着,或面无表情。甚至还有唱京剧的,千奇百怪。
醒来孙陪已经不在了。她屋子锁着门,现在离上班好早。我问房东,房东说她退了房,刚走没多久。我陷入了某些迷惘中。“为什么与我zuo爱的女人第二天有会离我而去呢?”我想这是个问题。我突然看到了真相,那就是一切都在结束。我想不久以后时间也会结束。那是世界的终点。
电话在屋子里响了起来。回到屋子拿起来一看是我妈。
“回来吧儿子,你奶奶快不行了”
我挂掉了电话,疯了一样收拾东西,心里不停地喊“奶奶,等等我,等等我。”
在火车上我不停地祷告:“上帝,奶奶信了你一辈子,她是我见过对你最虔诚的人。你这个丧心病狂,现在你要杀了她么?我会让你死得很惨的!我发誓!”
尼采告诉我,上帝早就死了。事实就是这样,我回家奶奶已经入了棺。
两个月以后时间愈合了我的伤口,却留下一道永远的疤。如果你失去过最爱你的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伤口会变成抹不去的疤。
这两个月在家什么也没干。为了不再腐烂,我打扮了一下去了琴行,给老师弹了几首在北京写的歌。听完后他建议我搞一个乐队。乐队?简直棒到了天涯海角。可找谁呢?
两天之后我的三个朋友,广志,营垒,郭朴和我巧妙地达成了共识。我们在营垒家的商场仓库找到了可供排练的地方。可还差一个键盘。广志说他有人,他打了个电话我们便在琴行等那个键盘。就在我们快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个美女出现了。广志站起来介绍:
“这是我女朋友姜琳。”
她看到我也是一句话说不出口,三个人都在纳闷我们为何死死地盯住对方。气氛奇怪到了极点。为了打破这中局面我站起来说:
“最近怎么样?”我很不自然的说。
“还好。”声音几乎听不见。
“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太好了!我们还等什么呢?试试吧!”广志拉着走不动的姜琳叫我们开始,我们选了首张炬的国际歌开始在琴行排练。默契出奇地好。
真好!我是指老天真对得起我。突然就给我我一个由三个好朋友与一个我喜欢的朋友的女朋友与我组成的乐队。
晚上五个人乘营垒的车吃庆功宴。席上我不停地喝酒。由于喝得有些过分。朋友们都劝我。营垒问我怎么了,我看着姜琳说:“高兴,高兴..”然后又是一饮而尽。
吃完饭我们都没有散的意思。天空中下起了小雨,营垒说:“下雨了,我们去漂移吧!”
四个人面面相觑,然后就是一阵欢呼。
我们在营垒的“赛车”上高唱《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我们真的起来了,在一个拐角由于飘得过长直接撞到了墙上,还好撞得轻,营垒还能把我们一个个送回家。
介绍一下营垒。他在某些方面和我如出一辙,我讲件事你就明白了。
那次我们在一个叫男孩女孩的酒吧喝酒,对面坐着一个穿超短裙的美女。营垒一直假装不经意地往美女下面瞟一眼又瞟一眼。有趣的是被那个美女看见了。等到瞟第N眼的时候美女猛地一张腿,营垒噗地一下喷了我一脸啤酒。我说了声操赶紧去了洗手间。后来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说他没出息,他说:“操!你要是看见没穿内裤的美女冲你一张腿试试!”
我不说话了,因为我要是看见肯定比他喷得还厉害。
提到内裤就不得不提到姜琳。
六年级时我坐在前后隔两排左右隔一条小路的后面没少看她的内裤。那时她特喜欢穿小而且紧的上衣,一坐下就会露出五颜六色的内裤。我说的不是一条什么颜色都有的内裤,而是很多内裤。她的内裤一天一个颜色,有时甚至一天几个颜色。那时我认为她要不是洁癖就是内裤癖。不知道她改掉了这个毛病没有。我可以没事看看。
第二天我们把鼓,贝斯,吉他,键盘,音响从四面八方运到仓库排练。排练时我看了几眼姜珍被广志发现了,他弹错了很多次。
休息的时候广志递给我一罐啤酒坐在我身边说:
“昨天我问她你和她的事了。你不该这样,弄得你们都痛苦。”
“她跟你我放心!”我拍了拍广志的肩膀。
“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广志的样子看起来有些内疚。
“好啊!”我装作兴奋地说。
时针不停地转下去,排练成了我们每天晚上的习惯。吃夜摊也成了我们的习惯。出乎所料的是我和广志以及姜琳的关系就这么保持了下来。只是我仍不怎么跟姜珍说话。
有天散伙后营垒拉着我去拼魔兽,几盘下来我已经被虐的从头爽到脚,说什么也不玩了。营垒就上了浩方继续去虐人。
我在群里看见一个小鬼写到:“摇滚乐对我来说是心灵的救赎。我笑了,笑得很轻蔑。倒是有个人的话让我很赞同:“摇滚乐?摇滚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自己。”
这句话推而广之对所有的爱好都适用。是的,爱好不重要,重要的永远是我们自己。可我们真的重要么?我是指在这个有六十亿人口的地球上,也在奔流不息的历史中。我看只能把重要关进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让我们存在的意义无限缩小,直到趋近于零才能谈得到重要。当然这都是些废话。
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我回头一看是姜琳。我装作平静地问:“广志呢?”
她没正面回答我却说:“你出来一下。”然后就自己下了楼。我下楼见她在月光中抽着烟,街上的万物都已逊色。
我站在她面前说不出话来。
“初中毕业后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她把烟灰轻轻地弹掉。
“你不觉得可笑么?如果我拒绝你那么多次你还会来找我么?”我也点上了一支烟。
“那你现在还喜欢我么?”她眼里闪出一丝忧伤。
“你觉得现在说这些对广志公平么?”我大口地抽了下烟。
“回答我!”她的样子很认真。
“喜欢!又怎么样?”我完全像是在和仇人说话。
她眼里闪出些泪花,默然地走了。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想到了什么,喊了声:“要我送你吗?”她头也不回地摆了摆手。我就这么定定地站在原地两小时一动不动。瞳孔里一直回放着她的背影。
又一个人拍了我一下,是营垒。我没有回头。他探着头看到我湿了的眼眶问我怎么了,我说我想喝酒,于是驾车来到白娃烧烤点了两件啤酒。和营垒喝酒我坐了两件事:一饮而尽和一吐而尽。对!我把我和姜琳的事全告诉了他。于是营垒又开始前卫起来:“现在知道女人多麻烦了吧?跟我好吧!”“去!”我说。“俗人!”营垒不屑地说。这是手机里来了条短信:
“初中你的情书被我爸看到了,他打了我一顿。并说再发现连你一块打。可上高中我为你选择住校等你到现在你都没来找我。我遇到了广志。他很好,可我不喜欢他。我随时可以和他分手。”
这短信让我陷入了两难。广志是我最好的朋友,姜琳是我苦苦爱了七年的女人,我该怎么做?
这个问题被广志解决了。当姜琳向广志坦白她喜欢我而不喜欢他的时候广志说无论怎样他都支持她。姜琳说他们才大一,广志以后可以遇到更好的。这中情况真出人意料。
姜琳的父亲,原来是他。我早听说过这个恶徒。赌博,酗酒,吸毒。简直无恶不作。姜琳的妈妈就是被他逼死的。
初中时一节语文课上姜琳被叫出来,在门口见面就是一耳光。要不是老师拦着,她肯定还要挨打。原因是姜琳把他的毒品倒进了马桶。
第二天我们照常排练。只是不停地出错。郭朴把贝斯一扔:“操!你们都傻了吧?不想干解散!”然后就愤然地出去了。广志说:“你们应该在一起的,我和姜琳本来就不合适。”营垒把鼓槌一扔:“一群****!”然后也出去了。“愿你们幸福!”广志把吉他安静地放在沙发上。
“带我走把。”姜琳平静静地说。
“去哪呢?”我也很平静。
“离开这,越远越好。”
“北京吧,我正打算回去。”
“好。”
我们走了,乐队夭折了。巧的是我们的乐队名字就叫夭折。2008,我失去了最爱我的人,得到了我最爱的人。我已不在乎真相是什么。我在乎的是,我依然在路上。
下了火车我们直奔原来的四合院,可是已经有人租了。于是住进了一家旅馆。我先去洗了澡,出来看见姜珍正在用打火机烧一个铁勺子,****和水已经变成了黄色的液体。她身边还放了一次性针管和皮筋。我上去把勺子夺过来,并把针管扔在地上踩得粉碎。她尖叫起来:“你干嘛呀?”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说:“说!你吸毒多长时间了?”她说两年了,我立马去翻她的箱子。她拼命地来我竟然跪了下来拉住我的腿求我,我仰天长叹一口气,转身抱住她的头流下了眼泪。我知道这不是她的错。突然我一把推开她,去翻她的箱子。从里面找到十几支一次性针管和一小包****。我拿出一支针管喊:
“这东西很爽是吧?给我也来一针啊!啊?”
她不住地摇头,我把她反锁进浴室。学着电影里注射毒品的样子给自己来了一针立刻倒在了床上。身体开始抽搐,开始产生一系列幻觉。我看见奶奶在向我招手,墙上落满了蝴蝶,地上我小学时养的京巴在追着尾巴转圈..感觉是我经历过的最棒的******乘上一千倍。我真的飞了起来!我感觉自己在太空,随时都能到达任何地方。心里开始喊:“我要zuo爱!姜琳,我要你!”
我打开姜琳一直在拍的门,上去就是热吻。她推开我去注射。我靠在墙上慢慢滑落,嘴角挂着邪恶的笑。等她注射完她晃晃悠悠地走过来骑在我的胯上把我的头按进她的胸部开始疯笑起来。然后就是zuo爱,疯狂地zuo爱!要是这间屋子不隔音,那么全世界都听得到。
第二天醒来发现床头柜上有张纸条:
不要再找我。不要再吸毒,不要再相信女人。
我彻底崩溃了。打电话关机也打了半小时。紧接着是莫名其妙的平静。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再失去任何东西了,我彻底一无所有了。
再找到一个民房租下已经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躺在床上特别,非常,以及极其地想给自己烧上一针。连打扮一下都没有就直接奔三里屯。零八奥运禁毒闹得很凶,我只能坐在吧台边喝酒。以此试图来击倒刚染上的毒瘾。
一个美女朝我婀娜地走过来。我看着她产生了姜琳走过来的错觉。直到她妩媚地跟我打招呼说:“帅哥,看什么呢?”我才清醒过来。谁都知道我现在太需要发泄了。我需要为自己找一个出口。直觉告诉我她就是我今晚的出口。我往前把头探到她脸前说:“看你呢,****!”
“呵呵,看起来不像本地人呀!”她好像很得意地搔首弄姿起来。
“河南的。”我坐好把身体转向吧台,她便在我身边坐下。
“河南人可不怎么地呀!“她****地说。
“好人你要么?”我不屑。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愿意给我咯?”
“是呀,我巴不得****你呢。”我也****地说。
既然都****了,那么条件成立,警察都无权过问。我们来到她的车里,她把车开进一个阴暗的角落停下。我吻着她在她的上三路摸了一分钟后开始往下攻。摸着摸着就到了关键部位,但一个我非常熟悉的东西被我摸到。干!这家伙是个变性人!我跳下车去掀她的车。掀了几下掀不动便开始用脚踹。她打电话报警我还是踹。
我可能这辈子都买不起法拉利,可这样踹法拉利的人也许不多。想到这我心里平衡了,昂首阔步地打了辆的逃之夭夭。
回到住所我拼命地刷牙。还是禁不住地恶心。
躺到床上看球赛。看了半小时阿森纳竟一个球也没进。关掉电视用枕头蒙住头睡觉,出了一头汗。又从浴室出来时拿出吉他写哥:
变性人是最强悍的人
因为她有最强悍的吻
她的****是两座坟
里面住着哈姆雷特和贝多芬
变性人是最强悍的人
你可曾吻过她最强悍的唇
她的老二是火车的轮
你握住就会明白卧轨有多残忍
哦变性人..
我把吉他往床上一扔说了声操便打住了。睡觉!再睡不着我也得睡。这绝对是我最难忘的一天。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寻找两样东西---姜琳和毒品。意外的是我没有找到毒品而找到了姜琳。
既然她想离开我,那么附近肯定是没有希望了。现在她已经换号了。她要谋生就要工作。在中国对于吸毒的女人来说。如果没有有钱的男人,那么她一半可能就是妓女。顺便说一下,北京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这里暗潮汹涌,不知毛主席身边有多少妓女的脚印。那些妓女可能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在的,更有可能是未来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我在一个公厕墙上看见有人用粉笔写道:同性玩130XXXXXXXX。于是突发奇想地趁没人跑到女厕用粉笔写上:本人急需妓女,请大家电联158XXXXXXXX。一天以后就有妓女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她我的住址晚上她便送上门来。
我正在看电视,门外响起了敲门声。一开门她便说:“有烟没有?”我说在屋子里,她便进来了。她扭着肥臀径直走到桌子变抽出一根烟点上不客气地说:
“你屋子这么乱,就这么小一张床我们站着搞么?”
“我付你嫖金,你不用跟我搞。你把你知道的**场所都告诉我就行了。”
“年纪轻轻的不会是条子吧?”她带着一股很走味的京腔调戏道。
“你说就说,不说现在就走人!”我真看不惯她那装逼的德行。
“还挺个性。北京的**场所等于中国人口的平方根,我卖过的场所就是你的**数。”说完用嘴把烟头翻进口腔朝我一瞪眼下巴一紧嗤地一声烟灭了。而她好像还很爽的样子。随即从鼻孔里吐出两条烟柱。
看来我看错人了。她绝对不是一个装逼的人。她根本就是一个神经病。我赶快把她轰了出去。坐在床上我依然惊魂未定。我给自己点支烟就着茶喝。喝完躺到床上开始想她说的话。北京的**场所那么多。我真的能找到她么?她真的去**了么?她还在北京么?我陷入了更深的迷惘。还有就是我没钱了,我得工作了。
我没有再去地铁通道,那根本养不了我。回头看看那其实是一种消费。我来到孙陪以前工作的场所做起了服务生。毒瘾已经没那么强烈了,烟瘾却越来越大。一定会有人问为什么我不去唱酒吧。不是我长得丑,不是我唱功差。真正的原因是我在梦想面前根本就是一个****。我追逐它,我恋慕它,同时我又害怕它。我怕它破碎。于是我沉浸于追逐的状态。不断地接近却从不触碰它。
在值夜班的一天晚上,酒店没有顾客。同事李天把吉他拿来让我教他弹琴。我教了他几个简单的指法让他先练手指。一男一女进来点菜。我把菜上到他们桌子上客气地说了声慢用就又去教李天弹琴。一会那个男的走过来想听我弹歌。我说给你弹个我自己写的歌吧他说好我便把在学校写的那首歌弹给他听。没料到他也说不错。他说还有没有了便把在北京写的歌弹给他听。这时那个女的也走了过来。我正在唱那个男的对女的说:“看,他自己写的歌。”那个女的用她的惊奇给了我赞扬。这时主管走了过来说:“不要再弹了!”女的说:“为什么呀?人家给你拉生意你还不让人家弹?”主管霸道地说:“不许弹!”我把吉他放下不语。那女的对男的说:“刘猛,把电话留给他。”李天掏出电话在旁边记着,然后她又对我说:“不要放弃,姐回头给你出唱片!”然后就愤然地走了。刘猛说加油然后也走了。
第二天我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刘猛。
“你好,我是昨天那个服务员。”
“恩,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做什么的。”
“我是吉他手,她是我们的经济人。”
对于梦想是否能成真我有自己的理解。我的理解是它不重要。拿我们有的去换我们没有的,到头来竟发现我们真正想要的竟是我们曾拥有的。这是我生活得经验。在青春这条路上我也有过一些小小的成功。但我一次次地发现成功根本不是追求时想的那回事。成功更多带给我的是失落而不是满足。所以我喜欢那些追逐梦想的人却看不起那些成功的人。我认为成功的时候失去的最多。
我把号码删掉,把头探进寝室的水池中用凉水冲了会头,看着镜子用我麻木不仁的脸挤出一个掩耳盗铃的微笑然后穿上我的翻绒皮鞋上班。
十点半的时候经理让我去送外卖。从地底通道出来,阳光把我砸得体无完肤。我朝太阳比脸个开枪的手势。我想也许我能把它打爆,从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女巫说:活着的时候要好好活,因为我们会死很久。我说也许我们活不到死的时候,这条路到处都是尽头。
保安拨通了户主的电话,户主让我进去保安就让我上了楼。电梯上升时的眩晕让我感到不安。我想起了她,我想起她一贯的沉默和偶尔的天真。她是时常仰望天空的人。她说她看的不是天空,是孤独。我知道,她的孤独比悲伤更悲伤,在时间的长河中已被冲刷的无可救药。可能是她母亲的离去造成的,但她父亲才是我所知道的真凶。我所不知道的,也许是类似于我的迷惘。就像我的京巴往沙发上跳碰到了桌子而害怕地离我而去所感到的无奈一样,这种迷惘到处都是。我还知道,他父亲曾强奸过她。当我与她商量我是否能杀掉她父亲时,她已经用几丝轻蔑回绝了我。我知道,那是她在万千无奈中抽丝剥茧的原谅。她已不想与过去再有任何瓜葛。
电梯门开了,我走到户主门口按响来门铃。开门的是一个干净而儒雅的男人。
“你好,这是您要的外卖。”我客气地说。
“恩,谢谢。”
这时一个女人穿着浴巾走了过来,还没被接住的外买被我洒了一地。这时那男的立刻目露凶光喊:
“****大爷,你干嘛呢?“
我抬脚踹在那男的老二上,他顿时捂着老二倒在地上,我把他的头狠命地往地上踩。姜琳跑过来推着我喊:“建文!住手!她是我男朋友!”那男的操起哑铃捂着老二就要砸我。姜琳又推住他喊:“海涛!住手!他是我男朋友!”
接下来我想你们都知道要发生什么了。除了面面相觑还能怎么样呢?我冷笑着往后退,退到门外咣当把门碰住。我想起了广志的话:祝你们幸福!在电梯里有一滴泪滑落。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滴泪了。我没有从单元门出来,而是很牛逼地翻墙而出。一个小男孩冲我喊:“哥哥你真帅!我喜欢你哦!”我冲他伸出拇指食指和小指,呵呵,哥哥也喜欢你呀!
我辞掉了饭店的工作,因为我已经开始咳血了,父亲就是在部队患肺结核死去的,奶奶也是肺癌。我想也许是我离去的时候了。我没有去医院,只是吃了些止咳药。因为疾病和梦想一样,它们不重要,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决定用可能的最后的日子把北京看一遍。
阳光依旧刺眼,一直刺进我心里。街上依旧喧嚣,一直喧嚣到意外。我背上我的吉他,背上我真正的恋人。
又是秋天了,街上有稀稀落落的树叶。我踩在这些叶子上,聆听这个世界最后的寂寞。我只能往前走,这次我要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尽头。
我看到一个精神病双手合十搓着十块钱在马路中央一次又一次地抛而不屑来往车辆的笛声和围观的人群。我看到民工脖子上挂着写有“房水”的纸板和正在讨价还价的雇主。我看到喊着“别跑”的城管和四散而逃的小贩。我看到打了男友一巴掌愤然转身的女孩和她转身后的窃笑。我还看都要钱的乞丐和不给钱的路人。我更看到与我擦肩而过的姜琳和她儒雅的男友。我还看到..
算了,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只看到掠过整片寂寞的飞鸟和荒谬的我自己..
作者:涅槃
(本故事纯属虚构敏感情节为写作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