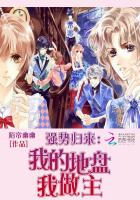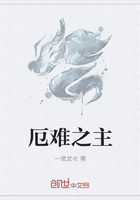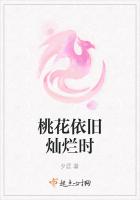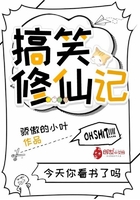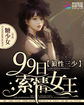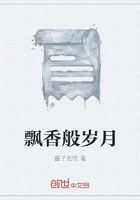市场经济越发达就越要求诚实守信。社会分工的日趋细密,必然伴随着广泛而频繁的交换。在现代社会里,绝大多数经济活动不得不采取“商业”的形式得以运作和展开,人们的绝大多数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要素都要从市场那里取得。不仅交换物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而且交换的复杂程度更趋增强。无论是商品交换、劳务交换,还是信息交换、服务交换,其交换的完成或实现,都存在着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导向要靠信用来保障。与这种广泛的社会依存性以及强烈信用需求相适应的,必然是信用关系的普遍化和形式多样化。如借贷形式的银行信用、赊销预付形式的商业信用、分期付款形式的消费作用、信用社形式的合作信用、以政府为债务债权人的国家信用、各种国际信用,以及日常生活中的保险、信托、租赁、信用支付手段(信用单、信用支票、信用卡等)都属某种信用形式。对广泛的市场交换来说,信用构成经济运转的润滑剂,不仅提高了交换的稳定性、安全性,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信用增加了市场经济运行效率。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并以信用的存在为前提。信用能使分散的社会资源得到更有效的组合,加速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转移,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保障。从经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人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使自己利益获得最优,那么这被称为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正如穆勒所说:“人类的产业活动和所有其他联合活动的效率,取决于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互信任,遵守契约。”这表明信用既有利于全社会信用效率的提高,又是经济行为的客观要求,也是公平交易、公正交易的表现。相反,如果一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是通过损害他人的利益实现的,那就不能给整个经济体系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带来任何改善。
信用降低了市场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包括搜寻交易对象的信息费用、同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达成协议的谈判费用,以及监督契约履行的费用,等等。
交易成本的支付在很大意义上可以看成就是寻求与确保信用的费用。一个社会如果人们相互之间的信用度很低,人与人之间缺乏起码的信任,就会大大增加交易双方时间、精力和成本的支出。在信用活动规范有序的情况下,交易费用大大降低,于是交易关系得以不断扩展,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得以提高。信用培育出经济主体间的长期的信任,节省了主体间的交易费用。在事前,交易双方由于信任,不需要付出过度的信息调查成本,并且不必设计过分复杂的交易契约,减少为获得交易机会而收集信息的时间、金钱。在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相互信任,避免了彼此间的猜忌和扯皮,从而减少了交易主体彼此的监督调查成本。交易主体恪守信用就会使契约得到执行,不会发生违约后的法律救济和自我救济成本,避免了违约造成的经济损失。
信用扩大了市场的范围和规模。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交易范围不断突破地域限制,并带动整个市场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市场秩序得以不断扩展的重要社会基础,就是借助于制度化或系统化的媒介,使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信用关系网络得以不断延伸与扩张。信用使经济主体在交易行为中彼此增加信任感和安全感,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使市场行为趋于长期化。经济主体追求长期利益的追求又会进一步导致普遍的信任。当市场主体认识到交易环境合作和信任成为主流时,出于利益的考虑,就会扩大生产和交易的范围,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与协作,形成一种经济扩展的秩序。正如马克思指出:“市场会扩大,并且会远离生产地点,因而信用必须延长。”“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同时,信用和竞争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扩大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产生了规模经济效益。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都是在信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信用能使人们将社会上分散的、小额的闲散资金汇集起来,投入到生产领域中去,加速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使原本单个个人或企业无法完成的经济活动通过信用合作的方式得到顺利进行,从而扩大社会经济活动的整体规模,分享各种规模经济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因此,从某种意义说,信用关系的半径,就是市场交易范围的半径;信用关系的网络延伸到哪里,市场交易的范围就扩展到哪里。
信用优化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经济学研究的新近成果表明,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是分析宏观经济的前提和宏观经济政策作用的对象。市场微观主体的市场交易和经济决策行为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整体运行效果和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信用对市场主体的投资与消费、生产与销售、供给和需求、劳动与就业都会产生积极影响。基本交易单位诚实守信既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又保证了市场信号的真实,为宏观决策提供了正确的决策依据。
信用带来了国际交往的收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信用给国家的整体带来好的形象,进一步促进国际经济交往。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表现出的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有助于提升国家的信誉。国家的信誉又会进一步巩固国家的经济地位,增强一个国家制度模式的影响力。此外,在国际交往中,国家的信誉与国内企业的信誉是相互影响的。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打交道过程中,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付款方面的守信,会积累国家信誉。同样,国家的信用度高也能够促进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国内企业的信用等级。
总之,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准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是一种资格,是一种信息产品,也是一种资本。对个人、企业、部门以至某一地区甚至国家而言,信用都是一种无形的资产和财富。自从有商品以来,无论市场交易行为采取多么复杂的形式,共同特征都是必然也必须要遵守交易行为自身的要求:信用。市场经济离不开信用,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与命脉。
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也就没有交换,没有市场。市场越发达越要强化信用意识;而信用意识越强,市场经济秩序就会越良好、越规范,市场经济就会越发展、越兴旺。
(三)信用:现代文明的基石和重要标志
信用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和重要标志。文明的实质是社会的进步、人际的和谐和人格的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社会信用秩序的扩展史。信用降低了社会交往和合作的交易成本,增强了社会的内部凝聚力,促进了人类合作秩序从血缘家族到部落文明,再到民族国家,直至全球文明的扩展。信用与信任是社会组织之黏合剂、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及社会系统动力。可以说正是凭着基于信任和信用关系的合作,人类文明才一步步地走到了今天。任何有损人类信任和信用的行为,都意味着文明的倒退。
社会信用水平同人类文明进步水平是正相关的。从信用概念的外延扩展来看,社会的信用水平与社会交往的普遍程度是成正比的。人们对社会信用状况越是抱有信心,就越是能够主动走出固定不变的交往圈子,积极扩大新的交往关系,增加新的交往内容。而社会交往关系领域、范围的不断更新与扩大,正是文明进化的重要尺度。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进化的步伐。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等各种要素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流动与合理配置,极大地提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效率;知识、价值观念及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使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彻底地摆脱了地域文化的限制,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创造力的提高。世界历史和“世界文化”的出现,当然是以资本的扩张和工业技术的突破为动力的,但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人类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必然地包含着信用关系在外延上的质的突破,即借助于非人格化的信用媒介,人类的信用合作范围得以由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扩展为世界性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已经从经济领域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信用关系所体现的平等的契约精神,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构建各种社会生活关系的基本原则。市场经济和经济信用关系的不断拓展,更是直接促进了社会生活关系“从身份到契约”的变革,进而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信用化的政治关系,产生了基于契约的现代民主政治,推动了人类政治关系由纵向的奴役,向横向的基于平等契约的委托代理的信用关系的转变。
基于契约的信用文化的兴起,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作为资产阶级解释国家起源和本质的主流思潮,其实不过是把经济领域的契约信用关系扩展到政治生活领域,是一种用社会契约的方式来说明国家和法律以及一切权利和义务产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学说。
在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视野中,公众同政府的关系,也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它内在地包含着一种信任和信用关系。一方面,公众基于对政府的信任而授予政府代理资格和代理权限,政府有义务和责任去尽心尽力地完成受托的事务。这种义务和责任是根据契约约定的,因而,对这种义务和责任的履行是政府守约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公众作为委托人也有守约的义务,公民的守信主要体现在守法、依法纳税、服从政府权威等方面。“在订立信约之后,失约就成为不义,而非正义的定义就是不履行信约。”如果统治者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依据契约原则,就是毁约;作为缔约另一方的人民因此也就理所当然地有权进行革命,推翻政府,重新选择自己的代理人。“政府不是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为了谋利就有权利去设或经营的店铺,而完全是一种信托,人们给它这种信托,也可以随时收回。政府本身并不拥有权利,只负有义务。”守信履约是政府最基本的行为准则。
在现代社会,信用不仅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撑条件,而且成为联结整个社会分工体系的纽带。在今天,一旦社会信用体系解体,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就会因此而全面崩溃。制度经济学家柯武刚、史漫飞写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与许多陌生的人和组织打交道,但我们却对他们的可预见行为寄予了很大的信任。在一家银行里,我们对其储备和管理一无所知,却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出纳员,并可能在数秒钟之后便将他的面容忘得一干二净。在我们以前从未进过的医院里,我们却会答应由医院中未曾谋面的医生给我们做手术。我们会向轿车送货商预付车款,而这些轿车却要在外国工厂中由根本不会与我们见面的工人们来制造。然而,在这些场合,我们都相信,我们肯定能得到值当的服务,汽车厂会对送货商履行其承诺。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都具备提供服务和商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为他们都受制于制度--对其不交货或蒙骗我们的机会主义动机施加的限制。”可以说,信用关系在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越大,社会生活秩序对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的依赖性就越强。
(四)信用:区域发展的软实力
信用是资源、是财富、是竞争力。一个地区的信用状况,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个区域对外合作的机会,决定了这个区域要素集聚的水平,从而决定了这个区域的竞争力。信用既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产业,既是一种软实力也是一种硬实力。提升区域竞争力,重点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区域集散力和文化支撑力,而这三个方面都与加强信用密不可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信用首先是一种人力资本。所谓人力资本,是指人自身中存在和发挥出来的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要素。人的信用意识和道德素质,是构成人力资本的关键因素。其次,信用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是现代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信用作为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方面,在市场交易中,企业信用是企业商誉形成和提高的基础和决定因素;另一方面,企业信用作为企业内在的一种无形的力量,激励着员工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的发挥,提高企业内在的效率。再次,信用还是一种社会资本。信用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运行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它通过弘扬一种共同的经济价值观,形成社会团结奋斗的凝聚力,激发和引导着人们积极的经济创造行为;它通过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选择,建立一种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伦理秩序,保障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它通过影响和制约一定经济制度的确立,对资源配置和经济效率产生重大影响。
近些年来,随着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加强软环境建设,营造区域竞争“软实力”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1990年,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软实力:世界政治的制胜法宝》中首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在国家层面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导向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即一种同化式的实力。如果说“硬实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