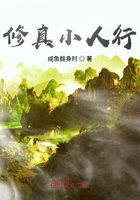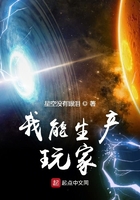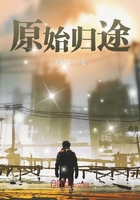转型时期社会信用关系的变化,隐含着一种深刻的危机,那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任危机。吉登斯认为,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这是一种随生活世界不确定性因素的大量出现,以及人们对生活世界的陌生感陡然增加而产生的精神焦虑。传统社会人们相互间的信任关系,建立在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生活场景和伦理规范之上,对这种规范的普遍认同,构建了共同体生活中一种强大的无形压力,迫使人们自觉服从世代相传的规范秩序。这种生活秩序,使得人们在作出某种行为选择时,可以对他人和社会的反应作出合理的预期,并由此产生一种生活的稳定感和自信心。然而,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与异质性,却使传统的熟人社会发展成为现代陌生人的社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共有规范的认同,造成了人们无法合理预期他人行为的心理紧张,并诱发出了大量的机会主义行为。
应该看到,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信用方式的深刻变革。英国着名法律史学家梅因在总结西方社会结构转型时曾经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一转变过程其实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描绘的,“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以身份为核心的高度凝固化的社会结构形式,每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先赋性地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规定,不同的身份先天地赋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行为准则。现代社会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与异质性,以及个体社会地位的平等化,决定了不可能再以某种先赋性因素为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只能以契约的方式来确定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由此给社会信用结构带来的一个深刻影响,就是信用的抽象化。与建立在熟人之间的关系基础上、与特定的情境相联系的传统信用关系不同,现代社会信任关系是一种抽象体系的信任,这种“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虽然“不可能满足个人信任关系所提供的相互性和亲密性的需要”,但正是这些抽象系统使得现代性社会获得了充分发展的可能,并使整个人类有可能在有效协调与控制之下进行普遍交往活动,使人类的合作秩序得以不断扩展。因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契约信用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人伦信用是两种有着本质差异的信用制度。社会信用体系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的这种结构性转型,即使在西方社会也意味着社会生存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在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如何实现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的变迁,这是我国经济制度和信用制度变迁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四)信用制度创新: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的必然选择
制度创新是实现从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的现代转型的基本途径。反观我国信用制度演变的历程不难看出,我国的信用制度建设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强制性变迁的背景下进行的,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人们求利动机的激发与制度约束的滞后导致各种反信用行为的出现。
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社会结构普遍而剧烈的转型严格地讲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开始的。强烈的赶超压力使中国不得不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转型历程压缩为短短的几十年时间。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转型是民族文化和传统社会生活秩序长期演变的产物。尽管现代抽象化的信用体系的建构不是一蹴而就的,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普遍的法律意识、契约意识毕竟也为现代抽象的制度性信用结构的建构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源。因此,西方社会即使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信用危机问题,但从总体上讲,还是较为顺利地完成了由传统的人格化信用到现代非人格化的制度性信用体系的过渡,形成了“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相形之下,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对于社会结构转型以及信用体系的转型都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传统的信用机制已逐步趋于解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社会阶层出现剧烈分化,人们的身份意识变得模糊不清,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按照自己的角色身份,沿着既定的生活轨道,按照明确的行为规范去生活;传统的依托于单位组织和政治化的基层组织的社会生活控制机制趋于失灵,社会自由空间急剧放大时,适应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制度体系却依然残缺不全,更谈不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并为现代抽象化和非人格化的信用体系的建构提供有力的支撑;市场主体的市场规则意识和按“游戏规则”出牌的行为方式还在培养之中;制度至上的意识,以及对制度规范负责而不是对长官负责的操作习惯,对许多政府官员来说都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问题这样,在传统信用机制逐步失灵,而新的非人格化的信用机制还处于艰难的培育过程中的情况下,全社会各阶层已经被充分撩拨起来的欲念,不可避免地诱发出了各种投机取巧的机会主义行为,诱发了严重的社会信用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0%,交易产品的价值也越来越高。随着市场的发展,对信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我国社会的信用状况却很令人担忧。当前信用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商业领域的信用问题,包括商业信用危机,其最直接的表现是“假冒伪劣”盛行(在实物消费品方面、知识产品方面、信息服务等方面)、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及合同违约和欺诈等;二是金融领域的信用问题;三是证券市场的信用问题,如财务造假、信息披露失真、内幕交易等,制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串通庄家做市,已经是上市公司心照不宣的“秘密”;四是消费领域的信用问题;五是社会中介机构的信用问题,如一些中介机构便利用其职能之便,欺诈消费者,沦为其他违信行为的帮凶,从中牟取暴利;六是政府的信用问题。当前的信用危机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政治领域,即政府信用问题突出。由于政府特殊的地位和职能,其失信危害要比公民、企业不守信大得多。因而,信用缺失现象已充斥在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使得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等均深陷其中。
失信行为的蔓延,加大了道德风险,导致经济秩序混乱和“市场失灵”,其危害之大、影响之深是难以估量的。一是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信用关系的形成和深化的过程。信用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根基,没有信用就没有高度发达的市场。由于信用缺失,企业、银行、政府、居民等各社会经济主体在经济交往中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一些企业、银行为避免风险损失不得不排斥信用、拒绝信用,信用经济得不到广泛发展,经济信用化水平偏低。二是增加交易成本。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市场失信、违信行为频频发生,严重挫伤了交易者的信任和信心,致使厂家不敢赊销产品。三是降低政府宏观调控的政策效果。
信用缺失,降低了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执行效果,导致“政策失灵”。四是经济发展质量受损,社会道德水平下降。信用危机带来的危害,从表面看,是企业成本增加,市场风险增大,投资和消费降温。从深层次看则是造成社会资源的配置失当和利用效率低下,降低经济运行的速度和效益,最终使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受损;更为严重的是使社会发展目标异化,人性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