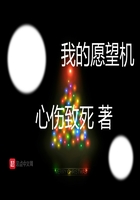某天上午,偶然在网上遇见了一个低我四届的小师妹,随意地聊起天来,自然就说起了我们一位共同的老师——郑传洋。
他是教网络新闻学的老师。因为平时课上得比较少,所以我对大学里的老师普遍没什么印象,郑老师算是为数不多的印象比较深的老师之一。
大学的前三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吃喝玩乐中度过的,每天把自己整得黑白颠倒、天昏地暗,直到大四开了这门课,他要求每个人开一个博客,如果到毕业的时候点击量能够达到一千就算及格——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什么是博客,但是既然这是及格的唯一途径,那就去写吧,于是最终我及格了,带着几百万的博客访问量,没等成绩下来就自己给自己毕业了。我那灰暗的、百无聊赖的大学时光,一秒钟都不愿意留恋。
离开大学之后,几乎没有再联系过任何人。我对大学的情感淡薄得有些诡异,反感得有些夸张:当年一个人孤单单背着书包坐上火车从石家庄奔到武汉,最后又是一个人孤单单背着书包从武汉回到石家庄,一来一去之间,四年的青春就这么流逝了,如同秋天的夜晚悄然飘落的一片黄叶,掺杂在一地的缤纷里,无声无息,而自己的年轮上面,平添了四个圆圈。
这次既然聊到了郑老师,我就顺便要了他的电话打给他。从小师妹的口中得知,虽然我如今已经毕业两年了,但他仍然把我视为他的骄傲——曾不止一次地向学弟、学妹们提起我,因此,我也多了很多来自母校的读者,虽然我并不认识他们。尽管这几年收获了很多虚名,但对于这样一份来自母校的温暖,还是觉得有些感动。
电话接通以后,从他颤抖的声音里能听出他的意外——大概他曾经希冀,但并没有真正相信我有一天会打电话给他。问候过各自的近况,情绪稍稍平静下来之后,他忽然说:“你的那门功课我给你打了满分,你可能不知道,因为那是你大学最后一门功课,那时候你已经毕业离开学校了。”
电话这边,我久久无语。
这是我大学里唯一一次满分,我不知道自己在以后的人生中还有没有得到满分的机会。记得小学的时候,家长、老师都是以“双百”来要求孩子的,那时候也确实得到过很多满分。上中学之后,满分作文成为向往的目标,凭借着自己的天赋,也得到过很多次满分作文。再长大,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忽然之间对自己没有了要求,好像一切都无所谓了:及格就能接受,不及格也能勉强接受。进了社会之后也是抱着有口饭吃就行的姿态,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看成人生的一大乐趣,在浑浑噩噩之中日复一日——当然,这不失为一种豁达的心态,但更多时候,这只是一个逃避无奈的借口——如果有可能,谁不想得到满分呢?尽管“满分”这个词在总有残缺的成人世界里更像是一个传说。在飞速逝去的时光中,日渐世故圆滑的我们,恐怕早已经将这两个儿时梦寐以求的字眼看成了某种需要嘲笑或是讽刺的代名词。
我想,在很多年之后,我仍然会记得这个两年前的满分,或许也是我成年之后唯一一个满分,尽管它迟到了两年,但足以在此后的人生中时时带给我激励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