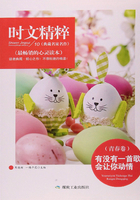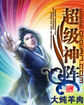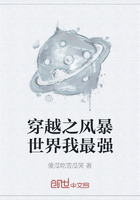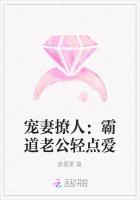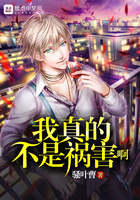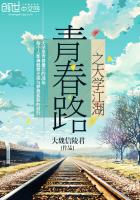潮中钓者
早晨4点40分醒来。枕上看见海天相连处闪着一道霞光,霞光越来越亮,海面上金波荡漾。十分钟就走到沙滩了,白沙细软,跟绵白糖似的。澳人三三两两在沙滩上走着,远处有更多的人在冲浪。潮水似千军万马滚滚而来,顷刻间又悄然退去,每一波都千姿百态,变化无穷。我靠近海潮,好几次被潮峰压倒,重重地跌在沙滩上。近处有个脸色黝黑的老渔翁,右手拿着长长的钓竿,左手正把一条银色的鳊鱼从钓钩摘下来,放进鱼篓。趋前一看,鱼篓里已经有好几条鱼了。趁他捏好鱼食又要去甩竿,我请他合了个影。潮涨潮落,万马奔腾,他如何能把得住钓竿?又如何能感觉到鱼来上钩?我想到欧阳修笔下的卖油翁。这里一定有什么玄机。沙滩出入口有自来水,我冲洗掉腿上脚上的白沙,便回来吃早餐。
悉尼港湾大桥
早晨6点半起床,走上悉尼港湾大桥。从北往南,大桥中央的钢铁部分,我走了一千三百六十八步。人行道在大桥的西侧,澳人穿着短衣裤、运动鞋在桥上跑步锻炼。年轻人跑得大汗淋漓,年纪大一些的多是步履轻健地走着。与人行道平行的另一侧,是自行车道。那边多是“驴友”,头盔下一个个猫腰蹬车,鱼贯而行。澳洲人特别喜欢健身,入澳半月,所见澳人无不健壮,脚下仿佛安着弹簧,颇能发力。即如耄耋老人,也是面色红润,眼睛明亮,精神抖擞,绝无萎靡之态。
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中间有八个车道,两条铁路。正是上班高峰,小汽车、巴士、摩托车风驰电掣,城际列车一辆又一辆呼啸而过。这座气势雄伟的大桥,始建于1923年,九年后建成。据说连接大桥全身钢板钢架的,有三千多万个铆钉,八十年间只换过十八个。从桥中间向下看,悉尼湾别是一番景象。蔚蓝的海水闪着金光,悉尼歌剧院巨大的贝壳浮在水面,仿佛在波光中翕动。
歌德的国度
经过十个小时的飞行,我们乘坐的国航747班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机场老旧,刚刚下了一场雪,天气清冷。出关后,汉诺威中国中心的一辆蓝色双层大巴,顶着寒风缓缓驶来。我们山西省行政监察与公务员管理培训团一行十四人,开始了为期二十一天的德国培训。培训日程安排得很紧,内容丰富,受益匪浅。这方面的收获,我已悉数写入参与起草的培训团《赴德国行政监察与公务员管理培训考察报告》。
此次出访,全团同志都是第一次到德国,我和几位同志又是初出国门,一股子新鲜劲儿。课余时间我们相约外出,去感受德意志,可谓目不暇接,兴会良多,略记于此。
去特里尔
上午9点离开宾馆,乘车向西,前往马克思的故乡——特里尔。这一带是丘陵山区,白雪覆盖着田野,灌木丛、乔木林错落有致,丛林上飘落的积雪煞是好看。山坡上的葡萄园,修整得像跑道一样整齐,似乎在向远方的客人彰显德国人认真和精细的品格。间或有一两只乌鸦,舒缓地扇着翅膀飞过。飞得很低,若是我们从大巴二层的玻璃窗探出手去,没准儿就会踩在谁的掌心来觅食。
眼前掠过一个又一个村庄,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尖顶教堂,那是村子里最高的建筑。似乎在告诉人们,教堂是这片村落的精神高地,掌管着人们的灵魂。临行前大哥建民送我一册赵鑫珊的《心游德意志》,书中对德国的乡村教堂有精妙的论述。偶尔还能看见谁家的屋顶上冒着白烟。
远处是风电场,轮叶在白色的地平线上转动。白色的太阳正穿越云层,出没无定,使得原本灰暗的天空,忽而露出怡人的蓝色斑块,灰暗的云层霎时幻化成洁白的云絮了。哦,欧洲的太阳,德国的太阳,特里尔的太阳。大家兴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像太阳一样,是挡不住的。”“特里尔的太阳出来了,欢迎从中国来的客人。”
到了,这就是特里尔。两千年前,这里是一座城堡,现在我们看到遗存下来唯一的建筑,就是青石堆叠的、在惨烈的战争中被通体烧过的“黑门”,据说被列为世遗了。穿过“黑门”往里走,圣诞节的气氛氤氲着,一座稍显热闹但绝不嘈杂的城镇。没有高层建筑,街道两边的建筑或粉白、或浅黄,洁净如洗。
一切都是有序的。汽车穿梭,听不见一声喇叭,更没有警灯闪烁,警报炸响。没有交警。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竖在路边,才一人多高,车辆行人,谁都能看见,自觉遵守。路边顺序停放的,路上顺序行驶的,满眼所见,大都是极普通的两厢家用车。偶然看见一块墓地,十字架也很低,墓碑紧贴着地面,虽在路边,却有一种宁静安谧的气氛。严谨、守法,低调、务实,不声张,不攀比,不炫耀,处处彰显着德国人的内在品质。
马克思故居临着一条小街,是一栋普通的三层建筑,中间有个很小的天井。每层都有展览,最后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邓小平等的介绍。介绍邓小平的,是一幅邓小平和朱德、彭德怀等人1938年初在八路军总部——山西省洪洞县马牧村的合影,看了不禁怦然心动。几天后我们在柏林,又冒着雨雪拜谒了马恩广场那尊一坐一站的马克思、恩格斯雕像,依然是怀着崇敬的心情。
莱布尼兹大学
汉诺威是下萨克森州的首府,五十二万人口,市区有几个城市小森林,形成天然氧吧,空气很好。每天我们去汉诺威中国中心上课时,都要经过那个小森林。
汉诺威中国中心位于一幢灰色大楼的底层,门口赫然挂着一块“孔子学院”的铜牌。从主人提供的一份宣传资料上了解到,汉诺威中国中心成立于1997年,它是一个公益性协会,隶属于州政府经济部和教育部,为中德之间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交流起着重要的作用。
17世纪,德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发现微积分的莱布尼兹出生在汉诺威。为了纪念他,前两年汉诺威大学更名为莱布尼兹大学。我们在暮色中参观了这所没有围墙的著名大学。莱布尼兹曾在下萨克森州倡导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并对孔子思想有过研究。汉诺威中国中心及其名下的孔子学院,继承了这一传统。
汉诺威孔子学院是同济大学和汉诺威中国中心联合办的。孔子学院有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教室,我们在汉诺威期间,每天就来这里上课。靠墙一排简易书架上,放着中文书籍,有二十五史,茅盾、老舍的文集,《汉语大词典》等。还有景泰蓝、屏风摆件、中国结,房顶上吊着两个小号的宫灯。学院还有一间图书室,大都是语言类的书籍,还有《鲁迅全集》,邓广铭治史丛稿,《中国大百科全书》等。
有一天课间休息,我敲开孔子学院办公室的门,向一位中国女士简单了解孔子学院的运作机制和日常工作。又从墙上的宣传画得知,今年孔子学院成功举办了蔡元培生平事迹展览、王安忆作品朗诵会。
勃兰特和俾斯麦
德国的中餐馆都有一些免费赠阅的中文报纸。有些明显是敌对势力的腔调,有些则值得看看。
有一天中午,我在一份报纸的显著位置看见一张黑白照片:一个中年人双膝跪地,神情庄重虔诚,他后面的人群惊愕肃立。照片的左上角有个标题——《震撼世界的下跪》。说的是1970年,上任不久的西德总理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献上花圈,把黑红黄的彩带整理好,然后凝视着纪念碑退后几步,在冰凉的风中,突然双腿下跪,表示深深的忏悔。第二天,勃兰特下跪的照片刊登在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上。三十年后,为了纪念勃兰特促进波德两国和解所作出的伟大贡献,波兰人把纪念碑附近的一个广场命名为勃兰特广场。
德国人的反思精神令世界赞叹。以此为镜,更能照出今天日本右翼的狰狞面孔。
德国的冬季,天黑得早。我们到汉堡那天才下午4时,却已是万家灯火的黄昏时分了。薄暮中看见一座教堂,翻译小单说,那是尼古拉教堂的废墟,二战中被盟军炸毁一部分,留下这废墟,为的是让后人记住战争的残酷。
汉堡是德国第二大城市,一百七十多万人口,也是德国最大的港口。易北河从这里向西北一百公里就入北海了。在港口,我们看见不远处停泊着一艘灯火通明、像泰坦尼克号的巨大客轮。来到市中心,湖边的圣诞市场煞是热闹。朦胧中看见一座高高耸立、气势非凡的雕像,翻译小单说那是在德国历史上可圈可点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他一百年前制定的世界上第一部劳动保护法现在还在施行。汽车正在拐弯,我急速地从大巴的玻璃窗望过去,只见那位矗立着的铁血宰相,正威风凛凛地注视着港口,注视着易北河,注视着百公里之外的北海和茫茫世界。
勃兰特和俾斯麦都是伟大的德国人。之所以堪称伟大,是因为他们生前能够把握未来,死后又能使历史变得鲜活可亲,让后人追忆。
在博物馆里
德国是汽车王国,课余时间,我们参观了大众、奔驰、宝马几个汽车博物馆。奔驰博物馆在山城斯图加特,几层楼高的博物馆称得上震撼、辉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1886年生产的世界上第一辆小汽车,还有第一辆卡车,第一辆公共汽车,深为德国的工业文明惊叹。另一家博物馆则让我们感到惊异。
那是在汉诺威的最后一天,我们在驻地听完弗瑞斯教授的课,乘车去汉诺威博物馆参观。刚进门,就被一种奇异的景象吸引住了:墙上挂着两两相对的大幅照片,相框里两幅照片都是同一个人,所不同的是,左面那个人看上去很精神,右面的则耷拉着眼皮。一问才知道,那耷拉眼皮的,是在心脏停止跳动的瞬间拍摄的。博物馆这样的展览的确独具匠心,若是给这个展厅挂块牌子,该叫“生死之间”吧。德国是哲学王国,这种展览举世罕见,发人深思,它使人们顷刻间警醒,更加珍惜活着的每一天。
在汉诺威博物馆,我们还看到战后重建时的艰辛。大家对战后靠两只手清理废墟的伟大的德国妇女,充满了敬意。
回收塑料瓶
在德国,我们所到之处都能感到,德国人做事低调,务实严谨,不尚奢华,极有秩序,特别遵守交通规则。夜晚极少看见景观灯、霓虹灯,路灯也很简单,办公楼、住宅区、宾馆饭店装饰简朴,大都是简易桌椅、简易沙发,一切都以实用、坚固、大方为宜。德国人诚实、守法,公务员永远成不了百万富翁。
从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总部出来,我们一行即冒着雨雪前往不莱梅。这是一次长途跋涉,出发前,翻译小单在超市买了一些零食、矿泉水,以备路上所需。每人拿到一小瓶塑料包装的矿泉水后,小单说,德国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为了回收塑料瓶,定了一条规则:一小瓶矿泉水,水卖一点二欧元,塑料瓶押金二点五欧元,任何一个超市都可以退塑料瓶押金。说完又叮咛大家,喝完水把塑料瓶放到车座旁边的白色塑料袋里,司机就收走退给路边的超市了。这规则真是了不起!
德国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给我们讲课的不莱梅大学教授多布瓦先生,参加“透明国际”组织的工作,并担任不莱梅地方组组长。为此他每年要向“透明国际”组织缴纳八十欧元会费。在他看来,“透明国际”组织的反腐败工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他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薪金拿出来投入这项事业。我不禁对这位高挑个儿、六十开外、举止随便、有些顽皮的老头儿,肃然起敬了。
离开不莱梅的前一天,又下了一场大雪。我们都担心是否会滞留下来。第二天上路后,大家的担心即刻被兴奋和吃惊取代了,高速路上的积雪居然全部被清理干净!就连联邦公路也清理了,偶然还能看见黄色的清雪车在清理路边的积雪。如此之高的公共管理水平,在国内是不可想象的。谁都知道,国内遇上这样一场大雪,高速公路早就关闭了。
一点缺憾
出国前就想,到了德国一定要设法去趟魏玛,瞻仰歌德的遗迹。我上大学时接触过《浮士德》片段,还买了一本《少年维特之烦恼》。1986年在蒲县买到一本《歌德抒情诗选》。歌德对中国的感情特别吸引我,那时就知道,在魏玛图书馆的院子里有一株银杏树,相传是歌德亲手栽下的,他为此还写了一首短诗《二裂叶银杏》。诗的前两节是这样的:“从东方移到我园中的∕这棵树木的叶子∕含有一种神秘的意义∕使识者感到欣喜。∥它是一个生命的本体∕在自己内部分离∕还是两者相互间选择∕被人看成为一体?”因为喜欢这首诗,我在一次远距离的旅途中,还给大家背诵了一遍,并讲了与这首诗有关的故事。遗憾的是,魏玛始终没有去成。听汉诺威中国中心项目部经理王原先生说,魏玛图书馆三年前被一场大火烧掉了,不知那棵银杏树是否幸免于劫。回国前虽在歌德故乡法兰克福逗留,终因时间紧,没去瞻仰市区的歌德故居。要说这次德国之行有什么缺憾,便要数这一件了。
不过,当飞机离开地面,我看着舷窗外渐行渐远的法兰克福,心里不禁默诵着《二裂叶银杏》的最后一节:“我发现了真正的含义∕这样回答很恰当∕你岂没有从我的诗里∕看到我是一,又成双?”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既是一体的,又是多元的。一百八十多年前伟大诗人的这种思想和情感,与我们的时代精神和世界愿景正相契合。
飞机升到万米高空,在夜色中飞向东方。
《山西日报》 2011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