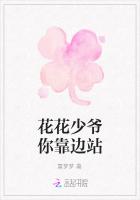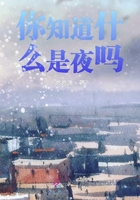吾以二月出都,河北之地,草芽未生。至吴而花开,至越而花落,入楚而栽秧,至粤而食稻。粤西返棹,秋老天高。至河南而木叶尽脱,归山右而雨雪载途。转盼之间,四序环周,由此言之,古今亦甚暂也。心不自得,而求适于外,故风景胜而生乐;性不自定而寄于形,故时物过而生悲,乐宁有几而悲无穷期焉。……生风云于胸臆,呈海岳于窗几,不必耳接之而后闻,目触之而后见也。然则自兹以往,吾可以不游矣。然而吾乃无时不游也矣!
其写登泰山一段,简约雅洁不让姚鼐,而情趣过之。文字较长,兹不征引。
这样一篇“奇制”不该入选吗?
吴雯(1644—1704),字天章,蒲州(今永济市)人。本卷收他三首诗,皆从方志中得来。
本卷编者似乎对方志比较青睐。书中有名有姓的作者五十八位,所选诗文得自方志者就有二十六位。吴雯之外,还有于成龙、范鄗鼎、陈廷敬、孙嘉淦、杨笃、杨深秀、常赞春、王用宾、景梅九、景耀月等。
一般来说,只有阅读著者的大部或全部作品,才能摸清其创作理路,感受其风格的形成及变化,最终选出其代表作。倘不看著者的诗文集,径从方志中抄出,倒是省去许多麻烦,但恐怕为一地之偏的方志所蔽,终致采择失当。若著者的诗文集确已无处可寻,自应采方志所录,聊备于无了。
吴雯的《莲洋集》收在四库全书,山西省图书馆、山西大学图书馆均有藏本。朱彝尊在《莲洋集》卷后题诗曰:“藉甚吴郎大雅才,赋诗不上柏梁台。”近人常燕生《山西少年歌》更称“莲洋何必逊渔洋”,渔洋即王士禛。王渔洋本人也很佩服吴雯,曾说:“余与海内论诗五十余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者终属天章也”(《分甘余话》卷三)。又说:“吴天章(雯)天才超轶,人不易及”(《古夫于亭杂录》卷五)。
这样一位诗人,若是从他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莲洋集》入手来选,该不会仅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首吧?
不妨做个假设。得自永济县志的那首《永乐早发》可以不选,换成七绝《题园壁芦雁》:“斜阳芦荻隐寒烟,接翅汀洲自在眠。只待晓风轻振翮,长鸣依旧傍青天。”清新自然,健朗劲拔,诵之可喜。前引朱彝尊题诗,后两句是“翻飞恰似横汾雁,几度秋风上苑来”。“横汾雁”这个意象,大概就直接得自于《题园壁芦雁》。当然这极可能只是笔者一私的偏爱,未必选得。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应从《莲洋集》两千首诗中去选。
倘能这样,即使只选三首,情形也会比现在要好一些。何况在有清一代山西诗人中,选吴雯总不该比祁隽藻(八首)、陈廷敬(七首)、裴晋武(五首)还少吧?
有些著者的诗文集虽然难找,但还是有一些不错的选本可供采择,并非只剩下方志一途。像民国时期的王用宾,《山西文史资料》就刊发过他的诗词选集;景耀月的诗文,胡朴安《南社丛选》也多有收录。
关于景耀月,本卷从《芮城县志》选出《授大总统莅任并致玺辞》。此文确是民国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献,收入方志足以彰显景氏本人乃至一方人的荣耀;但文学意味鲜寡,编在一省的文学大系中就未必允当了。虽然只是五百字的一篇短文。
再说选人之失
冯婉琳(书中误为“冯婉林”)是本卷所选唯一的女诗人。其实康熙、雍正年间还有一位著名的女诗人,也应入选。她叫田庄仪,号西河女史,汾阳人,著有《庄镜集》。
田、冯二氏一在清初,一在清季,堪称“闺门双璧”。没选田庄仪,要算是一件憾事。
本卷所选的民国七位作者中,杨韨田似不应入选,郭象升则最不该失选。
杨韨田民国初年(1912)在家乡闻喜当过一任县知事,他的父亲是“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本卷介绍,杨韨田的文治,便是卸任后“继先君之志”,修了一部《闻喜县志》,并援例写了一篇序。仅此而已。本卷概论称“其诗文也有过人之处”,但是我们见到的,只有这一篇虽清通、却平庸的《闻喜县志序》。
民国初年兴起一股修志热,郭象升曾作《山西各县志书凡例》,提供了修撰新志的范式。若以杨韨田序文为衡,则彼时修志各县,皆可提供一篇现任或前任县知事的即或平庸、但尚称清通的序文。或者因为他是杨深秀的儿子,才要选上?这规矩当然不应有,若说有,则傅山的儿子傅眉必得入选。傅眉“凡所为诗,古近体数十百首,皆不事吟风弄月之致,流漾篇中,如道如禅如逸人。”他死后,傅山作《哭子诗》十四首,谓“吾诗唯尔解,尔句得吾怜。俯仰双词客,乾坤两蘖禅。”在诗文上,杨韨田显然难与傅眉相匹。若是杨氏父子泉下有知,亦当同意拙见,不以为忤吧。
郭象升(1881—1942),字可阶,号允叔,晚号云舒、云叟,晋城人。曾任山西大学文科学长、山西省立教育学院院长等职。学问淹贯古今,是近现代著名的国学家、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家。在民国初年山西学界和文坛是一位领军人物。
关于郭象升的学问和文章,笔者另有专文。这里只简要介绍他的三部著作。
一是《郭允叔文钞》。这是他最早的一部诗文集,收文八十一篇,诗五十四篇。集中名篇佳什俯拾即是:《黄克强先生墓石刻文》《蔡松波先生墓石刻文》《故燕晋联军大将军吴公之碑》《振素庵诗集序》《山西全省天足会公启》《太原市上购书歌》《刘申叔先生游晋长句赋赠》等。《振素庵诗集序》是为南社诗人蒋万里诗集写的序,数十年后仍引起学者的重视。1959年,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诸先生,从《民权素》第十四集中将这一篇选出,编入《近代文论选》。
二是《文学研究法》。这是一部专著,分文体篇、文心篇、文派篇、文选篇。此著是郭象升纵横才气的一次井喷,为郭象升赢得极高的文誉。“山右第一才子”“中国古文殿军”,种种赞誉潮水般涌来。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近年仍将郭氏《文学研究法》,列为参考书目。
三是《古文家别集类案》。也是一部专著,收唐、宋、元、明、清五朝古文家一百一十人,始自韩愈,迄于贺铸。分甲、乙、丙、丁四案,每案后附各类文章目录,计三千余篇。书中品评每位古文家的文章风格、得失、源流,博洽精要,“一字不肯苟下”,其风神易于使人联想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如今,这部《古文家别集类案》作为文物,陈列在山西大学文科楼贵宾室里。
郭象升还著有《经史百家拈解》《渊照楼札记》《丹林生寤言》《云舒随笔》等。近代东南大藏书家刘承干因慕郭的大名,曾将其刊刻的《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从沪上邮赠给他。国学大师刘师培与郭象升接触后,称郭象升的学术和文章为“山西一人”。
——不选郭象升,民国初期的山西文学从何说起呢?
20世纪30年代,时任山西文献委员会常务委员的郭象升,领衔编选了一套《山右丛书初编》。大系第五卷中有九位作者的诗文,即全部得自这套丛书。郭象升编这套丛书,重点是历代未被注意、但确有价值的山西学者文人的遗著。根据稿本或抄本编入的就有:明代张道濬《从戎始末》,张慎言《洎水斋文抄》《洎水斋诗抄》;清代毕振姬《西北之文》,祁韵士《万里行程记》《西陲要略》,王轩《顾斋遗集》,耿文光《万卷精华楼藏书记》。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及其长远影响,学者早有论定,毋需赘言。
笔者只想说,《山右丛书初编》的著者和读者是幸运的,它的编者郭象升却没有这样好的运气。历史不能对照。
行文至此,忽发奇想:兴许这时候,允叔先生正把常赞春、马骏、景梅九,还有和他一起“失选”的几位文朋诗友:赵城张瑞玑(有《张瑞玑诗文集》)、沁水贾景德(有《韬园诗集》)、乡宁吴庚(有《空山人遗稿》)等,招集起来,把酒持螯,拈韵赋诗吧。
2007年5月作,载《名作欣赏》2013年第2期
山西省作协《创作研究》2013年第1期
一束现代精神的炬光
——余秋雨《文化苦旅》谈片
一
前年初春,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了余秋雨教授在上海签名售书的盛况:长长的队伍一路延伸,主办者为了照顾后面的读者,规定每人限购一本,苦苦恳求不成,许多读者不惜再去排队。人们渴望得到的这本沪版新书就是《文化苦旅》。
这是一本散文集。所收三十七篇文章都是作者近年来在国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觉得非写一点文章不可”的时候写下的。作者是著名的艺术理论家、中国文化史学者,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水平,由山川风物引发的勃郁诗情,以及酣畅淋漓、仪态万方、给人以壮美的艺术情调,在当今中国文化圈子里,投下一束炬光。这是一束闪射着现代精神的炬光。
二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现代人似乎走入了一个迷阵,疑疑惑惑地像是自问,又像是问别人。现代的诗人们更是把它当作一个主题纠缠着,虽然总也纠缠不清。
莫非我们的祖先也会这样思考?比如说白莲洞人?不。在《白莲洞》中,余秋雨告诉我们:“如果他们也有思想家,摸着海底生物的化石低头沉思,那么,他沉思的主体只是我们,而不是我。”
是的,白莲洞人只能把“我们”作为沉思的主体。他们别无选择。山崩海啸,天塌地陷,靠什么来消除内心的恐怖?我们。狮虎成群,豺狼当道,靠什么来抵御猛兽的袭击?我们。只能是我们,而不是我,这是自然的选择。因此:
白莲洞已经蕴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数万年来,常有层层乌云要把这个字荫掩,因此,这个字也总是显得那么辉煌、挺展,勾发人们焦渴的期待。当非人的暴虐压顶而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突然爆炸,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这个字还会燃起人们永久的热念。但是,这个字倘若总被大写,宽大的羽翼也会投下阴影。(《白莲洞》)
我理解这里所说的阴影是个性的淡化、泯灭和被抹杀。在大一统的格局里,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与人之间只是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汇聚。于是,贾府的老太君见了省亲的孙女的轿子就得下跪,老年闰土遇到童年的伙伴也禁不住嗫嚅着称老爷。于是,一个人口亿万的民族,在奇峰竞秀的三峡,只能演绎出一个个的贞节故事,并且长久地享用着这些残缺的神话,直到现在。在今天,一个充满进取精神、想有所作为的青年,多么希望自己早点成熟起来。然而环境对他说,好吧,请敲掉全部牙齿。这就是大写的人字那个宽大的羽翼投下的阴影。现代中国人背着因袭的重担,走起路来蹒蹒跚跚,要潇洒真是不易。然而,既然现代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正视人,为什么还抱着“阴影”不放,任其扩展?为什么不能“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
时代到了这一天,这群活活泼泼的生灵要把它析解成许多闪光的亮点。有多少生灵就有多少亮点,这个字才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白莲洞》)
余秋雨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据说他给每届新生上的头一堂课就是:活得潇洒些。比之于街市上常可闻见的“潇洒”,二者音形无别,义却迥异。后者是一种模仿出来的矫情,徒有其表;前者则是内心的彻底解放,是个性的完全苏醒。
看来,活得潇洒些,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是余秋雨的一个基本思想。从这里出发,他的笔轻轻一画,触及到了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化。
三
在《柳侯祠》里,作者认为对于被贬放到永州一待十年的柳宗元来说,灾难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创作出《永州八记》等篇什,使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本来他可以心满意足了,不用再顾虑什么仕途枯荣。然而,当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时,他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欢喜,急急赶去,还在汨罗江边吟了几句诗:“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余秋雨对此大为感慨:
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
这诱惑,我们不妨看作是“宽大的羽翼投下的阴影”。大哉如柳宗元尚且经受不住诱惑,何况其他无名的中国人、中国文人呢?
《白发苏州》写到了唐伯虎。京城的文化官员一听说这个名字就皱眉,原因是他放浪不驯,名声很坏,不干什么正事,瞧不起大小官员,写写诗,作作画,竟敢自称是江南第一才子。对于京官的皱眉,余秋雨很不以为然,他似乎也是皱着眉写了下面一段话:
唐伯虎是奸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在这里,作者更把自己的思想放开了。若不是对中国文化充满真诚,哪会有这样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