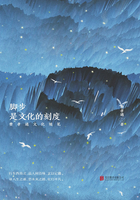他的诗译得好,不仅由于他爱诗,而且由于他写诗。他认为译诗不仅应在内容上忠实于原著,在风格上也应忠实于原著,一言以蔽之,应力求形神皆似。
《书屋》正在筹办之时,突然接到了他的来信:
周实同志:
你好。
非常高兴得知你在筹办《书屋》。
寄上一稿①,原为《中华读书报》所约,但是他们怕得罪人,其实冯亦代②不会介意,我已打过招呼。萧③也未必介意,因为是学术讨论。
但是,《中华读书报》的ULYSSES专版,并未涉及实质性问题。
邵燕祥④说,我替你为这稿找个出路,他介绍我投寄贵刊,最后提到你的大名,我告诉他,我们是老朋友了。
朋友归朋友,办刊归办刊。
是否适用,仍要取决于刊物宗旨和风格。
很高兴又知道了你的消息,祝你在新的事业中,取得辉煌成绩。
祝好。
江枫
1995.5.13
当然,我们是老朋友了。收到此信的十年之前,我就写过他的专访。那时,我还在《湖南日报》,刚刚迈入而立之年,而他则是到长沙来修订他翻译的《狄金森诗选》。我的专访是这样的:
① 周实注:《ULYSSES是不是天书——〈尤利西斯〉译本抽样》。
② 冯亦代(1913-2005),浙江杭州人,散文家,翻译家,曾创办英文版《中国作家》,主编《电影与戏剧》,有《冯亦代文集》五卷行世。
③ 萧即萧乾(1910-1999),蒙古族,世界闻名的记者、作家、翻译家,有《萧乾文集》十卷行世。
④ 邵燕祥(1933-),生于北京,当代诗人,晚年多写随笔、杂文,其主要作品有《邵燕祥文抄》等。
作为一个爱好外国诗歌的青年,好多年前,我就读过江枫翻译的诗了,那是美国女诗人艾·狄金森的。当时的第一印象是,从那些诗里读不出什么翻译腔,就像我国当代诗人用汉语写成的,文字凝练优美,句法跌宕有致。
后来听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译的《雪莱诗选》,想购来一读,遗憾的是,此书畅销,一连再版三次,竟然未能觅到,而只能借阅。
最近,江枫又到长沙来了。这一个“又”字包含了二十八个春秋。二十八年前,他曾在位于长沙黄土岭的解放军第一政治学校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二十八年不短,二十八年变化太大,怪不得他这次到长沙,竟感到有些陌生了。
江枫健谈,但不愿意过多地谈个人经历。从《雪莱诗选》译后记中得知,1949年初参军前,他是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参军后南下,随军从南昌、武汉辗转来到长沙,1956年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一直留在北京,目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提起译诗,他神采飞扬了。在《雪莱诗选》译后记中,我已经知道他译雪莱,是由于他爱雪莱,是为了让他的同胞能够通过汉语去听雪莱那时而高亢激越时而甜美醉人又时而缠绵悱恻的歌声,分享他从雪莱的歌声中所得到的启迪、鼓舞和欢乐。这次我又知道,他1946年读中学时,就办过一个文艺刊物,他为这个刊物翻译发表的第一首外国诗,就是雪莱的《西风颂》。他说:“当然,那是个不够六十分的习作……”他谈雪莱,谈得那么情真意切,就像在谈一个亲人。他译雪莱,就像为心爱的歌手传播美的旋律。他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这项工作的,其间断断续续,用了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翻译也像创作一样需要生活,经历贫乏,无法理解人生,也无法真正认识雪莱,再现雪莱……”他感受颇深。
谈了雪莱,又谈狄金森。江枫这次到长沙,就是为了出版他所翻译的《狄金森诗选》的。诗选已进印刷厂,不久即可问世。“狄金森和惠特曼是美国现代诗歌的先驱。”他激动地点燃一支烟,“惠特曼豪放,狄金森婉约,他们是标志着美国诗歌获得美国气派和现代特征的并列的分水岭。狄金森是描写灵魂风景画的丹青妙手。请听她这样一首诗,”他很有节奏地吟诵起来,“太阳出来了/它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车辆来去匆匆,像报信的使者/昨天已经古老。”狄金森的诗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共有一千七百七十五首,但生前她只发表过七首,绝大部分都是身后发表的,到本世纪初才逐渐为人所知,目前美国诗坛上对她评价极高。有人甚至认为,她是古希腊莎弗以来最杰出的女诗人。江枫的《狄金森诗选》,选译了两百多首,还选译了一部分书信。
江枫的诗译得好,不仅由于他爱诗,而且由于他写诗。多年的写诗实践,加上他在大学外文系打下的英语和外国文学基础,不仅使他译笔流畅、清新、准确,而且所用的语言也是诗的语言。他认为译诗不仅应在内容上忠实于原著,在风格上也应忠实于原著,一言以蔽之,应力求形神皆似。在他的《雪莱诗选》中,我们已经看到《西风颂》的奔放不羁,《致云雀》的优美清新,《阿多尼》的缠绵悱恻,《暴政的假面游行》的刚正严肃,《颂歌》有进行曲般的节奏,《印度小夜曲》有花前月下漫步轻语的细腻热烈……读者正殷切期待着《狄金森诗选》的问世。
这篇专访发表后,他看了对我说,你写得有点拘谨了,似乎还可潇洒些。我说是,说得对,但我同时在心里也为自己辩解道:在省级的党报上,也只能写成这样了,再潇洒就难发了。
他的这篇《ULYSSES是不是天书——〈尤利西斯〉译本抽样》在《书屋》的创刊号发表后,反响自然非常大,很多报刊都有介绍。他又写了一封信——《致〈书屋〉编辑的一封信》,发表在《文汇读书周报》上:
孝纯①同志、周实同志:
祝贺你们,祝贺湖南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书屋》在你们主持下顺利面世并引起良好的热烈反响,我也为我那篇《〈尤利西斯〉抽样》被如实承认为“持论公允”,特别是被萧乾和文洁若夫妇①欣然接受,并未像你们那里个别人所担心的那样而感到高兴。
① 周实注:刘孝纯当时为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兼《书屋》主编,我是常务副主编。
对冯亦代有关《尤利西斯》译本的评论方法,我曾当他面表达过我认为不读原作就无权评论译文的观点,他并不以为忤;《书屋》出版后我又在电话里告诉他,他仍然是高高兴兴地说:“圣人闻过则喜,我也闻过则喜。”
萧乾和文洁若会怎样想,我原来也难揣测,现在看来,担心冒犯他们倒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是“君子之腹”的容量是因人而异的,萧乾和文洁若对此文的反应使我感动。
我应邀来到萧家时《书屋》尚未出版,他们知道的只是《中华读书报》有关《尤利西斯》评论的一篇综合报道中引用了我根据一段原文对两种译本比较之后所说的一句话。文洁若问:“你认为金隄的译本比我们的好?”我说:“就引以为例的那一段来说确实是这样。”然而,那句话只是结论,我细述过我对那一段的理解,文洁若听了表示接受而且说:“这是全书最难译的一段。”她决定在修订本中完全采用我的试译方案。
又一次应邀来到复兴门外他们那套寓所时,我带来了刚收到的《书屋》。萧乾读完第一部分便说,“评论是不抱成见的”;读完全篇时,我正和文洁若一道在她的工作室里讨论她为修订英汉对照本译文所涉及的一些问题,萧乾高兴得像个孩子——他那副面孔一笑就像个弥勒佛,他就是带着一副弥勒佛似的面孔像个孩子一样跑过来说:“你是一个被埋没了的人才!”
文洁若说:“太多的称赞使我们飘飘然起来,真以为我们四年的功夫胜过了人家十几年的努力,你的意见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的译文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那个奖,我们不该得,我们准备放弃。”我问:“什么奖?”她说:“这部书得了外国文学图书一等奖,你不知道?”我告诉他:“知道,不过这奖不归你们,归出版社;你愿意放弃,出版社未必愿意,据不少人说,为了使这本书得奖,出版社很费了一番心思,但是你们两位从善如流的坦荡精神为文坛和翻译界所罕见,使我感动,我也为能有你们这样的同学和朋友而感到自豪。”她承认曾受过认为可以不必紧扣原文而强调“可读”和“灵活”的那种主张的误导。
① 萧乾和文洁若是《尤利西斯》译林版译者,另一版本为人民文学版,译者是金 。
文洁若说:“你得翻译终身成就奖确实并非偶然。”由于她一再重复,以至于使得这个自以为尚有点自知之明的我也简直几乎就要相信果真“并非偶然”了。而文洁若实在是过高估计了她这个老同学,所以竭力邀我和她合译James Joyce的另一部名著,由于极其难译河北教育出版杜正在悬赏征求译者的《为芬尼根守灵》。
为避自我吹嘘之嫌,我要求文洁若在写给杨德豫①的信中如实记录萧乾的反应,她是这样写的:“刚才和江枫通了电话,他说,你曾担心萧乾看了他那篇文章会不高兴,其实不然,他不但高兴,还夸了江枫,说他是个‘被埋没的人才’。其实《尤利西斯》英汉对照本早就交稿了,看了江枫所改译第三章第一段后,我才决定把收入对照本中的五章(1、2、4、13、18)重改一遍。”并且认为“江能在完成《芬》之后译《尤》的第四个译本,那将会是定本”。
由于《文汇报》认为我的抽样比较“分析精详,持论公允,富有说服力”,作家协会书记处分管对外文化交流的书记金坚范曾建议发行30万份的《作家文摘》全文转载,以示提倡外国文学翻译目前缺乏但是非常必要的严肃评论;《文摘》主编石湾见到全文后来电话表示,此文专业性太强,不适合多数文摘读者的趣味(对此我完全理解),全文转载虽不可能,但是准备发一个消息云云。
我知道你们关心并且介意与湖南渊源和感情都颇深厚的萧乾的反应,所以如实报告如上。我认为他那种胸襟和度量:很了不起!专此,
并致敬礼!
江枫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日
① 杨德豫(1928-2013),湖南长沙人,翻译家,译有莎士比亚长诗《贞女劫》和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朗费罗四人的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