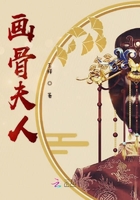林扶苏听到有人在喊门的时候,是龙纪十二年五月初一下午晡时。
当时老祖父给他擦拭完了那些没有敷药或用夹板夹住的身子,用热帕子捂着脸,好促使血液循环,使青一块紫一块的脸恢复。祖父的那混浊的眼泪没干过,一边流着泪,一边低声咒骂华府的那些奴仆:一群活该八辈子都是贱民,下手如此狠,简直不把孩子当人看,******,都是些失去人性的疯狗。
林扶苏感觉浑身无处不疼,但依然忍着,且温言安慰老祖父。说是自己不好,添完油剪灯花的时候突然想起昨日玄敬师傅教的“鹭浴盘涡势”弹琴手法,太过于入神了,没听到那些人入门;又说自己是少年人的身子骨,骨肉正发育成长,伤养养就好了,不要担心。
老祖父却不信这些,非常难过的说:“教观里的小师傅说了,老神官说可能或落些残了。你的身子本来就弱,虽说近几年随守一师傅学了些采形练体的养生法门有所好转,可毕竟先天元炁不足,武道可强身不足以养气啊。唉,若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你娘。哪些天杀的!”咬了咬牙,眼中闪出不甘,低声说道:“陆隆林家的人就这么被人欺负了,老太爷肯定骂我没出息。”
林扶苏皱着眉低着声劝:“爷爷——,这口气从我而来,由我来消,你放心我记得!”
林扶苏正欲进一步劝导祖父时,门外响起了一声:“请问这是林家吗?”声音悦耳,如琴音中的泛音,清澈明亮。扶苏一怔,感觉这似乎不是认识的人声音,忙让祖父去看。
仝桶正在打量这这个家,柴门青瓦屋,贫困而不衰败,柴草利利落落四四方方堆在院子的一角,一匹驮马在草棚下的槽子里吃草,圈粪的上面垫着一层干土,院子里没有牲口的骚臭味。正房的门敞着,门楣和两框有过节残留的已经褪色了的红纸对联,字迹已经模糊,不过不模糊仝桶也不认得——她不识字。在她准备喊第二声的时候,从门内走出一个发须花白、身体高瘦、衣虽旧却洁净的老丈,她不禁心里惴惴起来。难道是这老丈的儿子?若是应当也得三四十了,伺候一个三四十的男人……虽然心里在打鼓,仝桶仍不失礼数的忙走近老者跟前,温声问道:“请问老丈这是林家吗?”
林山看到一个小姑娘进入院子,他有些奇怪,边上下打量边回答道:“正是,姑娘你找谁?”小姑娘十二三岁,颇为瘦弱,穿着青色婢女衣,是个不协调的阴阳脸,左脸被一块大大的红色胎记遮住了容貌,右脸微黄,一双眦部睑缘充血、肿胀且浸渍糜烂的眼。林山昔日跟人走镖见过各种畸人,倒也没有大惊小怪。小姑娘答道:“老丈,我是华府的丫头,奉管事的命,来伺候卧床的某位先生。”林山一听到华府,又听到卧床,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气愤的道:“把人打成这个样子,再来伺候,扮慈悲善人?”
“嗯?!”仝桶一阵疑惑,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她搞不懂什么情况了。
“请你回吧。观里的师傅虽然曾说过华府有人要来,不过我们并不需要。”林山压了压气,在大家族生活过的他明白这事跟眼前这个小姑娘没什么关系,善良的人不会无故牵连怪罪不相关的人。想想华府这些年在宜阳城的蛮横霸道,也不是当下的他们爷孙能够惹的。刚才自己那一刹那没按住火气,不知这丫头回去会不会给自家惹来麻烦,唉,自己这把老骨头死就死了,无所谓,但是小星若有个好歹,自己死也不甘心啊!——凌晨五更就跑去教观帮忙的孙子,过了没几个时辰,竟然胸骨腿骨折断,鼻青脸肿的被人用担架抬了回来,老头恨不得躺在床上的是自己,而不是孙子。
“老丈,不经府里召回,我不能走的,来时执事已经再三说了。”
“啊!这——”
双方一时僵持了。
仿佛为了验证自己说的是实话,仝桶还向院门外看了一眼早已经消失不见的驮马车。
“爷爷,您请那位姑娘进来吧。”正在这时林扶苏孱弱的声音自窗内传来。
一个小孩的声音?仝桶再次犯起了疑惑。
林山领着仝桶进堂屋。迎门一间,约是吃饭的地方,谈不上什么布置,简单的几件家具,桌椅板凳,墙上挂着些竹木器具的生活用品。门屋左右各一间,声音是从右边的,他们走进,一张粗竹床上躺着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头上还梳着未曾散开的道髻,膝盖到颈下用一层薄被单盖着,右腿被数块短木板夹着,左腿上有青紫相间的伤痕。
仝桶侧眼去看他的面时,他也正在看她,眼神不小心对上了一次,仝桶枯黄的右脸上涌现了一丝羞红的血色。而她看到他是一张被打伤犹如烂茄子的脸,紫青之外正常的肤色大约有些黧黑,故而推测面色黧黑,双目却是有神,大大的,黑白分明。林扶苏看到一个长着一块胎记的女孩走过来,他不知怎么地就觉得那块胎记有点意思,好像一只红色的鸟,似乎在仰首愤怒而啼。他越看越觉得像,这图案似乎有一种魔力,引导着他的精神陷入其中。他如下死眼看姑娘的轻薄少年,仝桶虽然习惯了被人惊愕得看或嘲笑,但被这种非惊愕有些发痴的目光看还是第一次,尤其还是个八九岁左右的男孩子,她尴尬的不得了。林山拉拉椅子请仝桶坐的声音传来,才把林扶苏拉回了现实。
林扶苏尴尬一笑,牵引着脸上的伤,在仝桶眼里有些像狰狞的小鬼。大约脸上的伤委实相互牵骨带筋,这小鬼不得不放缓表情,缓声细语的说道:“姑娘,若是的确不能回华府,倒也不妨在这里住下。不过我家甚是简陋,饮食也甚是粗简,勿要嫌弃。”
这时林山说道:“小星,你怎么?唉——”林扶苏道:“爷爷您不必担心,送我回时,老神官爷爷跟我说了些内情。”林山还待说,仝桶已经直接应承了这话:“奴婢谢谢少爷,谢谢老太爷。”她内心一下子放松下来了,原来是个八九岁的男孩,不是男人,尴尬事就会少得多,吃住再粗糙也无所谓。
林扶苏牵了牵嘴角,浮现着一丝笑意道:“你看我们家,还有我,那用的上那称呼,唤我名就行。”仝桶神色放松,却依旧慎言慎行的接口:“老太爷和少爷都是良人,奴婢是贱民,可不敢称少爷的大名。”在东黎国,贱民分为两种,一为官贱民,二是私贱民;私贱民中又分四等,自高而下曰随身、客女、部曲、私奴婢。
林山道:“我们寻常百姓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也就没那么多忌讳,什么样的称呼都无所谓。你大小既然跟小星差不多,就唤我林爷吧。姑娘,还未请教你怎么称呼呢?”“回老,老,林爷,我叫仝、桶、灵犀。”仝桶有些慌里慌张的回答。
林山仿佛耳背之人重复了一遍:“童童灵犀?童童?这姓很稀罕,第一次听到。”仝桶想了想答道:“我姓仝。”然后,用手比划着她唯一会写的这个字,继续道,“叫仝灵犀,先父说是心有灵犀的灵犀。不过,因为在华府水房帮工,大家都叫我仝桶,青芸说是水桶的桶。林爷你们叫我什么都可以的。”说完后,她谦卑的一笑,笑里似乎含着无边的婉转。
林山是个普通人,自然不晓得什么“心有灵犀”四字成语典故,林扶苏躺在那里轻轻默念着名字道:“真好听。”随即又一笑道:“挺搞笑的。”林山肃然的说道:“叫人外号可不好,每个人的名字都应当得到尊重。”林山的话使仝灵犀内心一动,眼睛有些酸感,泛着一丝亮色。林山紧接着转过身子准备外去,边转身边说道:“灵犀姑娘,既然要住下,我们收拾清扫一下耳房,作为你暂时客寓卧榻的地方。”在进屋时灵犀已打量了这间房,故林山刚说完她就微笑的说道:“林爷,我是奉执事的命来伺候小公子的,不能别居一室。此外,这卧室地方颇为宽绰,公子的床在北墙下,桌椅在东墙下,西墙下就是再放一竹床中间仍有几席活动空间。小公子夜间喝水或有事需帮忙,我也方便随时照应,完成家主的吩咐。林爷直接唤我的名字就好了。”
“好。灵犀,哪能真让你做这事,小星晚上我来照应就好。白天若是你方便的话就照看一下。”林山老实而诚恳的说。
“这是我们丫头应当的。此外,林爷您上了年纪,日间还要忙活,要休息好才是。”
“爷爷,我看就按灵犀姐姐说的吧。你凌晨晨就要起来磨豆去渣煮浆点盐卤等,晚间睡不好可不行,再说晚上我也没什么事。”
“那好,就按你们说的。灵犀,我们虽然暂时在一个家里生活,也就不客气了,你自己要随便点。稍后我把耳房的竹床擦洗收拾过来。”
仝灵犀在这不大长的接触时间里,有一种渴望融入这个家庭的感觉。在这个破落的普通人的家里,她的心情有说不出的愉悦和轻松,如沐春风,仿佛十多年前父母还健在的时候在自己家。如今那个依附在华府之外的小家已经不存在了,父母死后那觊觎自家的人串通执事把那三间棚户似旧房收回,分给了觊觎的人家了,为了吃相不至于太难看,把她撵到了一间窄而霉的小房里,对外说是一个小女孩一间房子足以。
林家的孙子受伤的消息很快遍传附近的几道巷子,那些与林山老人相熟的人,及和林扶苏自小一块玩的小伙伴和他们的父母,接二连三提着各家觉得能补身体、有益身体的食物过来问候。林山打发着这些人,有些进房间来,林扶苏便强撑着喊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婶婶等各种称呼。那些人无不充满了诚挚的怜惜,不少妇人还落下了泪,都宛如对自家孩子。他们的神色里都有一种愤恨,但基于全灵犀在都不敢说什么,不过神色已经表达了心中所想。
仝灵犀在想,这些人在华府的主子眼里是上不得台面的,是次圣方洛川的天礼亦不下于他们的人,却是最有真实色彩的人。在接待这些人的时候,灵犀有时候会不着痕迹的避开一会,让他们方便畅所欲言的聊聊。无目的日子,有时每一天看来都如失眠的慢慢长夜,有时候如春风马蹄迅速的奔来奔走,这几个月对灵犀来说当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