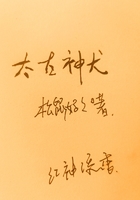最后,我爸气喘吁吁,像是应付了事似得,扔下铁锹不挖了,带着我把那染了尸水的土倒掉,又在外面地里挖了一些新的土壤把坑填上。地面上虽然能看到新土的痕迹,却再看不到人形了。
这一切完毕之后,天已经墨黑,我累的呼哧带喘,以为这一切终于结束了,回去好好睡一觉,过几天我就要上小学了,还挺期待的。
那天夜里我妹依旧被我妈赶出来跟我一起睡,我累的吃了一口饭便倒在炕上,眼皮发沉,我妹捧着一块西瓜在啃,一边啃一边和我说邻居家的二丫儿和她吵吵起来了,因为二丫说她光腚磕碜!
我妹义愤填膺的吐了一口西瓜籽,对我说:“哥,她腚才磕碜呢,比谁都磕碜,以后你别理她,别跟她玩,我膈应她!”
我想告诉我妹,她的腚不磕碜,是光腚磕碜,想一想,我说了也白说,万一她觉着我向着二丫儿说话了,再嚎丧起来,我说不定要挨揍。
我困的要命,我妹还不依不饶的和我说林二丫各种不好,我哼哼哈哈的应着,依稀听到隔壁我妈那屋在小声唏嘘什么,而且,还有一些女人呻吟的声音,我确定不是我妈发出来的。但我太累,沉沉的就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我体会一次水灾,由于我妹林小桃昨晚吃了太多西瓜,早上一泼尿把我冲醒了,那时候天还没全亮,我看着湿答答的褥子,直觉脑子疼!
可林小桃还躺在被窝子里呼呼大睡,似乎是对她尿炕的事一点都不知情,我拍她的脸,半响她才醒,醒了发现褥子湿答答的,直接哭了,其实林小桃心里还是有羞耻这份感知的,她告诉我,她做梦一直在找茅坑,好不容易找着了。。
我表示我理解她,只要她不哭就行,我和林小桃扛着被褥晾到栅栏上,之后我心血来潮,苦口婆心的给她讲,你不穿裤子虽然是露腚,但丢的是脸。
林小桃扑闪着无知的大眼睛,貌似是略略听懂,人得穿裤子这一说。
不大一会,我妈从屋里走出来,拎起院里的锄头出了门,临走的时候瞄了一眼栅栏上晾着的褥子,也没多说啥,直接走了。
村里人早上都起来的特别早,天再亮一些,公鸡开始打鸣。我奶奶爬起来开始做饭,最近几天我姑姑特别安静,一直独自待在屋里,没出过门。
可这天早上,我姑打了一大盆凉水,坐在屋里擦身子,我姑洗澡洗的勤快,盆里的水一直都是清冽的。
一家人忙活了一个早上,吃了早饭,我妈和我爸又下地干活儿去了,我去找小哥们儿林小牛,他正和林双鸭子在村口唠嗑,林双鸭子是隔壁二丫儿的哥哥,他俩见我来了,林小牛告诉我他老婶的坟又被填上了,还告诉我他看到他老婶的尸体了。
说是满身绿,其实就是现在说的尸斑,而且他老婶肚子很大,像一口大鼓似的。他说这话的时候,直接满脸的自豪,无形之中像是再说:“看哥们儿多列害,这都看过!”
我撇撇嘴,显摆道:“你那算啥?我昨天可是跟一帮人去定军山埋尸体了,那尸体冒水,可臭了,拉拉一道呢。”
林小牛听完,吓得够呛:“我也听我爸他们说了,说可臭了。说搞不好还要诈尸呢。”
“那还不算啥,我爸昨晚挖开祠堂的地面,那臭水渗的可深了。”
林双鸭听完我说的话,显然是不信,撇嘴道:“老子才不信呢。”
我拍着胸口道:“撒谎的是孙子。”
林双鸭这才有些相信,而且林小牛也满眼的好奇,捅咕我腰一把:“大哥,这么邪乎的事儿,咱们去祠堂看看呗?”
起先我还觉着害怕,但经过他俩的怂恿,我跟着他俩去了祠堂,本来打算把那个新挖的大坑指给他俩看看就回来。
可刚进祠堂里,登时被吓了一跳,我爸新填上的大坑上面,很明显能看到新土的痕迹,新土上明显印着一道人形的湿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