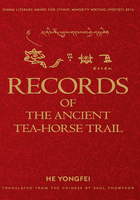释迦牟尼当年在菩提下证道后,本想即刻入灭,进入涅槃境界,但是他怜惜众生在生死苦海中沉沦不已,于是留下来普度众生。佛非枯淡,而是热切;佛非冰冷,而是慈悲;佛非无为,而是以爱度众生。如果信念向佛,那么你会多情于你的亲人朋友,多情于你的同族同类,多情于一切众生,多情于这个有情的世界。
想入非非——朱湘
贾宝玉在出家一年以后
去寻求藐姑射山的仙人
自从宝玉出了家以来,到如今已是一个整年了。从前的脂粉队,如今的袈裟服;从前的立社吟诗,如今的奉佛诵经……这些相差有多远,那是不用说了,却也是他所自愿,不必去提。
只有一桩,是他所不曾预料得到的。那便是,他的这座禅林之内,并不只是他自己这一个僧徒。他们恐怕是只有很少的几个人,像他这般,是由一个饱尝了世上的声色利欲的富家公子而勘破了凡间来皈依于我佛的。从前,他在史籍上所知道的一些高僧,例如达摩的神异,支遁的文采,玄奘的淹博,他们都只是旷世而一见的,并不能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遇到。他所受戒的这座禅林,跋涉了许久,始行寻到的,自然是他所认为最好的了。在这里,有一个道貌清癯,熟谙释典的住持;便是在听到过他的一番说法以后,宝玉才肯决定了:在这里住下,度为僧的。这里又有静谧的禅房可以习道,又有与人间隔绝的胜景可以登临。不过,喜怒哀乐,亲疏同异,那是谁也免不了的,即使是僧人。像他这么整天的只是在忙着自己的经课,在僧众之间是寡于言笑的,自然是要常常的遭受闲言冷语了。
黛玉之死,使得他勘破了世情的,到如今,这一个整年以后,在他的心上,已经不像当初那么一想到便是痛如刀割了。甚至于,在有些时候——自然很少——他还曾经纳罕过,妙玉是怎么一个结果:她被强盗劫去了以后,到底是自尽了呢,还是被他们拦挡住了不曾自尽;还是,在一年半载,十年五载之后,她已经过惯了她的生活,当然不能说是欢喜,至少是,那一种有洁癖的人在沾触到不洁之物那时候所立刻发生的肉体之退缩已经没有了。
虽然如此,黛玉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之前,仍旧是存留着。或许不像当时那样显明,不过依然是清晰的。并且,她的形象每一次涌现于他的心坎底层的时候,在他的心头所泛起的温柔便增加了一分。
这一种柔和而甜蜜的感觉,一方面增加了他的留恋,一方面,在静夜,檐铃的声响传送到了他的耳边的时候,又使得他想起来了烦恼。因为,黛玉是怎么死去的?她岂不便是死于五情么?这使得她死去了的五情,它们居然还是存在于他,宝玉的胸中,并且,不仅是没有使得他死去,居然还给予了他一种生趣!
在头半年以内,无日无夜的,他都是在想着,悲悼着黛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半年快要完了的时候,黛玉以外的各人,当然都是女子了,不知不觉的,渐渐的侵犯到他的心上,来占取他的回忆与专一。以至于到了下半年以内,她们已经平分得他的思想之一半了。这个使得他感觉到十分的不安,甚至于自鄙。他在这种时候,总是想起了古人的三年庐墓之说……像他与黛玉的这种感情,比起父母与子女的感情来,或者不能说是要来得更为浓厚一些,至少是,一般的浓厚了;不过,简直谈不上三年极哀,也谈不上后世所改制的一年的,他如今是半年以后,已经减退了他的对于黛玉之死的哀痛了。他也曾经想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要使得他的心内,在这一年里面,只有一个林妹妹,没有旁人,但是,他这颗像柳絮一般的心,漂浮在“悼亡”之水上的,并不能够禁阻住它自己,在其他的水流汇注入这片主流的时候,不去随了它们所激荡起的波折而回旋。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尽期。
这两句诗,他想,不是诗人的夸大之辞,便是他自己没有力量可以作得到。
在这种时候,他把自己来与黛玉一比较,实在是惭愧,她是那么的专一!
也有心魔,在他的耳边,低声的说:宝钗呢?晴雯呢?她们岂不也是专一的么?何似她独独厚于彼而薄于此?并且,要是没有她们,以及其他的许多女子在一起,黛玉能够爱他到那种为了他而情死的田地么?
他不能否认,宝钗等人在如今是处于一种如何困难,伤痛的境地,但是,同时,黛玉已经为他死去了的这桩事实,他也不能否认。他告诉心魔,教它不要忽略去了这一层。
话虽如此,心魔的一番诱惑之词已经是渐渐地在他的头颅里着下根苗来了。他仍然是在想念着黛玉,同时,其他的女子也在他的想念上逐渐的恢复了她们所原有的位置。并且,对于她们,他如今又新生有一种怜悯的念头。这怜悯之念,在一方面说来,自然是她们分所应得的;不过,在另一方面说来,它便是对于黛玉的一种侵夺。这种侵夺他是无法阻止的,所以,他颇是自鄙。
佛经的讽诵并不能羁勒住他的这许多思念。如其说,贪嗔爱欲便是心猿意马,并不限定要做了贪嗔爱欲的事情才是的,那么,他这个僧人是久已破了戒的了。
他细数他的这二十几年的一生,以及这一生之内所遭遇到的人,贾母的溺爱不明,贾政的优柔寡断,凤姐的辣,贾琏的淫,等等,以及在这些人里面那个与他是运命纠缠了在一起的人,黛玉——这里面,试问有谁,是逃得过五情这一关的?人世间的悲欢离合,无一不是五情这妖物在里面作怪!
由我佛处,他既然是不能够寻求得他所要寻求到的解脱,半路上再还俗,既然又是他所吞咽不下去的一种屈辱,于是,自然而然的,他的念头又向了另一个方向去希望着了。
庄子的《南华真经》里所说的那个藐姑射山的仙人,大旱金石流而不焦,大浸稽天而不溺,那许是庄周的又一种“齐谐”之语,不过,这里所说的“大旱”与“大浸”,要是把它们来解释作五情的两个极端,那倒是可以说得通的。天下之大,何奇不有?虽然不见得一定能找到一个真是绰约若处子的藐姑射仙人,或许,一个真是槁木死灰的人,五情完全没有了,他居然能以寻找得到,那倒也不能说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体。
他在这时候这么的自忖着。
本来,一个寻常的人是绝不会为着钟爱之女子死去而抛弃了妻室去出家的。贾宝玉既然是在这种情况之内居然出了家,并且,他是由一个唯我独尊的“富贵闲人”一变而为一个荒山古刹里的僧侣的,那么,他这样的异想天开要去寻求一个藐姑射仙人,倒也不足为奇了。
由离开了家里,一直到为僧于这座禅林,其间他也曾跋涉了一些时日。行旅的苦楚,在这一年以后回想起来,已经是褪除了实际的粗糙而渲染有一种引诱的色彩了。静极思动,乃是人之常情。于是,宝玉着僧服,肩着一根杖,一个黄包袱,又上路去了。
慧心禅语:
提起红楼梦,想必没有人不知道,“富贵闲人”贾宝玉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使人无法忘怀。关于红楼梦文本的解读,除了最具权威的脂砚斋,更是异彩纷呈。在大家的眼中,宝玉怜香惜玉是众人公认的,并且文中多次有描写宝玉参禅礼佛的细节,直至最后出家为僧。
此文大胆设想,从人的本性出发,想象宝玉之所以出家是因为精神伴侣黛玉香消玉殒,而他的乖张秉性使其依然对美好纯真的感情存有希冀,因而有寻访“藐姑射仙人”一说。此结果不论如何,都能证明一个事实,世界的本质是爱。因为爱,我们才会容纳于社会中,与人进行各种社交,创造各种文明。因为有爱,一切的人都是具有佛心的。
七宝池上的乡思——许地山
弥陀说:“极乐世界的池上,
何来凄切的泣声?
迦陵频迦,你下去看看
是谁这样猖狂。”
于是迦陵频迦鼓着翅膀,
飞到池边一棵宝树上,
还歇在那里,引颈下望:
“咦,佛子,你岂忘了这里是天堂?
你岂不爱这里的宝林成行?
树上的花花相对,
叶叶相当?
你岂不闻这里有等等妙音充耳?
岂不见这里有等等庄严宝相?
住这样具足的乐土,
为何尽自悲伤?”
坐在宝莲上的少妇还自啜泣,合掌回答说:
“大士,这里是你的家乡,
在你,当然不觉得有何等苦况。
我的故乡是在人间,
怎能教我不哭着想?
“我要来的时候,
我全身都冷却了;
但我的夫君,还用他温暖的手将我搂抱;
用他融溶的泪滴在我的额头。
“我要来的时候,
我全身都挺直了;
但我的夫君,还把我的四肢来回曲挠。
“我要来的时候,
我全身的颜色,已变得直如死灰;
但我的夫君,还用指头压我的两颊,
看看从前的粉红色能否复回。
“现在我整天坐在这里,
不时听见他的悲啼。
唉,我额上的泪痕,
我臂上的暖气,
我脸上的颜色,
我全身的关节,
都因为我夫君的声音,
烧起来,溶起来了!
我指望来这里享受快乐,
现在反憔悴了!
“呀,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
我要回去止住他的悲啼。
我巴不得现在就回去止住他的悲啼。”
迦陵频迦说:
“你且等一等,
我为你吹起天笙,
把你心中愁闷的垒块平一平;
且化你耳边的悲啼为欢声。
你且静一静,
我为你吹这天笙。”
“你的声不能变为爱的喷泉,
不能灭我身上一切爱痕的烈焰;
也不能变为爱的深渊,
使他将一切情愫投入里头,
不再将人惦念。
我还得回去和他相见,
去解他的眷恋。”
“呵,你这样有情,
谁还能对你劝说,
向你拦禁?
回去吧,须记得这就是轮回因。”
弥陀说:“善哉,迦陵!
你乃能为她说这大因缘!
纵然碎世界为微尘,
这微尘中也住着无量有情。
所以世界不尽,有情不尽;
有情不尽,轮回不尽;
轮回不尽,济度不尽;
济度不尽,乐土乃能显现不尽。”
话说完,莲瓣渐把少妇裹起来,再合成一朵菡低垂着。微风一吹,他荏弱得支持不住,便堕入池里。
迦陵频迦好像记不得这事,在那花花相对、叶叶相当底林中,向着别的有情歌唱去了。
慧心禅语:
正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佛教看来,一切众生都“有情”,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会有喜怒哀乐、亲情、友情、爱情。学佛,是由众生来学,是由凡夫开始。佛教徒并不需要排斥感情生活,但要以理性来指导感性,以感性来融合理性,以智慧来指导情感。如果佛教只提倡“不动心”“离欲”,那一般人无法进入佛门。如果佛的教化中没有“情”的成分,也很难教化众生。
所以,我们学佛人应该有这样的理念: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先生活再生死,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融入社会。这也是佛教的“慈悲”。何谓慈悲?“慈能予乐”,想办法使别人快乐,并且以别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悲能拔苦”,时刻都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别人的痛苦。其实,佛法的“慈悲”,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爱心”,爱及一切有情的心。
香愿——许地山
妻子说:“良人,你不是爱闻香么?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现在已经寄到了。”她说着,便抽出妆台的抽屉,取了一条沉香线,燃着,再插在小宣炉中。
我说:“在香烟缭绕之中,得有清谈。给我说一个生番故事罢,不然,就给我谈佛。”
妻子说:“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说,我也不会说。”
“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的罢,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你且说,什么是佛法罢。”
“佛法么? ——色,——声,——味,——香,——触,——造作,——思惟,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的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 这是什么因明?”
“不明白么? 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的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
南普陀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不过绿苔多长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天晴的信。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
“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咧。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完全,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到,我教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在这树荫底下坐着,真舒服呀! 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么好呢!”
妻说:“你哪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作荫,不应当受荫。”
“你愿我作这样的荫么?”
“这样底荫算什么!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的功用,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慧心禅语:
许地山的母亲和舅父笃信佛教,所以许地山与佛教也结下深厚的不解之缘。他以毕生精力从事佛学和宗教比较学的研究,因此其文学创作中也不自禁地折射出某种宗教思想。
“你应当作荫,不应当受荫。”道出了香愿的本质内核,也道出了作者的心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怀有一颗作荫的心,那么世间将不再有喧闹。
结缘豆——周作人
范寅《越谚》卷中风俗门云:
“结缘,各寺庙佛生日散钱与丐,送饼与人,名此。”敦崇《燕京岁时记》有“舍缘豆”一条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