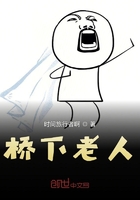西部商报赵梅
母亲的女儿、婴儿的母亲、丈夫的妻子、逃难的灾民、职业记者,这是我的身份。
地震后第一天起,28岁的我带着这五重身份,穿行于“5·12”汶川大地震后的四川废墟上。
25天,我在哭泣的城市和乡村,面对失去母亲的孩子、失去女儿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感同身受,在余震不断的灾区心灵经受更剧烈的强震。
我用苍白的凝聚着汗水和泪水的文字记录25天的灾区经历。
同时将“记者”二字写在了废墟之上,谨以此来表达一位80后职业记者的社会责任感,来祭奠亡灵,激励生者!
“妈妈对不起”
女儿——我是妈妈的女儿,妈妈的希望,但是,地震后第一天,我第一时间站在了重灾区都江堰的废墟上,在接到妈妈担心不已的电话后,我在心里轻轻地说:“妈妈,对不起。”
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在距离震中汶川仅92公里的成都三槐树街6号小区门口。在地动山摇的陌生城市,站在如水般起伏的马路上,看着面目狰狞的高楼扭曲,在不断的强余震中,和奔跑、尖叫的成都市民一样惊魂未定。
地震发生后的第一天,我第一时间站在了都江堰的废墟上。
这座曾经山清水秀的城市已经千疮百孔,找不到一座完好的楼房,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搭建起了简易遮雨棚,帐篷里极度悲伤的老人、孩子,社区里惊恐不安的市民,拖着行李在冷雨中无目的地行走着的人们,我的心揪结起来。
“女儿啊,你才21岁,你是救死扶伤的,怎么会就出不来了呢?”这位焦急等待在都江堰中医院门口的中年妇女,因为长期的哭泣双眼红肿,头发凌乱,整个人都是一副很疲惫的样子。
她不停地搓着双手来缓解自己的焦急情绪。她告诉我,她的女儿是都江堰市中医院妇产科的护士,今年21岁,从护校毕业后就在医院工作,已经3年时间了。
“这可让我怎么过啊?”嘶哑的哭腔透着万般的无奈。
她的家在崇义农村,只有这一个独生女儿。“你不知道我们农村的生活有多困难,女儿就是我们的全部希望啊!”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后她继续告诉我,她已经40多岁了,这个独生女儿是她唯一的希望,她省吃俭用,到处借钱供女儿读书,工作后,稍稍松了口气,可以好好地享受生活了。但是没想到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下子就把她打蒙了,她不知所措。
她和女儿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五一,女儿回家看她,说等闲一些就带她到市里玩。她和老公分别守护在医院的两个出口,希望有奇迹发生。
“护士是救死扶伤的,不会就这样轻易走了。”她无力哭泣的脸上带着希望的表情。
面对这位已无力哭泣的母亲,我只能像安慰自己的母亲一样轻拍她的背,一语未出,泪千行。
我不知道,这座地动山摇的城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接到妈妈电话的时候我竭力平静地说:“妈妈,我还好......”而在心里默默地对那些失去儿女的母亲和儿女们在灾区抢险、工作的母亲们说声:“妈妈,对不起。”
“孩子我爱你”
母亲——我是一位不满周岁孩子的年轻母亲,在家乡也发生地震的时候,在灾区废墟中穿行的空隙,心理几近崩溃的我只能给他写封他看不懂也听不懂的信。
在灾区,我最不愿意看到听到的,就是那些受伤的孩子和悲痛欲绝的父母。我不愿意去触及他们的伤处。因为我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在地震发生的前6天,我不满周岁的儿子还扑闪着无邪地眼睛在我怀里吃奶。怀胎十月到他出生我几乎和他形影不离,和其他母亲一样,他成了我的全部,在他露出笑容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了全世界,在他因为不适哭泣的时候我跟着他哭。我想把所有好的一切都给他,不管自己受多少苦,多少累。
但是,在坍塌的学校教学楼里,一具具孩子的尸体被抬了出来。在医院里,那些受伤的孩子无邪地笑……我忍受着疼痛去面对他们。
在华西附一,我见到了小玉烨,那个曾经很优秀的乖女孩,她失去了父亲,失去了自己的小臂,她的心灵受到了重创。旁边的志愿者告诉我,玉烨的烦躁让他不知所措。而她的母亲,在忍受丧夫之痛的同时面对疼痛和焦躁不安的女儿,面对女儿“爸爸为什么不来看我,爸爸为什么不来看我?”的问话,不知如何作答,她已经红肿的眼睛里已经流不出一滴泪了,她无助地看着我,那个眼神,我永远无法忘记,我不知道该向前走还是向后退,只要我向前一步,小玉烨就会大声喊叫,但是我的离开会让她的母亲更无助。最后,我还是选择了暂时离开。我能做的就是求助心理学家,将重建心灵家园的话题展开。
当我看到不满周岁的儿子的照片,听到电话中儿子的声音和他四处找我的消息后,我强忍泪水。又一次发生的余震让我不知所措,这么多天来,我都不敢去想他,我怕自己的情绪一旦决堤,无法控制……
“爱人原谅我”
妻子——我是一位深爱我的丈夫的妻子,当山崩地裂之时,我只能通过电波告诉他保重自己,听他轻轻地叹息。
“我就走了1个小时,怎么就再也见不到你了呢?”
在都江堰中医医院门口左侧,一位七旬老妇人手里打着一个“我找张国昌”的纸牌子,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一名医护人员来到她身边告诉她,刚才救出来的人叫韩国昌,是不是她的家人时,她原本虚弱的脸上立刻来了精神,不停地询问,试图抬起已经麻木的双腿去辨认。但是,护士询问了她亲属的年龄后给了她否定答案,刚救出的人只有40多岁,不是她要找的人。老人不放弃丁点希望,她说她想说服自己和护士,确定被救出来的人就是她的老伴。
此刻,她也只能这样欺骗自己了。说着,布满皱纹的脸上留下两串清泪,她哽咽着告诉记者,她已经在此守候了近三天两夜的时间了,一次次地失望又一次次地抱有希望。
她告诉记者,她是柳街镇人。纸牌子上写的人是她的老伴,今年81岁,因为心脏病比较严重从柳街镇医院转入中医院的,才三四天时间。老伴说家里要做的事情比较多,让她回家,等需要的时候再找她。
她放心不下,还打电话让自己的儿子过来陪伴,但不想刚回家1小时后就发生了地震。等平静一些后得知中医院住院部坍塌的消息,她立即赶车上来,不想在这一片废墟中始终没有了她老伴的身影。她说她会继续守下去,直到见到老伴为止。
她不停地哀求记者,一定要帮她发布信息,帮助她找到老伴。没有了老伴,她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继续活下去。她干裂的嘴唇里含糊不清地嘟囔着。
在医院看护学生的是映秀小学5年级1班教数学的李老师。
她的亲弟弟已经遇难,快8岁的侄女失去了左小臂,而她的丈夫,直到今天仍没有音信。她在成都已近8旬的公婆,她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告诉他们丈夫的去向。她的儿子今年高考。自始至终,我没有在她的脸上看到无助,那种隐隐言语中透出的坚强让我甚感欣慰,有时感觉她在平静地讲述别人的故事。
就在采访结束,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李老师追了上来,问我:“你说,我能回去看一眼吗?就看一眼也行?”我知道她放不下她的丈夫,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感到在她的个性里有太多与我相似的地方,她是老师、是母亲、是儿媳,她必须坚强,但是作为妻子,她的内心有多脆弱,只有我感同身受。
我想冲动地告诉她,“可以,你去吧,哪怕见一面。”但我还是拼命地让自己冷静下来,坚定地告诉她,不能回去,相信她的丈夫会没事,千万不要离开,因为余震不断,我们不能冲动,还有这么多的人需要她,我俩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她重重地点了点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但是他们剩下的路要一个人走。
当走出住院部大门的时候,我仍沉浸在悲伤的氛围中,不能自拔,默默地替那些先走一步的丈夫们对自己的妻子说声:“爱人,原谅我!”。
“同胞不要怕”
灾民——在灾区风餐露宿25天的生活,使我体重剧减10斤,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我可以笑着拍拍灾区同胞的肩说:
“地震走了,别害怕!”
一次次发生的强余震,和我每天的工作内容让我的承受能力再次接受考验,我几近崩溃。5月19日晚上10点40分左右,成都电视台反复播放19日—20日有强余震的信息,提醒市民做好防备。那些失去母亲的孩子的画面在我眼前一闪而过,采访对象描述的场景在眼前频现,最终,我还是决定和大家一起去避难。
我们拿着自己仅有的必需品找到一个宽阔的露天停车场,里头除了停了十几辆车之外,到处都是碎石,散落的木板,而且已经有几十户成都市民安营扎寨了。我们选择了一个石子堆,因为石子隔潮。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找到了一块长约两米宽一米的木板,垫平地面后铺上板子,再铺上报纸,我们7个人错落地躺在上面。“还是很舒服的啊!”我们这样安慰自己。天为被、地为床,抬头还能看见一轮明月,我们开始认真地赏月。
朋友发来短信说,据新华社报道,今晚最强余震可能是7级,一定要注意。
为了能安全渡过这个难挨的夜晚,做好了能做的一切不喂蚊子的工作,吃下了一片安眠药,盖上同事的床单,眼前的明月开始模糊。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凌晨5点了,发现周围的灾民们已经走了不少,我的同事们都起来了,他们说我睡得真香。至于昨晚震没震大家争论不休,没有结论。
采访、避难,从12号起,我的生活里就是这些内容,风餐露宿成了插曲,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和骨瘦如柴的身体已经让我成了名副其实的灾民。我拍着老乡的肩膀告诉他们,灾难远去,不要怕。
“新闻我无悔”
记者——我是一名怀揣新闻理想的记者,在哭泣的地震灾区,我做出决定,一定要和灾区人民在一起。
我奔波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寻找着感动,和震撼人心的东西。用不同的文字堆积起悲惨、同情、敬仰、失望、希望等等各种不同的味道。
当我来到都江堰新建小学、都江堰中医院时,凄惨的哭声撕心裂肺、此起彼伏,不同的人都在告诉我同一个事实,这些坍塌的高楼的废墟下面埋着他们可爱的孩子,至亲的亲人。同时我也了解到,已经有上百具孩子的尸体被抬出来放在门口,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我喝下了两包板蓝根,戴上口罩、手套,全副武装后来到都江堰中医院救援现场,进门之前再次接受消毒处理,站在这个埋有很多鲜活生命和逝去生命的废墟上,混杂着浓重消毒水味和尸体腐臭味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当搜救犬发出有生命迹象叫声的时候,我迅速地穿过废墟,冲动地想用自己的双手刨开废墟,我多么希望听到幸存者的声音,我希望多一个家属的脸上露出笑容。
已无力流泪的亲人,精疲力竭的医护人员,连续奋战的救援官兵,眼眶里充满着泪水,浑身流淌着汗水的志愿者,我只能将这些可爱的人们收入我的文字中,悲悯、同情等等多种情绪,错综复杂。
我在废墟中穿行,看到了断裂的双脚,淋漓的鲜血,我静静地守候,我用双眼和心灵期盼奇迹出现,看着一具具尸体从眼前抬走,眼看着一个个家庭的希望刹那间消逝,眼看着守候的亲人经历从希望到失望的过程。面对那些一时间阴阳两隔、痛失亲人的人们,我抬起头,告诉他们不哭,我们还有希望。
写稿时,我再次忍住了即将留下的泪水,当那些救援的画面呈现在眼前时,我告诉自己不哭。因为我是一名职业的新闻人,我必须在这里。而那时,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晚上,当采访结束的时候,又有一次强余震发生,街上的行人开始奔跑,地面再次开始晃动,马路右边倒塌了一半的高楼摇摇欲坠,我听到了惊慌的哭喊声,一位好心的大妈用浓重的川味说:“快离开这里,家人多担心。”忍了很久的泪如雨倾盆,我的心一次次地被悲痛、同情等等各种交织的复杂情绪撞击着。
我知道沉寂于悲恸,不是我该有的态度。我只能用吃抗焦虑的药品这种方式强迫自己镇定,来缓解自己心理上受到的伤害。
斗争、斗争,将伤心欲绝的情绪化成理性思考,我必须说服自己忍住悲伤,记录现场。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职责就是保证自己到抢险第一线,将我的见闻依托于笔端告诉所有有爱心的人们,告诉外界,这里发生了什么?告诉人们,生命是多么的脆弱,我们应该怎样认真地活着,这是我作为一名职业新闻人的天职。在这座哭泣的城市里,我做出决定,我一定要和灾区人民在一起。因为灾区的人们需要我,我是一名职业记者,我必须告诉他们,我们需要坚强地生活、悄悄地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