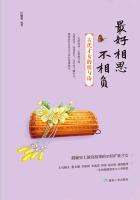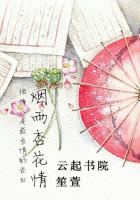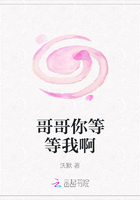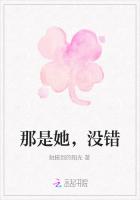个子生活的改变,来自于一个女人。那是邻居的一个寡嫂,因孩子多,怪可怜的,个子就把活儿轻而工分多的活儿派给她,寡嫂为了感激个子就把身子给了他。尝到了另一种生活滋味的个子便放开了手脚,他利用当队长派活儿加工分的权力,先后与多个妇女发生关系,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几乎是想搞谁就搞谁。他感到没有人敢反抗,也没有人说出来或报告上级,就盯上了队里的妇女,管你是妹子,还是姑辈、侄辈的,一到成年,几乎都不放过。有家族大的,个子明着不敢,就暗地里施些小恩小惠,多分几斤菜或几条鱼,多送几尺布票或一斤糖,便把女孩子甚至孩子她妈都打发了。也有不从的,个子就利用队长派活儿的权力,把那些最重最脏最难干甚至是危险性的活儿派给你,干不好不但扣你的工分,开会时还点名批评或羞辱你。那个把日本尿素袋漂洗后能当最时髦的衣服穿的年代,活命是多么重要,不少女人也就认了。有被家里或男人们发现的,但个子块头大而壮实,单挑不过,想父子爷们联手时,个子弟兄和堂兄弟又多。更重要的是迫于个子有上报抓人的权力,弄不好给你定个罪,还会被捆绑到公社里关几天黑屋。权力的魔杖就这样伴着罪恶诱惑着个子的疯狂,也蕴藏着他的毁灭和一个家庭的悲剧。
六
不是那个年代的缺食少药,不是那个乡下姑娘的羞怯和无知,个子也许不会犯事,更不会伏法。一个乡下女子的贞操和名声,犹如一把无形的利剑悬挂在头顶,比什么都重要。要么在道德的幌子下低头活着,要么在名声的光环中被恶棍或无赖欺辱着。人性中的恶就在这样的土壤中滋长着,他们用一点权力或利益的诱惑轻而易举地占领着乡村最神圣的领地,污染着人性中最原始的纯洁和善良,占领一个人或打垮一个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般。这正像田野或河边的一株野花,一朵刚刚凋谢,新的一朵又开始绽放,而使罪恶被放大而又继续着。无知无畏的个子,敢于在众目睽睽下结束一条鲜活的生命,而这生命,连一声哭叫都没有。而一个队长的一声“都散了,干活儿去”或“这事谁也不准说出去”便是律令。一条生命逝去和一个女子受辱被发现的两个多月里,村庄竟平静如水,要不是那个读书的愣头小子在外边报告上去,这乡村一件件屈辱的故事还将发生。乡村,不会因一个没有名分的生命而震颤,更不会因一个村姑的受辱而大惊。像一场暴雨或一场洪水,过去了就过去了,带来的创伤很快就会被深厚的土地掩藏并埋掉。
那个时代的乡村,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啊!
乡村人物之四:呱嗒三伯
一
乡村,好像是我生命的母系和原生态,它天真而烂漫,恣肆而蓬勃,永远有无穷的魅力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诱引着我,并用草根的自然神韵和鲜活赋予着我的幻想并滋养着我的性情。
我现在还有些童心和力量,就得助于童年时候的一些人和一些事,他们像暗夜中一股柔弱的微光,一直点燃在我的生命和记忆中。呱嗒三伯就是其中的人物之一。
“呱嗒”是村里人给他起的外号,按辈分排,我应叫他三伯。他不但能呱嗒,而且能日冒,用本山小品中范伟的话说就是会忽悠。娶媳的、嫁女的、当兵的、看病的、论理和事的,他都能忽悠着解决,这就注定了他是六七十年代中乡村的风头人物和民间名人。到70年代末的顶峰期,甚至大队干部和公社的头头脑脑不能办的事,呱嗒三伯也一样能办妥。
“呱嗒”,已不再是原先带有贬义的绰号,而是成了大家的一种希望或救助符号,谁要是能攀上呱嗒或找呱嗒办事,那是天大的荣耀和面子。全大队甚至连那一带的乡村都以呱嗒三伯为荣,说事或评理时总爱用:乔湾呱嗒说的,以确认自己的正确或权威。
呱嗒三伯家和我家是房子搭山的邻居,但按祖辈的血缘,到我父亲辈,已出五服,但仍算是比较近的家族。1975年唐河流域的一场大洪水,把我们两家的房屋冲毁倒在了一起,灾后拣砖拣瓦时发生矛盾而结下怨恨,从我记事起,两家都不来往。但两家的树木是不管这些的,一有阳光和空间都疯长着,他家的枣树枝伸进了我家院子,我家的洋槐花也能落到他家。儿时贪吃而又不懂大人们的恩怨,枣还没熟时,伸向我家的枣枝上已净光,呱嗒三伯好像也不在意。孩提时代的心目中,他还是蛮和蔼的。
听我父亲讲,解放前呱嗒三伯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非常贫穷。他们兄弟五人,全是光棍,他们的父亲死得早,就由他们的母亲我叫大奶的领着他们给人家当长工、打短工,直到解放后分地分房,他们一家子的生活才稳定下来。老四旧社会给郭滩镇的一个商铺当伙计,合作社时就成了一名吃商品粮的工人;老五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沈阳解放时按投诚人员留在了部队,后成为全军有名的模范和针灸专家而蜚声海内外,呱嗒三伯也就是沾了五弟军官的光而名噪一时。
二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全国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造神时代,呱嗒的五弟当时已是营职的军队劳模,学雷锋标兵。敲锣打鼓的县、公社干部把大红花和慰问品送到了呱嗒家。有日用品、图书、毛主席画像及像章,还有登有他五弟模范事迹的《解放军画报》。而让我的村庄沸腾并为之骄傲的是赠送给军属呱嗒的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是全村人见到的第一辆真正的自行车,人们围着它转来转去,为能亲手摸一摸而自豪。大队也为了照顾英雄的哥哥,便安排呱嗒三伯到大队里当了通讯员。那个时代,通讯员也是万千人中的佼佼者。从此,只要村头响起“丁零零”的自行车声,不是邮递员就是呱嗒三伯报喜或报忧的通知。村头吸着旱烟袋的老人们,看着呱嗒三伯一跷腿飞身上车,睁大着眼睛一直追看到老眼昏花,人和车都消失在田间村头中,才回过头唠叨着:“唉,咱家要是也出个军官就好了,八辈子的福哟。”
自行车就是呱嗒,呱嗒就是自行车,名人加名车,成了一道乡下难有的绝配。谁家想说个媳妇,媒人和呱嗒骑着车子走一趟,准成;闺女想嫁个好婆家,由呱嗒骑车去一打听,对方拍胸应诺。呱嗒看到了自行车的神奇魅力,就格外地呵护,甚至车比人都金贵。车架上,大梁上,凡是车子不转动的地方,都被缠上保护胶条,外面再缝上布套。天一阴,呱嗒便步行去大队部,偶有赶在路上下雨时,呱嗒便把草帽或其他遮雨的东西盖在车子上,扛着车子回家。我记忆中的呱嗒三伯已是五十多岁的年纪,每看到他雨中扛着车子吃力地回家,雨水顺着干瘦的身子,落汤鸡似的往下流,我就纳闷:到底是人主贵还是车子主贵?
三
呱嗒三伯解放时就已过了而立之年,加上他有哮喘病,虽是风光无限却是光棍一条。他的二哥在1960年“断伙”时被饿死,大哥是生产队的老保管,近六十岁的人了也没有家小,只有四弟、五弟后来娶了媳妇。但老四媳妇因年轻时太漂亮出众,被街上的恶霸和地痞霸占多年,吃香的喝辣的惯了,就像现在的小蜜或二奶,不在乎婚后生育不生育,能享受就行。还听说她结婚后还风流不减,一天晚上和人鬼混时被丈夫撞见,那人一刀劈下,把我那可怜的四伯当头劈开个大口子,险些丢了性命。
呱嗒三伯为家庭的后继担忧,就四邻八村地为四弟抱养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为占有一份土地,男孩过继给自己,也算是有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我叫龙哥的,他1960年生人,比我大三岁。儿童时为替家里挣工分,暑假时到地里割草,公子哥总是篮子空空,他就拿些糖块或街上孩子们玩过的破玩具,引诱着我们替他割草。他坐在地头或坟边的树荫下哼着小曲,我们却为挣一小块糖而拼命干活,中午或傍晚回家时,每人均一份给他,他的大伯又负责收草时过称,他也就一天又一天混过干活的假期,开学后,就到镇里上学去了。我四伯家还有一个叫凤的姐姐,到乡下来玩时简直就是一朵花,女孩子们争着看她的蝴蝶结和花裙子,她的漂亮也勾动着乡下的懵懂少年们,当然也包括我。后来她当知青,返城后嫁在唐河县城,现在已经儿孙满堂,80年代我在唐河教书时曾去看她,提起童年之事,她说好些都忘了,只记得一次在寨河里洗澡,呛水被淹个半死,被大人们捞上后搭在牛背上来回跑动,水倒出后又活了过来,以后便再也不敢下水了。
四
我上初中的1976年,呱嗒的五弟、军官五叔回来探望已八十多岁并有点老年痴呆的母亲。又是一队锣鼓红花和几辆小包车(吉普车)开进村里,让乡下人再一次大开了眼界。这次,军官五叔在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挨家挨户串门,给小孩们留袋糖,给老年人一包烟或一袋点心,有腰酸腿痛或风湿麻木的,就取下随身的针为人针灸,好些老人感动得泪如雨水,拉着五叔的手不放。他每天总是早早地起床,背个粪筐子满村转悠,然后把拾的粪倒进集体的大粪坑;他挽起裤管、打着赤脚为雨后集体的庄稼排水、培土;他掏出自己的钱为村里修桥铺路。他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娃子,好好读书,将来为国家做贡献。五叔没文化,耽误了好些事,你们现在多好哇!”并把一支粗大的英雄牌钢笔插在我的书包上。这支笔,伴我度过了初、高中五年的学习生活,现在,仍和我的老海鸥牌120相机一起,被视为家宝。
五叔秋后走时,带走了已哮喘得有些驼背的呱嗒三伯。到春节回来时,他家便成了村子里的新闻中心。
呱嗒三伯说:那东北实在是太冷了,说句话就得快点,不然,张开嘴就合不上了;耳朵是不敢摸的,一摸就会掉下来。还说,苏联的老毛子开着坦克想过江侵犯咱们国家,解放军猛轰,但不对着毛子打,而是炸冰,冰一塌,老毛子连同突突的铁疙瘩一同沉到了江里。还说我五叔在军队里是个大官,当兵的见了都“啪”的一个立正,敬个礼说“首长好”,并经常小车来小车去的,每顿饭都有红烧肉。东北的鸭子也比咱这里的大,一只头和脖子就一大盘子。他说回来是怕在那儿住久了,胖得走不动路,等等,等等。说得村上的人跟听说书似的,一愣一愣的,心里向往着东北的大鸭大肉,只是害怕那里太冷会冻掉耳朵。
呱嗒三伯讲的东北,多少年来都萦绕在我的脑际,填充着东北和军人生活的神秘和我的向往,并形成一个梦想的情结。直到新世纪初,我去黑龙江参加一个笔会,并绕道看望了当年的军官五叔。想起呱嗒三伯讲的那些东北往事,我不由得笑出声来。
其实五叔那时只是一个享受团职待遇的军医,因针灸治风湿和胃下垂出了名,又是学雷锋标兵,曾受到过周总理接见。80年代末离休,离休时享受副师级待遇,现在仍休养在沈阳第二干休所。他双目几近失明,腿也半瘫状态,下床走路都困难。他拉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小时还吃过我光荣花婶(我亲奶奶,我爷爷叫光荣)的奶。你三伯(指呱嗒)死时我就想回去,一是眼睛不好使,二是走路困难,就叫你几个妹们回去了,我很想念老家,也多想在老宅上再住几天,可是人老了,回不去了。”我安慰五叔道:“三伯一生走村串户,虽没文化,可也没少给庄上办好事,晚年五保,乡里、村里都照顾得很好,他那个身体,能活过七十岁,也算高寿了。当年上级奖的那个自行车,也遵照他的遗愿陪葬了。也许若干年后,还算个古董或宝贝呢。”说得五叔笑了起来,病患的痛苦在谈论家乡的往事中消减着,故土、老家,看来在每一个游子心中,都不会抹去。
如今,我已人到中年,已融入城市的喧嚣生活,回想起乡村往事和乡村人物,总难以释怀。虽然物质和时代的洪流撕扯着我,不自觉地陷入其中,但我对生活并不是一个有太多奢望的人,那些从我手下或身边走出去且发了财的大款,我实在没有羡慕或嫉妒的心理。看他们一天到晚苍蝇猎狗般地忙碌,飞机火箭般地奔跑,磨破嘴皮地奉迎交易,真是让人心痛。唯一值得保留和珍藏的还是那一点对于生命的原初记忆,贫穷但很干净的童年生活。它们真像一杯浓淡相宜的老茶,虽苦点,却越喝越有味,有味得甚至无法说出或描绘,只能闭起双目,保持沉默。
乡村人物之五:中校吴天
一
卑微的乡村总是和卑微的牲畜家禽连在一起,但土地并不卑微,再高贵的人,谁能永远悬在空中。俗话说,脚踏实地,只有踏着实地,人才会心里踏实。悬在空中,弄不好会摔得粉身碎骨。所以,你别小看了乡村和土地。深山出俊鸟,乡野出高人。冷不丁的一两个人物,也会弄出一段悲喜剧甚或惊天传奇和历史。吴天就是我的乡村人物之一。
吴天也叫乔天,十几岁前是离乔湾有十五里地的吴庄人,原随父姓,父亡,随改嫁的母亲来到乔湾,改叫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