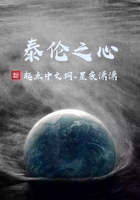白箫已知两人是师兄妹,忙答应了。那老人向婆婆笑道:“这丫头很会吃,你烧的够她吃吗?”说着向白箫做了个鬼脸,白箫顿时觉得老人甚为亲切,不由得笑了,急着离去的心也暂时放了下来。
老妇人笑道:“你走的时候不是说一个月后回来吗?今天刚好是一个月,我估量你要回来,一早就多弄了几个菜,还怕你们吃不了呢。
玉箫,好孩子,都是山里的野菜,别嫌弃。”
白箫这才笑道:“姥姥,瞧您说的。”
老妇人一听白箫开口唤“姥姥”,不由大喜,一把搂住了白箫,却又流下泪来,叹道:“可惜姥姥眼睛瞎了,看不见你。”
那老人忙走过来劝慰:“师妹,你外孙媳妇上门,是一件喜事,怎么反倒伤心起来?”
白箫见两个老人彼此关心对方,心中不免感动,但见那老妇人行动自如,显是有武艺在身,再加上长期居住在此,已经习惯了山里的生活。
午餐也是简单,不过是嫩笋、鲜菇加野菜,但味道却清新可口,十分受用。
饭桌上老人很少开口,待到饭后,三人回到房中,老人才开了腔:
“玉箫,你听说过沈英杰的名字吗?”
白箫一听,疑惑地看了老人一眼,忙道:“知道。是我的太师父,雷震派的开派人,义父常提起的。莫非你——”
婆婆已在一旁接口道:“孩子,他就是你太师父呀。赶快行礼呀。”
白箫的确常听义父提起太师父。义父还对她说过,他之所以要大操大办他们的婚事,就是为了惊动太师父来参加婚礼。可惜太师父没来,两人始终没见面。白箫想到九泉之下的义父,想到自己的际遇,禁不住感慨万分,当即双膝跪地,行了大礼。
沈英杰受了礼,命她坐下,细细说起往事来。
“我与你外婆年轻时是同门师兄妹。我们那时原是郎有情妾有意的,后来我迷恋武学,便到别处去拜师学艺了,等我回去,你外婆已被她父母接回许配给了文镖师。你外婆本来是不愿意的,可既找不到我,又难违父母之命,只得嫁了过去。后来我回师门,知道你外婆嫁人了,无可奈何,发誓不娶。后来偶然遇到陈南城,救了尚在襁褓中的你师父,因与你师父十分投缘,这才应他家邀请,做了你师父的师父,创立了雷震派功夫。这样一过就是十八年,这时你师父要娶妻了,女家由我做主定的就是你外婆文家!我原在徐家隐身,正好那时我有个朋友让我替他去找个人,我想离开徐家也好,免得再见你外婆,彼此尴尬。可谁知天意弄人,竟让我在查访时无意中救了你外婆——当时她险些被红筹寺的道士划花脸,幸亏我及时赶到。我原本就在那房子周围转悠,找的那个人那时就住她家附近,那晚见文镖师家房门大开,我觉得奇怪,一进去才知你外婆受袭。”
白箫已从陈南城处听说过文镖师家当年的那宗案子,便问道:“那些道士可是为了五真碗而来?”
“正是。”沈英杰叹气道,“当年,为了那个破碗,我们可没少遭罪。
那晚,我救出你外婆后,便将她带到客栈。本想让她先歇口气,等天亮了,我再把她送到云台山庄去,谁知,那日半夜,我们在客栈遭遇突袭。那人本是跟着那两个道士到文家,想夺回那个木碗的,不曾想他到文家的时候,两个道士被打翻在地,木碗不翼而飞,于是他想到了我——我抱着你姥姥离开时,正巧让他看见了后背。他后来使他的弟子满城找我们,终于在那客栈将我们逮到。他向我们要那木碗,你姥姥就是为了那只木碗才被那两个道士打伤了,故而一听他要木碗,立即跟他吵了起来,后来自然就打开了。那厮将我俩打伤后,听我们说木碗真的不在我们这里,便又返回了文家。他临走时让他的弟子看着我们,还放言,若找不到木碗,还会回来。不大一会儿,他就回来了,他说文府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碗和两个道士都不见了。他认定我跟你姥姥拿走了木碗,于是我跟他自然又是一番恶战,最后你外婆身受重伤,我也被他打伤手脚,无法动弹。后来,你外婆拖着伤残之身,历经千辛万苦与我逃难到此人迹稀有之处,才避过那人的追杀。可怜她双眼因没及时治疗,就此瞎了,我瘫在床榻二十年才疗好伤,重练武功,今年才下山回宿城。”
白箫听得惊心动魄,这时才插嘴道:“那个打伤你们的是何人?”
“那人便是蓬莱派的甘傲天,人称神仙手,掌上功夫一流,在江湖上名头不小。你或许也听说过他。”沈英杰道。
“他的名字我是没听过,”白箫道,“但我此次去临沂,听说过蓬莱派的名号。”
“临沂?你去了临沂?”老婆婆朝她这个方向伸长了脖子。
白箫知这两位老人都是可信赖的亲人,便也畅所欲言起来。
“因为我和陈老掌柜都觉得,义父的死、滨哥的失踪及当年外公家发生的事彼此之间似有些牵连,所以觉得该去临沂探个虚实。”白箫说罢,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跟义父之间的渊源,及她在费县如何找到王仲昆,又如何顺藤摸瓜在临沂找到李家旧宅子的经过一股脑儿说了出来。两个老人全神贯注地听着,等她说完,沈英杰忽道:“原来你是远樵师叔的女儿。”
白箫听不懂。
沈英杰笑了起来:“你恐怕不知道,你爹白志远也是蓬莱派的人,而且辈分高得吓死人。”
“我爹也是蓬莱派的?”这可是白箫头一次听说。
沈英杰摸着白胡须道:“你爹白志远从小被玄净老道姑的师父收养,后来就当了他的徒弟。不知是因为你爹天生不宜练武,还是他自己不喜欢,师父教他的武功,他一样都学不会。后来太师祖就将一本古人验尸的书丢给了他,原是让他解闷的,没想到,他对此倒是情有独钟,从那以后他就开始钻研这一行了。你爹在蓬莱派,我们都管他叫远樵师叔,他是玄净的师弟,四岁到十三岁,他一直跟着太师祖到处远游,到了十五岁就离开蓬莱了,故而没几个人认识他。”
“我爹原来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那自然。那时岛上出了人命案,你想想,若非他是蓬莱派的人,以他为官府做事的身份,玄净老道姑岂会求上门?当年若不是他,没人知道那是觉乘干的。这事之后,觉乘就离开蓬莱了……”沈英杰说罢,有些感慨地长叹了一声。
“那太师父,你在蓬莱是什么辈分?”白箫好奇起来。
“我啊,论辈分还比你爹低一级,我得叫玄净师伯,我过去的师父是玄净的师妹。明白了吗?”
白箫忽然又想到,“那外婆是你的师妹,外婆也是蓬莱派的?”
“才不是。”外婆笑道,“你太师父就喜欢四处拜师,所以什么门派都有他的份。”
“原来是这样啊,”白箫也笑了,“那我可要向太师父好好讨教几招了。”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沈英杰朗声道,“老实说,以你现在的功夫,只能打几只鸟,打人嘛,我看还差得远。你今晚就别走了。”
白箫看天也快黑了,心想,也罢,今天就暂住一晚,明日让太师父指点一下功夫便下山,希望这次能把陈掌柜顺利救出来。这时,她听到外婆在问她:“丫头,你刚才说,你到过那姓李的宅子里,可有什么发现?”
“我和庆叔发现了几个黑木碗。”
“哦?”沈英杰皱起了眉头。
“我们拿着那几个黑木碗还去找了当年办案的仵作,仵作说,挖到枯骨时,他们也找到几个木碗,后来觉得没什么用,就给扔了。”
“那碗有何特征?”沈英杰问。
“有两个的外皮只漆了一半,有的表皮还是原木,没漆过。我估摸着那些碗可能跟死人有关,于是就到县衙去查了前几年的失踪记录,发现就在文镖师——哦,不是——外公出事的那一年,县里真的有个木工失踪了。他老婆还到县里去报过案。我和庆叔那天去找了那人的老婆,她说那时有人请她丈夫到府里去做活,她丈夫离开家时跟她说,雇主是蓬莱派的,出手很大方,让她放心,两个月后就回来。可谁知这一去,竟杳如黄鹤。”白箫说到这里,外婆又伸手过来摸了摸她的手。
“我外孙媳妇真聪明。”
白箫被夸得心花怒放。过去义父总说她勤奋,滨哥只说她美,可是聪明倒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说。
沈英杰笑道:“嗯,是有几分小聪明。可那人怎么知道对方是蓬莱派的?”
“我也是这么问的。他老婆说,他跟那个雇主见面时,有人来找过这个主顾,他耳边听到了两句话,故而知道他们是蓬莱派的。”白箫言罢,又问:“外婆,当年最后一趟镖是不是一个姓李的托的?”
虽然王仲昆的话将她引向了李公子,这李公子也确实种过茉莉花,在他的宅子里也曾发现过枯骨和丢弃的黑木碗,可要将这些事要跟文镖师的惨案联系在一起,还需要一个正式的确认。
“对,那人是姓李!”外婆的语气很肯定。
白箫心头一松,这下确认无疑了。
“外婆,你可曾见过此人?”她又问。
“我没见过,只听说他是京城什么大官的儿子,因为跟老爹闹别扭才到我们这个小城来落户的,他好像没什么爱好,就爱种个茉莉花。
这也是我听那些镖师说的,有一两个见过他,都说他很年轻。”外婆道。
“我爹当年被杀时,身上藏着一张纸,上面提到过一个人,我爹说那人已经长大成人,但锦绣依然。我总觉得那好像是在说个女人,而且一般只有女人才会特别喜欢茉莉花的吧。我爹过去若曾在蓬莱派学艺,那他说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蓬莱派的。”白箫朝沈英杰看过去。
“若他是蓬莱派的,认识他爹的时候还很年轻,你说那会是谁?”
外婆也看着沈英杰。
沈英杰琢磨了一会儿道:“……呵呵,倒让我想起一个人来。”
“谁?”外婆忙问。
“皓月。皓月五岁就到蓬莱了,当时远樵还没走,他们可能认识。
皓月当时在岛上可是个出了名的小美人,据说很顽皮,经常闯祸,为此青木常替她受过。二十年前,她大概十六岁,应该说是青春年少,跟五岁的她比,自然算是长大成人喽……至于那些茉莉花,恐怕除了她自己喜欢,也是为了掩盖尸体的气味。——咦,你说有两副枯骨?”
沈英杰忽道。
“是的,有两副。”
“其中一个你说是那个做碗的匠人,那另一个呢?”
“仵作说是个女人,死亡时间跟那个工匠相差几个月,或者一年。
他说时间太久了,只能查出这些。”白箫说到这里,忽见沈英杰眉头紧皱,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心里纳闷,便问:“太师父,你想到了什么?”
沈英杰没说话,站起了身。
“好好地说着话,你又要瞎忙什么?”外婆马上道。
“今儿个早点休息,明儿我便代她师父授艺,教她一套功夫。如今我老友陈南城父子被抓,我也是心急如焚,只等着快点教她些,也好下山救人。”
白箫一听他要跟她一起去救人,不由心中大喜。
这时沈英杰忽然大声对白箫道:“徒孙,你对我跟你姥姥的事儿好奇吧?不妨告诉你,三十年来咱们厮守在一起,早已由天地山川做媒,结为夫妇。所以我不仅是你的太师父,还是你的姥爷!”
“你——小点声,让小辈笑话!”外婆竟有些害羞。
白箫正在不知所措,沈英杰却又大声道:“笑话什么!咱俩从年轻时相爱,只因我错过了机缘,才让你姥姥嫁了文家;后来咱俩患难之中相依为命,她照顾我这个瘫子,我怜惜她盲目,她这才嫁了我,难道有错吗?老实说,只要咱俩确有情意,我才不在乎旁人说什么呢!
徒孙,你说对吗?”说罢便瞪着白箫。
白箫被瞪得不知所措,垂下了眼睑。不过,她心里却觉得着实别扭,总觉得外婆似乎应该为外公守贞的。
外婆虽双目失明,却仿佛窥见了她的心思,只听她缓缓道:“外孙媳妇,在当时千难万险的情况下,我俩要彼此照顾,也无法避嫌,我再三考虑,才嫁给了你太师父。更何况,我们两人在学艺时本就相恋,是我父母拆散了我们,也是你太师父出外学艺,迟迟不归才错过了婚姻。我们是武林中人,特别已到了暮年,只要问心无愧,不必顾忌那种礼数的。这与世人寻花问柳、朝三暮四是不同的,孩子,你懂吗?”
白箫听了外婆一番肺腑之言,心中豁然开朗,高高兴兴站起身来,向两老施礼,大声道:“外孙媳妇祝贺两老百年恩爱。”
沈英杰这才哈哈大笑道:“乖徒孙,叫姥爷吧。现在咱们真的是一家人了。明儿就教你功夫。我看你练得不怎么样,你师父的剑招威力没使出来,内劲不行,底子也不足,要补补。”
这一晚白箫就在这嵯峨的绝崖入睡,室外松涛起伏,劲风怒号,她却睡得很安稳。
第二天一早,白箫还没睡醒,就听得太师父在叫:“懒姑娘,练功去了!”又听到姥姥在低声道:“你别喊,她累了,让她多躺一会。”
“你总是妇人见识。岂不闻‘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
“她是男儿吗?”
“她可比一般的须眉还男儿呢!有丈夫要找,有师仇要报,更有师门绝艺要传承,担子重着呢!还有,玉不琢,不成器,她这块玉,全靠我们磨炼了。你说我能对她不严厉吗?”
“那总得给她吃好点,长结实点吧,咱们藏了的……给她吃了吧……”
下面的话白箫听不明白,但两老的话却大大地感动了她。原来太师父对自己这般青眼相看,自己一路上还跟他闹别扭,又险些将他视为歹人,姥姥又这般慈爱,就像自己的亲娘一样。想到此,她一跃而起,大声道:“姥爷、姥姥,我起来了!”
外婆惊喜道:“这么早就起来了?该多睡会儿!”
“可不能让姥爷叫我懒姑娘呀!”说着朝沈英杰调皮地一笑。
“呵呵,勤快可不在嘴上,”老人笑了笑,“快去吃早饭吧,你姥姥早弄好了!”
果然有好吃的,大包子、糯米糕、烤野味……白箫直吃得酣畅淋漓。
两个老人见她吃得这么香,都喜上眉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