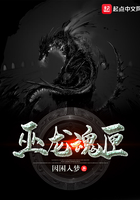在第二天的早晨六点,诺第留斯号准备开走了。这时,这里已经完全变成极夜了,天气冷得很,温度表显示为零下十二度。海面渐渐冻结,无数灰黑的冰块在水面上漂浮着,这表示新的冰层形成了。很显然,在冬季六个月里,南极的海面全是结冰的,根本无法通过。
这时,诺第留斯号慢慢下降。直到一千英尺深的时候,它停了下来。然后,它以每小时十五海里的速度向北方驶去。
这一天,我一直在整理我的笔记。我心中也一直在想南极点的情形。我到达了这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没有任何危险,从没觉得疲倦,现在又踏上归途了。还会有新鲜惊奇的事发生吗?我想一定还有的,海底的神奇世界可真是奥妙无穷啊!不过,从那个偶然的机会开始,我们在这只船上有五个半月了,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走了一万四千里,有多少或新奇或可怕的偶然事件让我们惊心动魄啊!这一切让我们的旅行充满了无穷的乐趣。克列斯波林中打猎、托列斯海峡搁浅、珊瑚墓地、锡兰采珠、阿拉伯海底地道、桑多林火海、维哥湾亿万金银、大西洋洲、南极!夜间,所有这些像梦一般连续着,让我的脑子一刻也不能安息。
早晨三点,一下猛烈的冲击把我惊醒了。我马上坐起来。这时,我突然被抛到了空中。很显然,诺第留斯号肯定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引发了很厉害的颠簸。我靠着墙板,小心地沿着墙到走廊,又从走廊慢慢到了客厅。大厅里面灯火通明,家具都翻倒在了地上。庆幸的是,那些玻璃柜没有倒下来,因为它们的下部钉得很结实。诺第留斯号是靠右舷倒下来,并且一动也不动了。我听到从船内部传来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不过我没有看到尼摩船长出来。就在我打算离开客厅时,尼德·兰和康塞尔进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马上问他们。
“我正要问您呢。”康塞尔回答。
“真是奇怪!”加拿大人喊,“诺第留斯号到底碰上了什么,从它躺下的情况来判断,我想这一次跟上一次在托列斯海峡中遇到的情况不一样,它不能脱身了。”
“不过,”我问,“它至少能回到水面上吧?”
“我不清楚。”康塞尔回答。
“确定这事是很容易的。”我说。
我一看压力表,感到非常惊讶,表指着三百六十米深的水层。
“怎么会这样呢?”我喊。
“我们去问尼摩船长吧。”康塞尔说。
“去哪里找他呢?”尼德·兰问。
“跟我来吧。”我对我的两个同伴说。
我们离开客厅,先是去了图书室,又来到船员工作室,结果都没有找到船长。我想尼摩船长可能是在领航舱,我们只好等着。于是,我们三人又回客厅来。
等了二十分钟后,尼摩船长进来了,他像没有看见我们一样。他安静地看看罗盘、压力表,把手指放在地图上标出南冰洋的这一部分。我不想去打扰他,过了一刻,他向我转过身子来,这时我才问他:
“船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他答,“先生,只是发生了一次意外事件。”
“严不严重?”
“可能很严重。”
“那么,有没有危险?”
“没有。”
“是不是诺第留斯号触礁了?”
“是的。”
“这次为什么会触礁呢?”
“是大自然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人们的无能。在我们的指挥驾驶中,并没有犯一点错误。可是,我们还是不能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那么,”我问,“您能告诉我这次事故发生的原因吗?”
“整整一座冰山,翻倒下来了,”他回答我,“当冰山下面在受温热的水流,或者是来回的冲击耗损的时候,它们的重心就往上移,那时它们会发生幅度很大的翻转。我们遇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它们其中的一大冰群翻倒的时候,正好撞上了在水底行驶的诺第留斯号。它们随后从船身下溜过,又使出巨大的力量把船顶起来,这些冰把船带到浅一些的水层,并且在船身上靠着不动了。”
“我们把储水池的水排出去,使船重新得到平衡,这这样的话,诺第留斯号不是就脱身了吗?”
“我们目前就在这样做。您可以听到抽水机正在运作。压力表上的针指出诺第留斯号正在上升,但冰群跟它一起向上,除非有一件障碍物挡住它向上的运动,否则,我们的地位还是不能改变。”
果然,诺第留斯号一直在那里倾斜着,不过在冰群自己停下的时候,船就可以站起来。但在这个时候,谁能保证我们不会碰上冰山的上部,被挤在两个冰面中间呢?我想象着在我们所处位置可能发生的一切后果。
船长不停地注视着压力表。冰群倒下来后,诺第留斯号只上升了一百五十英尺左右。忽然船体出现一阵轻微的颤动。很明显,诺第留斯号开始站起一点了,悬挂在客厅中的东西又恢复了它们原来的位置,墙板也接近垂直。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就这样看着这一切。忽然,我们感到船竖起来了。我们脚下的地板又变为横平面了。十分钟过去了。
“看呢,我们站起来了!”我喊。
“是的。”尼摩船长说,同时他向客厅门走去。
“但是,我们能往上浮吗?”我问他。
“当然能了。”他回答,“不过现在储水池还没有排水,等排水后,诺第留斯号自然就会浮到海面上。”
船长离开了,不久,诺第留斯号停止了上升。它可能碰上冰山的下部,让它留在水中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侥幸脱险了!”康塞尔说。
“对,我们可能在这些冰块间被压扁,至少被困往。那时,因为不能调换空气,……是的,我们侥幸脱险了!”
“它完蛋了才好呢!”加拿大人低声说着。
我不想跟加拿大人进行没意义的争辩,我没有说话。
此刻,在距离诺第留斯号的两边十米左右,各竖起一道雪白眩目的冰墙。船的上、下两方,也有这样的冰墙。船上面,由于冰山的缘故,它看起来像宽阔的天花板。诺第留斯号看来是被困在真正的冰的地洞中了,不过这个地洞有二十米左右宽,里面是平静的水。因此,船是不难出来的,或前进,或后退,然后再往下数百米左右,在冰山下面找到一条通路就行了。
天花板上的灯熄灭了,不过,客厅中还有辉煌的光线照明。受四面冰墙的强烈反射,探照灯的光波也被反射进客厅中来了。此刻,冰上的每一角度,每一条棱,每一个面,都反射出各种不同的光线。这仿佛珠宝玉石的眩人眼目的绚丽光芒,蓝宝石的蓝光和玻璃翠的碧光交织起来,处处布满了无限柔和的蛋白色调,散布在晶莹的尖点中间。
“好美!”康塞尔喊起来。
“真的很美!”我说,“尼德·兰,这是多么好看的景象啊!”
“真美!”尼德·兰回答说,“真壮丽!人们从没有看过这样的景象。不过这景象可能会让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我要尽情说出来,那我想,我们眼前看见的事物是上帝不许凡人看见的!”
尼德·兰说得对,真是太美了。忽然,我听到了康塞尔的喊声。我回过身子来,问:“怎么了?”
“先生,不要看了!把眼睛闭上!”
康塞尔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已经被手遮住了。
“怎么啦?”
“我眼睛花了,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向玻璃边看去,那光我受不了。
我明白这件事的原因了。当诺第留斯号在快速地行驶时,所有冰墙上静穆的光辉于是变成闪闪的光芒,这无数的光就混合起来。当我们的眼睛被阳光过度猛烈地照射后,眼膜上就浮游着强力集中的光线,我们现在就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用两手挡住眼睛。要过些时候我们的眼睛才能恢复正常。后来,我们把手放了下来。
凌晨五点,诺第留斯号的前端发生了一次冲撞。我知道它的冲角肯定是碰上了冰层。这可能是由于这条海底地道受冰群的堵塞,不易航行,正好船不小心碰上了。因此我推断,尼摩船长是在改变路线来绕过这些障碍物。总的来说,障碍是不可能阻止船前进的。不过,令我想不到的是,诺第留斯号分明是向后倒退而行了。
“难道我们要倒回去吗?”康塞尔说。
“对!”我回答,“恐怕这一边没有出口了。”
“那么……”
“那么,”我说,“很简单,我们倒回去,再从南口出去就可以了。”
我这样说是想表示我心里很平静,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诺第留斯号这时倒退着开行,速度分明是愈来愈快了。
“这样是耽搁时间的。”尼德·兰说。
“早点晚点都没关系的,只要能出来就行。”
我在客厅到图书室之间不停地走动着。我的同伴们坐着,谁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躺在长沙发上,拿起一本书来看。几分钟后,康塞尔走过来对我说:
“先生觉得这本书很有趣吗?”
“很有趣。”我回答。
“我想应该很有趣。先生所看的书是您自己写的书吧!”
“我自己写的书?”
仔细一看,我手中拿着的正是自己写的书。真没有想到。合起书,我又开始来回地走起来了。尼德·兰和康塞尔两人站起来,想要离开。
“等一等,”我拉住他们说,“我们都不要走,直到我们退出这条走不通的道路再离开吧。”
几小时过去了,我看了看挂在客厅墙壁上的机械压力表,它告诉我们诺第留斯号保持在三百米深的水层中,罗盘指向南方,测程器记录的速度为每小时二十海里。
到了八点二十五分,又发生了一次冲撞,这一次是在船的后部。我的同伴们来到我的身边,我拉住康塞尔的手,默默无语,这种情况真的让人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时候,尼摩船长走进来了,我向他走过去,问:“难道南边的路也堵住了?”
“是的,现在,冰山把所有的出口都堵住了。”
“这就是说,我们被困在这里边了?”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