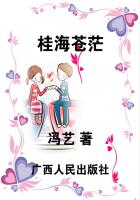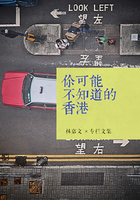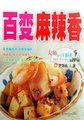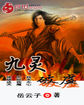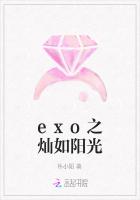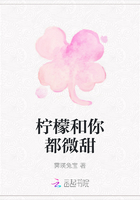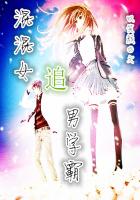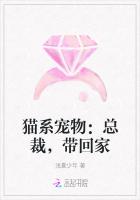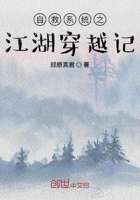子: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
子,十一月乾气动,万物滋,人以为偁。象形。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从前有一位秀才,胸无点墨还自以为是。一天,他拿起《韩非子》一书摇头晃脑地诵读,在众人面前装出很有学问的样子。当他读到“卫子嫁其子”一句时,突然停下来,感慨地说:“这卫国人真是糊涂,儿子怎么能出嫁呢?”其实糊涂的是秀才自己,他连“子”字在古代既指男子也指女子都不知道,所以才闹了个大笑话。
“子”是一个象形字,《说文解字》李阳冰注:“子在襁褓中,足并也。”其甲骨文是根据“襁褓婴儿”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两手连成一斜短横,身和下肢已简化成一条稍斜的垂线,强调了婴儿头大的特点,这是符合身材比例的。早期的金文是实化的,就像“襁褓婴儿”一样。到了晚期金文,其头部轮廓化,上肢和躯体已瘦化为线条了。小篆与金文中的字形并无太大的差异。发展到汉隶时,形体起了很大的讹变:“子”头变成三角形了,两只小手平伸,变成一横了,躯体和下肢变成弯竖了。楷书便是由此衍化而来的。
从“子”字的造字便可以看得出其本义指的是“婴儿”。在古代汉语中,“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分性别的。《仪礼·丧服》:“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郑玄注曰:“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显然这里的“子”既指男孩,也指女孩。由此引申为人的通称,既可指男人,也可指女人。除此之外,“子”的引申义还有很多,如“子”在古代用作尊称,如孔子、孟子。“子”还可表示某种次序,在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中,子爵是第四等爵位;作为地支,“子”排在第一位。汉字中凡从“子”的字,大多与婴孩或子嗣有关,如孩、孙、孝、孕等。
孩子,在父母的心中永远是那个长不大的样子,因而关注与教育便是天下父母一生的事业。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虽然这句话未免有些偏激,但也体现了一种教育的理念。叱责确实是教育孩子的一种方法,但是怎样责骂却大有学问。有人说:“懂得骂孩子的父母,同时也最懂得夸奖孩子。”爱孩子是需要技巧的,应该多了解孩子,体察孩子的心,并配合孩子的生活方式来教导他们,这才是正确的爱。孩子,是一块尚未经过雕琢的璞玉,如果雕刻得好,能够价值连城;如果雕刻得不好,就会被遗弃于草莽。因此,做父母的既要用爱心去感化孩子,也要用严格的标准教育孩子。毕竟,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儿:尊敬长辈,也不能轻视小儿
儿,孺子也。从儿,像小儿头囟未合。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古时,一个妇女为一只猫和邻居家发生争吵。妇女说:“若是儿猫,即是儿猫;若非儿猫,则非儿猫。”妇女的话中第一句和第三句中的“儿”字,是“雄性”的意思;第二句和第四句中的“儿”字是“我的”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是:如果是雄性猫,就是我的猫;如果不是雄性猫,就不是我的猫。邻居听不明白,经过别人的指点后才理解了其中的意思,最终解决了问题。
一个简单常用的“儿”,却有如此多的含义。《说文解字·儿部》云:“儿,孺子也。从儿,像小儿头囟未合。”可见,“儿”的本义就是指儿童。其甲骨文看上去像一个面朝左站着的大头娃娃,头顶上还开有一个小口子,这就是许慎提到的“头囟未合”。脑袋下面部分向左伸展一笔是小儿的手臂,右边弯曲一笔是小儿的身子和腿。整个字形生动地描绘了一个儿童的形象,所以,“儿”是个象形字。金文字形基本未变,只是儿童头顶上的那个小口子变得更大了。发展到小篆,“儿”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突出的头部特征已经消失,但仍可看到“儿”的影子。在此基础上,逐渐演变成了现代楷书。
在古时,“儿”同“子”一样,既可指男性,也可指女性,如《木兰诗》中的“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和《孔雀东南飞》中的“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中的“儿”都是成年女子的自称。但“儿”较常用的还是指男性,所以引申为“雄性的”之义,如顾炎武《日知录》中的“今人则以牡为儿马,牝为骒马”。此外,“儿”字还可作为词尾,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儿”,幼小的代名词,似乎也总给人一种稚嫩的感觉。丰富的经验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管理者心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面对重复性的工作时,拥有经验的人,总是可以快速掌握状况,完成任务。经验代表的是一种自信,是一种从容。但经验并非万能,尤其是在高速发展的今天,别再用“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为理由轻视那些后辈,他们早已不是黄口小儿,他们甚至可能登上更高的山峰。
孙:儿孙满堂,福泽永续
子之子曰孙。从子,从系;系,续也。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最讲究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子孙绵延、多子多福的观念根深蒂固。同时,中国人又很看重延续香火一说,古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子孙越多就越能代表兴旺发达,越是有福气,“孙”字便清楚地表达了这种“多子多孙便是福”的观念。
“孙”在商末周初的甲骨文里,右边像一根绳子,左边是一个“子”字,像用索带套引着“子”学走路,同时,绳索有牵系之义,表示子孙连续不断。战国时代,金文与甲骨文没有太大的变化。发展到小篆,右边的绳子变成了“系”旁。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系部》中所说:“子之子曰孙。从子,从系;系,续也。”在小篆的基础上,出现了繁体,到此时,“孙”字左“子”右“系”的会意字形体结构就完全定型下来了。“孙”字的使用频率很高,于是草书便将繁体简化,之后的楷书便是由草书楷化而来。
“孙”字的字形,很容易让人想到“愚公移山”中,愚公对智叟的回答:“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很明显,这里用的是“孙”字的本义,即儿子的儿子。后来,“孙”字不再仅限于其本义,也泛指孙子以后的各代。古代有关于“九族”的说法,其中的下四代除了儿子一代外,其他的“孙”、“曾”、“玄”皆可称为“孙”。此外,和孙子同辈的亲属也称“孙”,如儿子的女儿叫“孙女”,女儿的儿子叫“外孙”,兄弟的孙子叫“侄孙”等。“子孙”、“子子孙孙”则用来泛指后代。
在传统观念中,子孙越多越是兴旺发达,子孙越多越显得有福气,这种观念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想将家族发扬光大的传统。但是,要想做到代代相传、福泽永续,需要的并不只是更多的“孙”,而是更优质的“孙”。正所谓:“学润身,德润心”,要想家族生命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就应该注重“孙”的教育,让“孙”成为既有丰富的学识,又有高尚品德的人,这样何愁不能福泽永续呢?
长:延年益寿还须复归于婴儿
长,老也。
——(三国·魏)张揖《广雅》
据说,有一户人家以卖豆芽为生,他希望自家的豆芽长得好一些,于是在门口贴了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长长长长长长长”(chángzhǎngchángzhǎngchángchángzhǎng),下联是“长长长长长长长”(zhǎngchángzhǎngchángzhǎngzhǎngcháng)。整幅对联全部是由“长”字组成,且表意清晰,真是妙趣横生。
“长”在甲骨文里上部是两根向右弯曲的长头发,其下是人的手臂和身子及腿,是个弓腰扶杖的老人踽踽独行的形状。主要强调的是人长长的头发,因此有人认为“长”的本义是“人的头发长”。余永梁在《殷墟文字考》中就有:“长,实像人发长貌,引申为长久之长。”由于先民没有理发的习惯,头发长的人,也就是辈分高、年龄大的人,因此“长”的本义就是“老年人”。发展到金文阶段,老人的头发尤其夸张。晚期金文是在“长”字的发展过程中变化最大的,它将原本的拐杖从“丫”讹变为“止”,之后的小篆也跟着从“止”,上部的头发变成了三横。隶书里的“长”,老者变成了“人”,拐杖讹变为“丨”。由此发展出了繁体字的字形。在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草书“长”字的基础上,经过楷化变成了今天的楷书。
“长”字的本义为“头发长”,由此引申出了空间时间上距离大、长度、长处、擅长、多余等含义。此外,“长”还有“老年人”的意思,又引申为长幼的长;又引申指排行第一、辈分大、长官等义。
长生不老,历来是人们的一个愿望,但只是一个奢望而已。一个人的生命从年轻到衰老,是无法抗拒的,而人们总是希望可以延缓衰老,保持年轻。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外界的力量实现自己的这一幻想,却忽略了保持青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一颗年轻的心,它可以为你留住岁月的脚步。
父:父爱如山,虽不言语却一直都在
父,矩也,家长,率教者。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里,父亲都是高大威严的,他们很少会像母亲一样和蔼地对我们嘘寒问暖,他们的态度总是相当严厉,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的爱比母亲的少,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子女的关切。其实这种严父形象,早在“父”字产生之时便已经有所体现了。
在上古社会,“父”是部落之主、家族之长,是最有权威的人物,所以先民在造字之时,便要突显“父”的显赫地位。从甲骨文的“父”字字形来看,“父”像一只手抓住一柄石斧或棍棒的样子。在原始社会,石斧、棍棒是主要的武器和生产工具。而手持石斧、棍棒与敌人作战或从事艰苦的野外劳动,是成年男子的责任。又一说,“父”字手中所握的为杖棒,而杖棒是当时奴隶主用来刺戳俘虏奴隶眼睛的锥形东西。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显示出了在当时的父系社会中,“父”所处的社会地位。他们必须孔武有力,智勇双全,对外能抵御敌人,保卫氏族,对内能使群众信服,治理有方。可以说,“父”是男性中心社会的标志之一。之后的金文、小篆中,“父”的字形与甲骨文中的字形相差不大,仍然可以看到手的形象。但发展到隶书阶段,字的形体已开始从线条变为笔画化,发展到楷书时,“父”字手中所握之物变成第一笔的短撇;上面的手指已分离开来,变成第二笔的侧点;其余的手指和手腕则变成第三笔的长撇和第四笔的斜捺,已经完全看不出“父”字当初的形象了。
“父”的本义就是父亲。《说文解字》云:“父,矩也,家长,率教者。”意思是,“父”是主持规矩的人,是一家之长,是引导教育子女的人。商周以后,“父”便逐渐用作对男子表示尊敬的美称,如尊称老农为“田父”,渔翁为“渔父”。家族制度形成以后,把一家之长称为“父”,如祖父、父亲,把老人称为“亚父”、“伯父”。父,既可单用,也可作偏旁。凡从父取义的字皆与长辈男子等义有关。以父作义符的字有爷、爸,以父作声符的字有斧、釜等。
父亲是威严的,但发自内心的爱总是会在点滴中流露出来。朱自清的《背影》中父亲那蹒跚的脚步触动了心中的那根弦,来自父亲的爱像白酒,辛辣而热烈,容易让人醉在其中;像咖啡,苦涩而醇香,容易让人为之振奋;像茶,平淡而亲切,让人在不知不觉中上瘾。我们或许无法恰当地做出描述,但是真实地沉浸在其中。父爱分为外壳和内质两部分,它的外壳常常是严肃、沉默、无声的,透过这层外壳,我们会感受到父爱的内质——博大、深厚、温柔,它与母爱一样伟大,是人间最为珍贵的东西。
母:世间爱都为相聚,唯有母爱是为更好地分离
母,牧也。从女,怀子形。一曰象乳子形。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一首《游子吟》,让我们感受到了既普通又伟大的人性之美——母爱。母亲给了我们生命,也给了我们生命中美好的一切。千百年来,母亲在人们心目中永远是美丽温柔的,这种印象反映在汉字中,也是一样。
“母”是一个象形字,因母是女性,所以便用“女”作基础来造“母”字。母亲是要给孩子哺乳的,所以先民抓住这一特点,在“女”的胸前加上两点,这就惟妙惟肖地把“母”的形象画出来。
甲骨文中的“母”字,除两点之外的部分为“女”,像侧身站立,低着头,双手收起,屈膝下跪的样子,充分体现了女子的温柔顺从之意。在“女”的胸前加了两点,实为指事符号,点出了这位女子已是袒胸露乳,乳峰高耸的样子,看上去完全是一个正在哺育小孩的母亲。
“母”字的金文与甲骨文形体相似,之后有小篆、楷书,虽然“母”字的字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代表母乳的两点一直保留着,这是作为母亲的突出特征。“母”字的本义为“母亲”,《说文解字·女部》:“母,牧也。从女,怀子形。一曰象乳子形。”许慎认为“母”字形象地描绘出女子怀孕的形状,因而他将“母”训释为“牧”。段玉裁注:“牧者,养牛人也,以譬人之乳子。”许慎认为“母”的本义就是“育子”,即段玉裁所说的“乳子”。应该说“育子”是“母”的引申义。“母”还引申用作女性尊长的通称,如伯母、祖母等。因为母能生子,所以母字也引申指事物的本源。我们把祖国比作“母亲”,因为祖国是自己出生的土地;我们把自己曾经就读过的学校叫作“母校”,因为它用知识的乳汁培养了我们;我们又把最初学会的一种语言叫作“母语”。
母亲的形象是慈爱的,母亲的胸怀是温暖而宽容的,母亲的心是善良的,母亲给予的爱是伟大而无私的,无论身在何处,我们总是被母爱所笼罩着、温暖着。我们应珍惜母亲以鲜血和痛苦、以爱心和乳汁换来的生命,同时,也应以自己最大的努力,让母亲也获得来自子女的爱与温暖。母爱是天下最无私的爱,不论子女长得美丽还是丑陋,不论子女聪明还是笨拙,不论子女成为高官富豪还是沉沦潦倒,母爱都不会改变。母爱永远是人说不完、写不尽的话题。
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
家,居也。从宀,豭省声。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家”是什么?千万个人有千万个说法。有的人说,家是一种文化;有的人说,家是一段时光;有的人说,家是一种情怀……虽然我们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块温暖的天地,家不是房屋,不是彩电,不是物质堆砌起来的空间,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地方,也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舍弃我们的港湾。但“家”字却是由猪圈发展而来的。
在上古的图形文字中,“家”的上部是房子的侧面形(即“宀”),房子下面豢养着长满鬃毛的豕(猪),这是猪圈,也说是“家”。上古时代,先民在树上“架木为巢”以作住所。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才转到地上架木为屋,驯养野兽作为家畜。为防止外来侵袭,房子的结构一般是上居人、下作圈。猪是当时已经驯养的家畜之一,所以,房下养猪就成了“家”的标志。而甲骨文中的“家”已经开始线条化了,“豕”已倒过来头向上了。发展到金文阶段,房形依旧,但“豕”的腹部轮廓线进一步简省,后腿和尾巴变成了交叉形,“豕”的形象已经面目全非了。小篆时期,“家”的字形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了现代楷书中的“家”字字形。
“家”的出现标志着我们祖先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已经成为过去,开始架木为屋,豢养牲畜,进入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业社会,因此才有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氏族社会也进一步形成发展了。
在现代忙碌的社会生活中,人们正在逐渐地迷失自我,越来越多的人感觉自己如同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一般,始终在寻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停靠的码头——“家”。正如“佛在心中”一样,“家”也在每个人的心底。家是一个感情的港湾,家是一个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一个精神的乐园。贫困时,家是一个窝,可以挡风遮雨,抵御豺狼;战争中,家是一个箩筐,一根扁担,扶老携幼,相依为命;和平时,家是一汪平静的清泉,又是一座精神的圣殿,洗去污垢,重返本真。拥有它时,它平凡如柴米油盐酱醋茶;失去它时,掏心掏肝也找不回。珍爱你的家,爱惜你的家人,从容平淡才最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