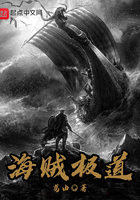有段时间,卓谦很喜欢和果果斗嘴,准确的说,应该是他单方面损果果。
“你是在画你的自画像么?”卓谦嘴一咧,指着果果在草稿纸上的涂鸦损她。
果果当场脸胀红,“你!”
“你干嘛欺负果果啊,不许说果果,这么明显的图案你都看不来,是不是该带老花镜了?”我转身,黑笔在他桌子上敲击着。
“……”
其实果果很有美术细胞,这一点,卓谦和我,心知肚明,只不过,他就是喜欢损她。
果果不是一个懂得语言反击的人,这才导致我经常以老母鸡保护小母鸡的姿态反击卓谦。
卓谦不怎么反击我,是因为他太多“把柄”在我手上。
代购什么的就不用说了,整理文件夹,打扫卫生,抄记作业,随便丢一项出来,就够让他“求饶”。
我们的政史地的任课老师史麦飞,明明是个二三十岁来着的小伙子,却有个“啤酒肚”,看起来是个心宽体胖的人,实际上是个深度洁癖主义者。
政史地的笔记资料很多,他也是个比较“善良”的老师,每次都是会下发打印的资料,不需要我们上课抄板书。资料一多,丢失的可能性就增大的许多,他不仅要我们不能丢失资料,而且他看不得资料乱糟糟地叠放,一定要整整齐齐的收纳在打孔文件夹里,还要用专门的分类纸夹开。
卓谦向来觉得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是不可取的,但是碍于老师的威慑,只能选择服从。大中午,他翻来翻去的在分类资料已经差不多半个小时了,因为下午第一节课就是政史地,已经被老师“关照过”的他,是检查的重灾区。
“啊,这怎么分啊。”嘟囔的声音显得无助,又有一些恼怒,文件夹被他翻得哗啦哗啦地响,“不对,不对,不能这么放,啊呀。”
唉,算了,我捧过他的资料和文件夹,“唉,我来。”
“哇,涟晴你好好哦!”
十分钟后,“那,好了。”我把一本文件夹摆在他面前。
“涟晴,你好厉害!”卓谦翻了翻文件夹,“我付你工资,20块,你从银行扣吧!”
“不用啦,本姑娘今天心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