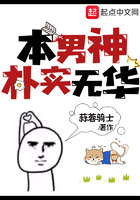江湖是什么?江湖只不过是一群人,一群疯子罢了。
天涯驿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再来过一个外人,毕竟这是大漠最深最远处的城镇,远的让世上的人甚至于忘记了,在这茫茫大漠里,还有那么一个城,也远得让这里的人,忘了这世界上,还有别的人。
有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而江湖到底在哪?杨君尘偶尔会问这个问题,可是如今他想破脑袋我想不到,江湖会在哪,在不远处的廊沧江,还是在不远处的边牧湖?想到这,杨君尘又笑了,这五年来,他已经不止一次的问廖远山,廖远山总是笑着说,江湖在女人的胸脯上,在老子撒尿的盆里。
廖远山是天涯驿真正的主人,平天山是一座客栈,也是一座赌场,天涯驿里那些神态各异,看上去尽皆凶神恶煞的酒鬼赌徒们需要廖远山,不然这大漠里的岁月,却是熬不下去了。杨君尘是五年前跟着廖远山到天涯驿的,廖远山教他最快的剑法,给他最烈的酒,若不是廖远山,杨君尘也不会是杨君尘了。
天涯驿里无好人,近千个居民全是各种各样的恶人,廖远山是最凶狠的,又是最温柔的,杨君尘是最单纯的,却也是最残忍的,这五年来,他为廖远山杀了多少人他已经忘记了,只是院子外被他杀死的人的剑已经堆了一座小山,五年时光,天涯驿里所有敢站在廖远山对立面,敢反对廖远山的人,都已经不见了,杨君尘曾经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厉害的剑了,但廖远山却总是告诉他,江湖,人外人,天外天,七派天上殿,三盟殿上仙,杨君尘心里对那遥远的中原,充满了憧憬,对那所有的江湖,也满是期待。
今天的月亮特别圆,就像是廖远山的刀法,滴水不漏,杨君尘躺在床上,看着窗外,那柄青绿色的墨鱼,安静的躺在他身边,今夜的月亮有些不平常,杨君尘如是想到。
一群奔马的疾驰,打破了夜的寂静,在平天山的大堂前,嘎然而止,然而除了杨君尘,整个天涯驿,没有一个人惊讶,杨君尘一个鱼跃起身,到了大厅,廖远山和手下另外十三个人已经在大厅中坐着,周边站的是平日里凶神恶煞的赌徒们,而门口,站了一个人,紫色的长袍,紫色的帽子,两根长长的带子在帽子两边垂着,面目有些非男非女,他腰间的剑上散发着瘆人的血腥味,杨君尘第一眼见到他,下意识的就握紧手中的墨鱼,这几年所杀的人,和这个人比起来,简直像是牲畜一般。
“你还是来了。”廖远山的神情不像其他人那样紧张,似乎那滔天的杀意跟他没有一点关系,“五年了,平天王这次不逃走了?”那个人说话了,声音有些按耐不住的愉悦,“宋师亲自奔赴大漠,廖某却是不敢怠慢,况且五年前,本该就有这次会面了。”
“可惜可惜。”
“大好月色,宋师又可惜什么了?”
“可惜这天下,从此再无平天王廖远山”
“哈哈,那又如何!廖某人五年前,就该已经死了。”
话音还未落,一柄血色长剑已经破空而来,直刺廖远山面门。廖远山拔刀了,那刀这十八年来杨君尘只见过一次,那快得已经可以泼水不入的刀,这一刻,居然是果断的拔了出来,这十八年来不曾严肃认真的廖远山,第一次,面目凝重,一切说起来漫长,其实也不过是转瞬之间,杨君尘甚至还不曾看清那人的模样,甚至才刚刚进屋。
一切来得太快,杨君尘没有机会问为什么,也不再需要问为什么,那人已经出剑,赌徒们纷纷亮出了武器,廖远山的十三个手下,也把廖远山包围了起来,亮剑易,出剑难,没有一个人去管那个人,因为即使去管,也是无用之举,那剑已经触到了廖远山的刀。
杨君尘在心里却想起一句话,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一群疯子,杨君尘听出了廖远山话里的绝望。没有去拔出墨鱼,他也是快剑,天涯驿最快的剑,但是他来不及也挡不住那个人,而且廖远山也不会让他出手,他突然想起来,这五年里,廖远山不止一次的告诉他,江湖险恶,若是有一日,我们再入江湖,便再没有今日的好生活。
廖远山的刀裆下了那一剑,可是第二剑已经攻杀过来,第三剑,第四剑,两人刚一接触,便像是过了许久,赌徒们已经冲杀过来,十三人也纷纷出剑,大堂内一瞬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世上本来就没有天涯,那里来的天涯驿了?只不过是一群人在等待另一群群人罢了,门外冲进一批紫袍剑客,无数的刀,无数的剑,无数的血,无数的人。
只七剑,廖远山的刀便被破了,宋师一脚便把廖远山踢飞了出去,“五年不见,你却是一点长进都没有。”说完,那人抬手,剑起剑落,廖远山便已经气绝身亡,大厅中弥漫着一股怪异的味道,死?杨君尘从没想过这样的结局,一切来得太快太急,就好像一副绝佳的书法中,突然出现的错笔,突兀,生硬,却又真实,人世间的事大多是这样,没有一点准备,已经如崩山之势。
那人不屑于出手,而天涯驿的人,廖远山一死,剩余的人便都像失了魂似的,任由紫袍剑客们的剑,刺破自己的胸膛,杨君尘不明白,却也不愿意明白了,挥剑挡开两人,冲过去抱起廖远山的尸首,撞破房顶跳了出去,廖远山已经知道今天无法活下去,杨君尘却只关心廖远山能不能活下去。
一声机关扭动的咯吱声在背后响起,杨君尘只觉得背后一阵巨痛,咬牙还是跳出了上三天。
“不用追了,中了断肠针,没有活下来的可能,把这里的人都杀光,屠了天涯驿”宋师不介意跑掉一个虾米,他千里奔袭,不是为了杀小虾米,而是为了廖远山的命,廖远山死了,其余的人在他眼里不过是蝼蚁,没有人会在杀人的时候担心旁边的蝼蚁不开心,也不会惧怕那个小虾米会来报仇,这天下间,也没有人能寻他报仇。
杨君尘已经有些跑不动了,那背后的巨痛模糊了他的视线,他只觉得怀抱里的廖远山,越来越冰冷,冷得他自己,也受不了那种悲哀了,江湖是什么?不是一桌上好的酒菜,不是一场规矩严明的赌博。而是悬崖边的河流,一个不经意间,天翻地覆,山崩石裂。
他突然想起,五年前他十三岁,在漠北的尸山里靠捡死人身上的财物为生,这世上幸福的人大抵受不得苦,若是一点不如意,就觉得人生艰难难以继续,可那些不幸的人,却总能用幸运的人不能想象的方式活下去,但若非要深究起来,杨君尘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却颇多争议了,五年前那个大雨天,那一堆人快马而至,为首那个满脸桀骜不驯的中年人,和那只举着一壶酒的手,那个手把手指点剑法的身影,那个总是一脚戏谑的踢在他身上的男人,这五年的生活让杨君尘一度以为曾经的噩梦只不过是错觉,而现在错觉又回来了,怀抱里的廖远山已经死得不能再死,杨君尘像是气极了,脸上的表情时而开心时而难过时而愤怒时而大吼大叫,终于是断肠针的毒发,眼前一黑,再不醒人士。
“你不是说过你是天下最厉害的刀吗?为什么你就这么死了?为什么你不逃跑?”这是杨君尘心里最后的声音,不喜不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