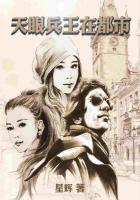我趴在亚克的背上。准确地说,两条宽宽长长的布带将我牢牢捆绑在这个人的背上。一条从他左肩绕过我的背托起身体,另外一条从右肩穿过把我和他固定住,带子在他胸前打成结。这样我的姿势虽然难堪,但是没有被捆绑的血脉不通的感觉。他将行囊分成两个分别固定在两侧,长剑插在行囊的外端。黑色的长袍包住两个人,将我口鼻留在空处。我所要做的事情不多,其实只有在我需要的时候动弹一下就行了。
洞里的情况远比想象中杂乱。从原来躺的地方五步远开始,地上掉落了各种短箭、击斧、锤枪,凝结成冰的血浆和碎甲片散落到处都是,洞壁上布满各种划痕。没有看到尸体,重物在地面拖痕一直延伸到外面的悬崖。在血崩渐渐平息的那段时间一定发生过极其残酷的激斗,奇怪的是我毫无知觉。
不知道鹰眼有没有受伤,我看着直直钉在墙上的一杆标枪。
外面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大雪早已停止,天色阴沉。远方高处连绵山脊线上的细雪被山那边的风倒灌卷起,雪雾飞舞与天色连接一起。群山的雪线下面雾气腾腾。整个世界灰蒙蒙的一片。崖边窄道往下的尽头是一个斜坡,鹰眼倒拖着几件有掩盖气息的奇怪气味的长衣开始攀越。他一边慢而沉稳地走着,一边不断抖动拖落身后的长衣掩盖地面的痕迹,时不时站立起来伸出沾湿的食指判别风向。转过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巨大山体之后,他将掩饰用的衣服埋在深雪下面,开始全力加速行走,深而有规律的足印在身后雪地上逐渐延伸成了一条看不见的虚线。
陪伴了我三个月的疼痛感消失了,偶尔在记忆中有些触动,如同深谷下隐约的回响。血凝术确实神奇,我所有的感觉都如此的清新自然,甚至连灵之护卫也被奇怪地融合消失了。刚才经历过的血崩假如没有灵之护卫的话,估计我所有的记忆都将给抹去,那就彻底成了一个初生的婴儿了,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呢?皮亚路克幻化的精血彻底和他痴爱的古黛儿结合在了一起,和我结合在了一起,这对于他又是否是幸运呢?他的灵魂现在去了哪里?
我不由呆呆痴想。
不管怎么说,我现在真正是一个人了,而不是由几百个人拼凑起来的怪物。身体的深处还有些轻微的颤动,我知道那是血崩之后正常的现象,如同地震以后的余震。我还会经历几次小的多的余崩,每次余崩的痛感将会越来越小,时间间隔将越来越长。那是以后的事情了,我既然能度过血崩,那些余崩算不了什么。
我开始凝聚思觉去体味。令我惊喜的是,我灵觉与周围元素的融合感回来了,身体里各种种族的部分完全融合——只是还是过于娇嫩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比较奇特的是,身体内现在即保留了个种族的特性,又完全地融合在一起。我能感觉到水元素的能量一丝丝地被我的血液吸取,皮肤聚集着火元素的力量,其他部位也各自吸取着各种元素。而且它们之间被身体内一种奇怪而不受控制的力量牵引着自己相互融合着,并没有任何那几个长老所说的各个种族不适应的异状。
可我找不到本原!
本应该是我生命本原的地方被一团奇怪的能量取代,不受我的控制却又时时和身体内的元素缓慢地融合着。可我知道,随着时间过去,即使现在吸取的能量如此微不足道,身体会慢慢强壮起来,能量会慢慢积蓄壮大。我终于恢复自由的感受了,我确实是一个人!可是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所有的大陆上,或许只有我这样一个怪人。
前面的鹰眼亚克依旧沉默着,和我印象中一样。他不是沉默寡言的人,也不滔滔不绝,他只是根据需要说话。几个月前的那段路程已经让我有些了解他。他任何时候都不会轻易放弃,也不会做徒劳无益的事情。所以,除了有些奇怪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其他我不用多问,到了应该知道的时候他自然会告诉我。不过我对于他的韧性还是很好奇,他几乎一刻不停地走了半天了,频率还是那样不紧不慢。我在他背后能感觉到他的肌肉骨骼的运动,他以一种奇怪的共振的方式进行着,这样使他实际花的气力不象看起来的那么大。而且和他的人一样,他只用他用得着的部分。
.
哥豪拉雅山脉的天气变化莫测,转眼就下起雪来。高冈高地吹来的温暖潮湿的湿气变成了鹅毛大雪。亚克在一个三面靠着山崖的凹地将我放了下来,风和雪花都到不了这里。他先用手拍出一个雪凳,拿大袍垫在上面,将还是包裹一样的我放在上面,然后抽出长剑将一件布袍割成细细的带子。我还在茫然地看着他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象是修剪枝叶一样裁剪起我身上的包裹。他将我身上过于宽大的衣服理顺,用布条将手臂腿上的衣服缠紧,将脚上包了几层布之后塞进不知道从哪个兽兵脚上剥下来的大靴子里,最后给我披上了连帽兽皮衣。我试着站起来,除了有些摇晃,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没有任何约束、没有任何疼痛的站立!
我有些百感交集地品尝着有些蹒跚地自由走动的感觉。那边亚克又从包裹里拿出些干肉,从怀里拿出个水囊一起递了给我。他倚靠着山崖就着雪块咬着干肉。
等我吃完之后,他才第一次对我说话:“月儿兰小姐,你有一位朋友希望我转告几句话……”
“我知道,”我转向了他,记起了皮亚路克对他说的话,想起皮亚路克的归宿,想起我一直在苦苦追寻的问题。我不禁问道:“人的灵魂究竟是在哪里?”
他皱了皱眉头,有些奇怪地看着我。或许我的问题是奇怪的,忽然能比较流利地说话也令他诧异,不过我知道他的表情并不是这个原因。我第一次听到了自己新的声音之后也有这样奇怪的感觉。新的声音确实娇柔清脆也很悦耳动听,除此之外,我感觉到话说出口之后,声音引起了周围元素的一阵奇怪的波动而产生了一种很奇特的力量,仿佛能够引起周围人身体里元素一起抖动。
“灵魂?你的在你那儿,我的在我这里。”他依旧靠着那里回答我。
那儿是哪儿?这里又是哪里?这是个奇怪的答案。不过我能明白他的意思,就象灵魂一样,用这个含糊不清的答案来回答也许比较合适,虽然似乎他并没有回答我。我接着问他:“是不是人的身体消失了,其他的一切也都消失了?”
他想了一会回答我:“阳光照射过了大地,因此万物就此生长。人走过了大地,地面就有了足迹。”
“人是否会因为自己过去的罪恶而遭受惩罚?”
这次他回答的很快:“只有过去里才有罪恶。现在没有,将来也没有。”
我静静地想着他的话。
他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行囊并捆扎好,又拿起水囊盛满雪块放进自己怀里。这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样寒冷的季节,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我刚才饮用的水。我不禁开始有些感激他,这时我这才注意到他脖子上有一道不深但是很长的伤痕。再仔细看,发现他前面衣服上有许多被划破的痕迹,但是后背却没有。这一定是在洞里留下的,他为了不让兽兵靠近我,居然宁愿自己受伤,而且走了这么长的路。
我不想欠这个人太多东西,可现在却又如此无奈。我只好让他坐下,对于现在的我而言他有点太高了。我感受着周围元素的雀跃,念动咒语,让元素聚集在身体,然后以手结引导元素的能量释放在他的伤口上。与一般单一的魔疗术不同,我用的是自己组合的一组咒语。我现在能召唤聚集的元素能量还是太少,不过效果可不是一般的魔法师所能相比。
“你为什么要救我?”我问他,一边让他把所有的伤口都给我检查,一边忍受身体里元素紊乱产生的不适应。真糟糕,一般魔法师穷其一生都在修炼强大的灵觉,可对于我的新躯壳而言,灵觉却过于强大了。
他非常惊讶地看着我跳跃着各种微弱的魔法光芒的手回答我:“因为你有和我一样骄傲勇敢的灵魂,而且你又如此奇怪。”
是啊,奇怪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太多的疑团需要通过我来解释,而我又恰恰无法解释。他身上的伤很多但是并不严重,最可怕的是左臂上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不过他自己好象显得满不在乎。
“你怎么不问问我为什么在这里,以及我带你去哪里?”在我处理完最后一道伤口之后,他反而忍不住问我了。
“假如你会告诉我的,我为什么要问。假如你不想告诉我,那我问了有什么用?”使用魔法而穿越身体的元素力量有些过于强大,引起了身体一阵晕旋。
“你不怕我带你去不应该去的地方?”他挑了下眉毛接着问。
“不怕,”我看着他的眼睛回答:“你有和我一样骄傲勇敢的灵魂。而且我能活着本来就是一个奇迹。生命本来就是如此,神给我的,我也拒绝不了,无论是好是坏。”
他笑了起来:“你果然很奇特,月儿兰小姐。你听说过流风吗?”
我到过亚里巴桑大陆的很多地方,知道很多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但是流风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有些疑惑地看着他说:“我知道在很多年前亚里巴桑大陆上有一个圣之盟,在欧卡亚大陆上有一个赤夜之山,还有甲亚桑大陆的黑月之会,在一些传说中他们在千百年前各自领导着自己的大陆。传说中我们是在一个很大的圆球之上,被海水包围着有各自神灵主宰的几个大陆和很多个岛屿。我不知道流风属于哪里。”
鹰的眼睛变的有些怅然,他遥望着被纷飞雪花混淆了的天空说:“赤夜之山早已经倒塌,黑月也被云彩遮住。神离开了亚里巴桑大陆,圣之盟也早已消散。我的名字是亚克·圣·恺撒,出生于很远很远的地方,也是流风的首领。”
流风并没有引起我的关注,倒是他的姓名我很熟悉。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氏,也许是南亚里巴桑大陆最古老的了。在我出生之前这个名字还统治着南亚里巴桑大陆大平原上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在离我出生之地以南千里之远的地方。传说之中这个姓氏是圣之盟中的一位。那些记忆中久远的岁月啊!我轻轻地说:“很久很久以前,我曾经独自在南亚里巴桑大陆的平原上流浪,曾经在远处看到过圣恺撒山顶的落日。”
“看来我们都在同一个地方流浪过。”亚克仔细地看着我,雪团在他手中被捏蹦出来。很久之后他才继续说道:“我曾经是圣之盟里的一个国家国王的儿子。岁月同样侵蚀了我祖先们的高贵品格,我的祖先们失去他们的国家是神的决定,我与你一样尊重神的选择。令我惊奇的是,据我所知你似乎是忽然出现在凯格棱特城堡,也是忽然出现在这个大陆上,但是你又恰恰知道这个大陆上的很多的事情。假如要说这个大陆上还有什么事情让我惊奇的话,那就是你的出现。”
我叹了口气。他的惊奇是有道理的,我知道我的很多事情是不由得别人不怀疑的。可多年以来,我从不掩饰自己,即使是现在。对于我而言,生命在十年前就已经失去,和蕾丝一起死去。寒风一阵袭来,我不禁拉紧了衣服。那双鹰眼很坦然地看着我的眼睛,我茫然地说道:“我在暗夜里生存了很长的时间,生命现在剩余给我的都只有那些夜中的记忆。如果可以,我宁愿从不曾在这个世界上出现过,但愿如此。神是仁慈公平的吗?那为何他让我们经受不一样的生命和痛苦?也许他真的离开了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还如此眷顾他?你应该离开我,我也不是你所想象的,不是任何人所想象的。”
他站了起来,伸手轻轻抚mo着我的头发,就象很久以前他所做的,就象蕾丝以前所做的。他轻轻地说:“我感到周围的元素是如此的悲伤与冰冷。生命之神并不总是给予我们想要的,我们也总如此无奈。或者我们可以忘记,选择记着一些事情。”
忘记?怎么能够忘记?无数的场景忽然涌进我的脑海,愤怒、屈辱、悲伤、羞愧紧紧纠缠住我。我变的狂燥不安,我对着亚克嘶叫起来,仿佛所有的一切都是他造成的:“忘记?能忘记饥寒交迫的时候在潮湿泥泞的路上爬动吗?能忘记所有的一切被残忍的剥夺吗?能忘记自己沾满别人血肉的双手吗?能忘记那些自诩为光明之神的臣民的大长老们对我所做的一切吗?能忘记吗?不,我忘记不了,那些已经刻在我这个身体上了。不要碰我,放开我。”
他的手象钳子一样紧紧抓住我,将我摁在他怀里,任我反抗。这该死的身体实在太弱小,我只能徒劳地挣扎着,愤怒地叫喊着。
“想想你的那个朋友,他是皮亚路克吗?想想皮亚路克。还有蕾丝,她是谁?你的姐妹还是母亲?这些都无关紧要,想想她吧,想想他们吧。”他在我耳边轻轻说着,逐渐瓦解了我的挣扎与嘶叫。
我不由泪流满面,有生以来第一次失声痛哭。
“你想去哪里?”在我终于没有力气完全平静之后,他放开了我。
我坐在雪凳上,无力地摇摇头。天下之大,我想不出能去的地方。月儿兰山谷没有了蕾丝,也就失去了对于我的意义,我也不想回到那里。或者,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那好吧,”他在我几步远的地方随意跺了跺脚:“我说说我的想法。我的行踪被我原来的王国知道了,那次柯哈玛河边的偷袭就是他们。他们派了些人到了高冈高地请求七湖盟不要帮助我,我们从高冈高地走的话将会非常的危险——我的喀琉斯国王非常的圣明,但是也不允许我的存在。而且七湖盟也知道了你,我们的危险都是一样的。因为一些原因,我必须回到亚里巴桑的一个地方去,有一些人和事情在等着我。去那里的另外一条路是通过欧卡亚大陆。我希望你现在能和我一起走,在我们翻越了哥豪拉雅山脉之后,你依旧可以在任何时候离开我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我无力地点了点头,茫然地看着远方。那里天色愈加阴沉,雪花迷漫的空中传来山风隐隐的呼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