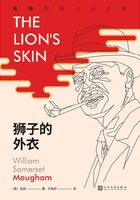第六卷2 (1)
淑就坐在那儿看着房间里没铺地毯的地板,因为这房子和过去的村舍差不多,不过坐落在城里就是了。然后她又注视着窗户外的景象,窗户上什么窗帘也没有。在对面不远的地方,石棺学院的外墙——寂静、暗淡、无声——把它四个世纪以来的阴郁、偏执和衰败气氛,都一古脑儿倾注进了她所住的这个小小房间里,夜晚挡住了它的月光,白天挡住了它的阳光。在这所学院的那边,还可以看清朱书学院的轮廓,再远一些是第三所学校的高塔。淑这时想到,一个头脑单纯的人产生了一种主导一切的激情之后,这种激情会发生多么奇特的影响啊;它竟然引着裘德把他们带到这样一个使人抑郁不堪的地方——尽管他非常疼爱她和孩子们——因为他还被自己的梦想萦绕啊。他渴望着进大学,但是那一堵堵学者们的大墙发出阵阵回响,把他拒之门外;可是即便现在他仍没有清晰地听见那些冷漠的回音。
他们没能找到另一个住处,自己爸爸在这个寓所里又没住的地方,这些都对那个男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因此他内心似乎笼罩着一种含而不露的恐惧。最后他才打破了屋里的沉默,说:“妈妈,咱们明天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淑万般失望地说,“我真担心这会让你爸爸心烦的。”
“我希望爸爸身体好起来,又有住的地方!那样就没有什么要紧了!可怜的爸爸!”
“不会要紧的!”
“我能做点什么吗?”
“不!到处都是麻烦、不幸和痛苦的事!”
“爸爸走开是为了让我们孩子有住的,是吗?”
“是的”
“离开这个世界比留在这个世界好,是吗?”
“差不多吧,亲爱的。”
“也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你们才没有一个好的住处,是吗?”
“哦——人们有时确实是不喜欢孩子的。”
“既然孩子这样麻烦,那为什么大人又要生他们呢?”
“哦——因为那是自然规律呀。”
“可是我们并没有要求生出来吧?”
“确实没有。”
“而且我更糟的是,你不是我亲妈,你当初要是不愿意,就可以不用要我。我不应该到你这里来——真的不应该!我在澳大利亚给他们添麻烦,在这里又给你们添麻烦。我要是没生出来该多好!”
“你是没有办法的啊,亲爱的孩子。”
“我想凡是孩子生下来时,如果不想要就立即处死,免得他们有了魂儿,免得他们长大到处乱跑!”
淑没有回答。她感到疑惑,沉思着怎样对待这个心事太重的孩子。
她最后认定,只要情况允许,她就将以诚实坦然的态度,对待一个像老朋友一样同情、分担自己困难的人。
“不久咱们家又要添一个小孩子,”她犹豫说。
“怎么呢?”
“因为又一个婴儿要出生了。”
“什么!”男孩发狂地跳起来。“上帝啊!妈,你绝不会又怀上一个孩子的,因为你已经遇到这么多的麻烦了!”
“不,我怀上了,真对不起!”淑咕哝道,眼里泪光闪闪。
男孩子突然哭泣起来。“啊,你不关心,你不关心我们了!”他极其痛苦地责怪道。“妈呀,你怎么这样坏,这样不讲情呢。你本来应该等到我们的日子都好过些了,爸爸的身体也好了,才要孩子的!你要让我们遇到更多的麻烦了呀!我们住的地方都没有,爸爸不得不被赶到别的地方去,明天我们又要被赶出去了,可是你不久又要生一个孩子啦!……你是故意这样做的!——是故意的——是故意的!”他啜泣着在屋里走来走去。
“你一定要原谅我,小裘德!”她恳求道,胸部也像那孩子一样剧烈起伏着。“我无法向你说明白——等你长大一些我会对你说明白的。好像我这样——是故意的,因为我们大家都遇到了困难!我无法解释,亲爱的!但是这——绝不是我故意的——这也由不得我啊!”
“就是——你一定是故意的!因为谁也不会那样来打扰我们,除非你愿意那样做!我不会原谅你的,永远永远不会!我再也不会相信你关心我、爸爸、或我们任何一个孩子了!”
他起身走到隔壁那个小间里去了,里面地板上已铺了一个床位。她听见他在里面又说:“要是没有我们这几个孩子,就什么麻烦也没有了!”
“别那样去想啦,亲爱的,”她非常断然地说,“快睡觉吧!”
次日一早她六点就醒来,决定起床,在早饭前赶到裘德告诉她他住的那个客栈去,在他出去之前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他。她轻手轻脚地起来,以免影响孩子们睡觉,因为她知道他们昨天奔跑了一天一定很累了。
她到了裘德的住处时发现他正在那个偏僻无名的小客栈吃早饭,他有意选择了这个极差的小店,为的是能省下钱来支付她的房租。她对他说了自己被赶出寓所的事。他一晚上都在替她焦急担忧,他说。现在是早晨了,不知怎么地,她被赶出寓所的事似乎并不像头天晚上那么令人忧郁丧气,甚至她出去没能找到另一个住处的事也不像最初那样使她深感不安。裘德和她都认为,他们不值得再费心思去坚持住一个礼拜的权利,而是要立即从那儿搬出来。
“你和孩子一定都到这里来住一两天,”他说。“这个地方是很粗陋,对孩子也不是很好,不过我们可以有更充裕的时间四处去找别的寓所。在那个郊区寓所不少——就是我从前常去的‘啤酒塞巴’。你既然来了就和我一同吃早饭吧,我的人儿。你肯定你身体没事吧?现在时间还多着呢,在孩子们醒来前赶回去给他们准备早饭完全来得及。说实在的我会和你一起回去。”
她于是和裘德一起匆匆吃完了早饭。十五分钟后他们便动身返回了,决意从淑住的那个太尊贵体面的寓所搬出来。他们到了那里,爬上楼去。她发现孩子们的房间里悄无声息,便带着怯生生的声调对女房东叫着说,请她把茶壶什么的带上楼去一下,他们好做早饭。房东马马虎虎地照她说的做了,她拿出带来的几个鸡蛋放进水开着的壶里,让裘德把为孩子煮的蛋照看着,她去叫醒他们,因为已经快八点了。
裘德俯身站在茶壶边,把表拿在手上计好煮蛋的时间,所以他就背对着孩子们住的那个小屋。这时淑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惊得他转过了身子。他看见那个房间的门——或者说小室的门——她推的时候似乎在门轴上转动得很沉重的样子——被打开了,淑正好倒在了门内的地板上。他急忙过去把她扶起来,转过眼去看地板上的那个小床,然而上面一个孩子也没有。他迷惑不解地看看四周才发现门后有两个挂衣服的衣钩,两个小些的孩子的身体就分别挂在上面,每人脖子上都系着一根捆箱子的绳,而在几码远处的一颗钉子上便以同样的方式挂着小裘德的身体。这个大男孩旁边是一把踢翻了的椅子,他那双呆滞的眼睛仍斜斜地盯着小屋,但小女孩和小男孩的眼睛都是闭着的。
一看见这个极度恐怖的奇特场面,他顿时像半瘫痪了似的,赶紧放下淑,取出小刀割断绳子,把三个孩子都放到了床铺上;但是,在搬运那些小身体短暂的时刻里,他的感觉似乎在告诉他:他们已经死了。然后他又抱起一阵阵昏过去的淑,把她放到外面房间里的床上,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房东叫来,又跑出去叫医生了。
他回来时淑已经苏醒过来,只见两个无可奈何的女人俯在孩子们身上发狂地想把他们救活,加上那三具放在一起的小尸体,这情景使他完全失去了自制力,最近的一个医生请来了,但正如裘德早已推想到,他来是多余的。孩子们已无可挽救了,因为尽管他们的身体还有一点热气,但据推测他们已上吊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这对父母恢复了理智,便推断出发生这件惨案的可能性:那个大男孩醒来后往外屋里看看淑,发现她不在,本来头天晚上遇到的和听到的那些事就使他心灰意冷,因此现在他那病态的心理就变得更加绝望了,所以就发生了如此的悲剧。他们还在地板上发现了一张字条,上面是那个男孩的笔迹,他用自己带的铅笔这样写道:
我们完了,因为我们太多。
淑一见这情景神经就彻底崩溃了,她有一种可怕的想法,深信她昨晚和男孩的那番谈话是造成这个悲剧的主要原因,她因此一阵痉挛,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这种痛苦有增无减。他们不顾她的反对把她抬到二楼的一个房间,让她躺在那儿;她一面喘息,瘦小的身躯一面不住地哆嗦,眼睛直直地盯住天花板,房东极力安慰她,但是毫无用处。
从这个房间他们能听到人们在楼上走动的声音。她恳求着让她回去,但大家让她相信,如果孩子还有一点希望的话,她去是只会有害无益的;大家又提醒她说,她必须照顾好自己,以免伤害到腹中的胎儿。她因此才没有回去。但她一刻不停地询问着情况,最后裘德下楼来告诉她已经毫无希望了。她刚刚能说话时,就告诉了他昨晚她对孩子都说了些什么,她如何认为自己是造成这个悲剧的祸根的。
“不是那样的,”裘德说,“是他的天性促成他那样做的。医生说在我们中间正出现一些这样的男孩——这种男孩在上一代里从没听说过——这都是新的生活观造成的后果,他们似乎过早地就看到了生活中所有的恐惧,而又缺乏坚韧不拔的力量去阻止那些恐惧。他说将来人们会普遍不愿在世为人,而这件事就是这种愿望的开端。那个医生是一个思想开明的人,但他却不能够安慰——”
因为她的缘故裘德一直克制住了自己的悲痛,但是现在他的的精神也垮了;淑因此而受到激发,对他产生了万般同情,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她一时忘却了对自己严厉的自责。等人们都散了的时候,裘德才又让她去看孩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