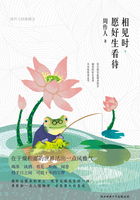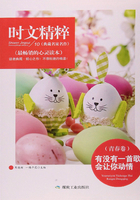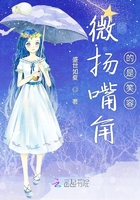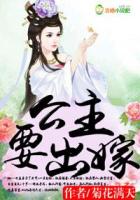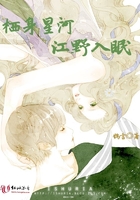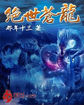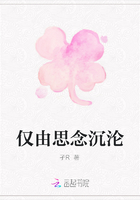乡村手艺人生存状态素描之三:铁匠
小时候,队上常常请铁匠来打铁。我们一放学就跑去看。至今仍记得铁匠在这三个地方打铁:天井屋、我们的老屋以及老杨家屋外的席棚。也还记得打铁的景象。
那是一间大屋,里面一口用青石和砖头砌起来的半人高的炉灶,一边连着一一个比木桶还要粗的巨大风箱,炉灶旁边竖着一截短粗结实的木桩,木桩上摆着一只铁砧。打铁的时候,有专门的人拉风箱,以保证炉灶里随时都有较好的火力,有两个体力很好的人帮锤。而铁匠则站在一边,一手里抓着一把长长的铁钳,不时翻动着火中的铁坯,一手握着叫锤(小锤,主要用途是要给帮锤的人指点打击的部位)在需要打击的部位敲着。
这里,只要炉火一烧起来,人即刻就可感觉到一种亢奋和力量。拉风箱的人有节奏地拉动风箱杆,将气流源源不断地灌进炉膛里,让炉膛里的火燃得更旺。炉膛向外喷射着色彩艳丽的火苗,发出嘹亮的呼啸声。铁匠看放在炉火中煅烧的铁块烧得发亮,便用大钳夹起,快速地拿到砧子上,同时,右手抓住叫锤,在上面一敲,帮锤的汉子则把大锤抡起了,准确地敲打在铁匠打击的地方,捶击声起,千万束火花立刻绽放起来,礼花一般耀眼夺目。
开始的几锤都是这样火花四溅,直到火红的铁慢慢黯淡。
在这短暂的打击过程中,我们除了看见火花溅出的优美,还可以看到打铁者那近乎表演的姿态。他们一般不穿上衣,只在面前罩一个被火星烙得满是大窟窿小眼的围腰,这样,他们的颈脖、他的胳膊上的疙瘩般的肌肉都亮在外头,他们的脸上滚着豆大的汗水,炉里的火光照着他们的脸,把他们的脸弄得像是上了彩釉的雕塑;
我们可以听到风箱在拉动中发出的那种似絮叨亦似歌唱的声音,以及铁匠和帮锤者共同演奏出的富有节奏的音乐。铁匠和帮锤者抡着的锤子重量是不一样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因而声音也不一样。那是“当—砰—当—砰”像鼓点一样的敲击,而节奏亦很快,一声追赶一声似的。打击开始,声音是软的,是小的,让人感觉有一点点绵软,随着铁慢慢变黯,声音也越变越硬,到后来便透着一种清脆。
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在当时体制下,请铁匠打铁是队长的事,打铁的地方也是队上安排的。因为当时土地都是集体的。虽然劳动的工具都是私人准备,但请铁匠实则是一件大事,某个农户要请铁匠到家里来打铁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铁匠的工具体积大,打铁需要很大的地方。
铁匠的工具主要有:风箱、砧子、大锤、小锤、钳子(不同规格)、剪子、宰子(一种切割工具)等。风箱是木质的,约有三尺长,一尺多的直径,主要用作给炉膛里鼓风,让炉碳充分燃烧。砧子是铁质的,似一个木斗,一侧有一个锥体,这是铁匠打制器物的平台。
乡村人家一般有这么一些铁器:锄头(大小挖锄、怀锄、羊角锄)、刀(菜刀、弯刀、镰刀)、斧头、钉耙、搪耙、锥子、剪子等。这些铁器,绝大多数是生产的工具,坏得快,因此每过一两年,队长就须把铁匠请来,给每家每户打制或者修理农具。
一眨眼二十多年了。自从上学、工作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打铁。我问父亲和大姐夫他们,现在还有没有铁匠来村上打铁,大姐夫告诉我说,自从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铁匠再也没有到村上来打过铁了,而是自己开铺子。农户要打制什么工具,就去铺里去订制。
听说我想写铁匠,大姐夫立刻讲起铁匠来。
相对于其他的行当,打铁首先要劳力好。俗话“打铁还须本身硬”,原就是说铁匠身体要好,要有足够的体力。
铁匠的力气主要用在打锤上。这是需要观察力也需要体力的。他举着叫锤,敲打着红红的铁器坯时,自己是不可能只轻轻点一下的。他想让帮锤的使力锤打时,他自己也得用力锤打;他轻下来时,帮锤的也会轻下来。因此,在力度上,叫锤的和帮锤的也是协调的。也就是说,铁匠每时每刻都是既要用心,又要劳力的。而且,铁匠一直站在熊熊燃烧的铁炉跟前炙烤,须臾不能离开,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行?
打铁需要消耗很大的体力。正因为如此,铁匠到农户家里打铁时,往往会受到更多的尊敬。农家要打铁,一般会做腊肉、糍粑等有营养、耐饿的食品让铁匠食用。
铁匠的技艺,主要体现在“火色”、“煮火”等方面。所谓“火色”,是指器具锋利、坚实程度的。譬如说刀,能吹毛断发,这就是火色很好了。而对于锄头来讲,没有火色,挖地的时候,锄尖就会上卷。
火色好坏,取决于器具刃口上粘的钢和淬火的技巧。打铁一般是这样一个过程,先用铁打制出器物的形状,然后,再在器物的关键位置粘上一截钢。钢是铁和碳的合金,硬度比铁要大,一般的家具,无论是刀,还是锄,要添钢,只有添了钢的器具才有硬度,才锋利耐用。但添钢是要技术的。先要按照大小形状取材,然后放在炉中煅烧,使之变软后粘在器具刃口上。铁烧红后,会生出一些铁渣,粘钢过程中,要把铁渣都捶打出来,不能让铁渣混在里面。如果混在里面,那个地方就会脱壳、裂口。
钢粘好了,还要淬火。淬火是把打好的铁器烧到一定程度时,再放入水中冷却。这里,铁器烧到什么程度最重要,如果达不到火候,火色就不好,烧化了,铁质的那一部分就会变形。所以掌握火候十分关键。这全靠铁匠的经验。
“煮火”是一种焊接方法。一般的铁器,都有一个联结木柄的接口,这个接口,俗称为“裤子”,如刀斗刀把的地方,钉耙斗木柄的地方等。制作裤子要把一个扇形的或是长条形的铁片弯卷成一个圆形,接口那儿就要煮火。
煮火是铁匠运用广泛的工艺。除了打制新器具要用,整修旧器具也常用到。整修旧器具一般也是“裤子”开口了,要么是羊角锄、钉耙断了一根齿等等,都需要通过煮火来维修好。
铁匠尊太上老君为祖师爷,因此,正月初九不开工。因为这一天,是太上老君的生日。如果这一天动了家伙,会冒犯师尊。传说某铁匠因为在这一天打铁,火星喷溅出来,把他双眼都弄瞎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巧合,并不重要。但打铁损坏眼睛却是事实。因为眼睛一直在受着烟熏火炙,而且大部分时间要一直盯着熊熊炉火和明亮的铁器。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铁匠上门打铁的事就没有了。铁匠们开了铁匠铺,人们要打制工具就到铁匠铺去。这时,铁匠这个行业顿时变得吃香起来。我的两个远方表哥打铁发家,顿时成为当地勤劳致富典型。
但好景却不长,因为:像镰刀、火钳、菜刀、甚至挖锄等等一些农具,商店里都有卖的了,而且价格十分便宜。譬如发镰,镰刀在鄂西一带特指一种割谷割麦的镰刀,形状与弯刀相同,刀身比弯刀略窄,刃口是用错错出来的,不能用磨刀石磨。这种镰刀叫做发镰。铁匠打一把发镰,至少要半个工,半个工只说工价,现在至少是十五元以上。而在市面上,一把发镰,只要两块钱,因此,现在几乎没人打发镰了,而主要是买。
乡人们怕麻烦,不再去铁匠铺去打铁,而是去供销社买一些铁质农具了。
铁匠的生意渐渐冷清下来。
我们家住的上仓那一片(大约有十几个自然村,一度时间曾做过公社),原来少说有十几个铁匠,可现在只一至二个了。一位名叫唐家明的铁匠就住在河下一个叫做温泉池的地方,我去了两次,没有见到他。他老婆朱永林说,他出坡去了。因为天道(天气)好,他必须去做田里的活。
这话告诉我,唐家明打铁现在只能算是业余的了,而主业应该是种地了。
我问朱永林唐家明为什么不一门心思打铁呢?朱永林说,现在打铁赚不到钱,养不活人,主要是燃料贵了,打铁要好煤,一吨“好块子”(块煤)要600多块钱;还有就是请人帮锤,工钱也高,请个人帮锤,一天要40块,还要供吃缴。算下来,打一天铁,只和给别人做小工差不多。
朱永林说着把我带到楼下的打铁铺里,看了一看。
第二次,我去,因为小孩生病,他带小孩去打点滴去了,又没见着。
因见不着唐家明,回到县城,我在城郊的郑家花园找到了打铁的徐龙。
徐龙的一支腿瘸了,走起路来有点跛。一见面,我脑子里就想起了那句“打铁还须本身硬”的话,有些奇怪,为什么他一个跛子竟然要以打铁为生?
一了解才知道,他父亲是个老铁匠,而他原本就在镇上的铁业社里做事。因为铁业社垮了,他们下岗时,单位按照工龄给每个人算补贴,他没要补贴,而要了铁业社的一架气锤。
他的腿是六岁时被炸弹炸了——父亲准备炸狐狸的炸弹,藏在衣柜里,兄弟两个饿,想找点吃的,把炸弹找出来了,以为是什么零食,准备吃,所幸比他大一点的哥哥认出了这是炸弹,一巴掌打落了他手中的炸弹。炸弹在他腿上爆炸了,因此他的腿也残疾了。
这当然是闲话。
徐龙下岗后,凭着一架气锤和自己的聪明办了一家铁匠铺。
在徐龙的铺子里,我看到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铁匠铺了。他使用了汽锤、鼓风机、电焊枪。
这些新工具的出现,使打铁具有了几份现代感,同时,传统的上门作业方式、多个人配合一起作业的方式等等也发生了改变,人体的劳动消耗减少了,效益也提高了。
各个过程变得更加简单。把鼓风机一开,炉膛的火烧旺起来,一块铁一会儿就烧红了,然后用铁钳夹起,放入汽锤下面打击,只要脚触动开关,便可控制打击的节奏和力度。
我就在汽锤有力浑厚的“砰砰”声中,和徐龙进行了如下的交谈。
问:现在主要打制什么铁器?
答:农具厂破产的时候,正值移民搬迁,有很多单位建铁围栏,围栏上面需要卫矛,买不到,我就开始给他们打卫矛。搬迁结束以后,三峡库岸治理部门要挖石头,需要大量的十字镐,我就打十字镐。现在,文物部门整修老建筑,需要过去那种门环门镣,我就打这些东西。
这就是说,徐龙这个铁匠,实际上已经不是打制乡村农具的铁匠了。他打制的主要是城市建设所需要的工具。这不能不使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东西的需求是有限的。一旦这些建设竣工,可能再没有人光顾他的打铁铺。
我问他以后怎么办,他说,那时就再去找别的活干吧。
我从徐龙的话里听出了一点无奈。
200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