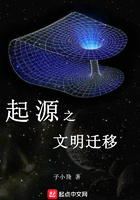我把自己惨遭菲利普劈腿,并决定和安琪、菲利普统统断交的事通通告诉了西尔弗曼医生。“你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许有点一根筋?我这一路听下来,觉得你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别人吹毛求疵,而对自己就更加挑剔严苛。在你看来,这个世界必须非黑即白,你的道德观里容不得任何中间路线。”西尔弗曼医生听完后对我的想法有些不以为然。
“你张口闭口就是那个‘金兰之约’。它真的是金科玉律吗?人性复杂多变,是人就难免犯错。你能否试着对别人再宽容些?也试着不再苛责自己吗?有时我觉得这个‘约定’就是你强加在自己身上的一副锁链。”
我瞪着他,泪水瞬时盈满眼眶。我觉得他的话像是责难,像是攻击。
“你要明白,对人宽容就是对己宽容。”
我像是被逼入死角的小兽,重重威胁之下浑身的刺都竖了起来。“我只能这样。这是我唯一能做好的事情。做好自己是我自个儿选的。既然选择了,那就必须坚持下去。”
“我明白。说下去。”
“至于能不能对别人好点儿,我实在有心无力。我也想和颜悦色讨人喜欢,可问题是我做不到,理智总会在我需要它的时候弃我而去。总会有人无端把我给惹毛,我要么恶声恶气,要么找茬跟他们大吵一架,要不就脑袋里轰地一下炸开了锅,任凭仇恨蒙蔽双眼。这一切的一切我都无力掌控。”
他点点头,提笔在本子上记了点什么。
我又开始揪指甲边上的肉刺。“外婆从没教过我如何为人处世,我只能靠自己摸索。她总说我坏,将来一定得下地狱,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地要行得正,站得直。那个‘约定’,还有我给自己列的条条框框,就是我过河时摸的那些石头。”不知为什么,我陷入深深的不安之中。这次对话似乎拨动了隐匿在内心深处、从未被触及的思绪。毫无由来地,我突然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因为我没办法对别人好,所以我只有努力做好自己,”我哭诉道。“我就是想做个好女孩。”我哭得喘不上气来,一个劲地用衣袖擦着眼睛,拿手背抹着鼻子,环抱着肩膀瑟瑟发抖,牙齿也跟着咯咯咯地不停打战。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四岁那年,一样的孤独,一样的无助。
我在希尔弗曼医生这儿看病看了这么多年,这似乎是他第一次真正与我心意相通。我看到他眼里的同情,看到他嘴唇微微张开,就像最后他终于理解了我的苦楚,并为之动容。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如果我是个真正的好女孩,他们就会要我了。”我的声音低得几乎没人能听见。这个念头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我会如此心烦意乱?然后,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妈妈的声音:“记得要做个好女孩”,原来如此,原来这个声音就是所有一切的“因”。我抬手抹去脸上的泪水,压根就没顾上桌子上的纸巾盒。而后,我低下头看着双腿。
“霍莉,你是个好女孩。你一直都是。你外婆说的那些话都是骗你的,别听她的。”
他听上去不像是个心理医生。那声音温暖如怀抱,透着慈父般的殷殷关爱,它让我内心深处的某一角骤然塌陷。“你是个了不起的女孩。如果你是我女儿,我会为你骄傲的。”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几乎相信有人竟会以我为荣。我仰起头来注视他的眼睛:“真的吗?”
“真的!”他说着,从盒子里抽出纸巾递给我。我听话地接过来擦干了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