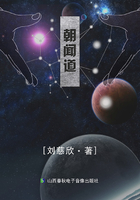回家后的第一个周末,凯伦便向我传授了溜进演唱会后台的诀窍。
“面带微笑看着保安,什么也不要说。身体顺势靠着一侧的墙壁。如果他问你话,你就说你在等朋友黛碧。”
于是,我靠着墙壁,冲着保安一个劲地微笑。那保安用眼角的余光打量我一番,神情中的严厉与怀疑一览无余,然后他把我晾在一边,自顾自地直视前方。
凯伦离我几步之遥,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夹着香烟,眼神有些涣散。
“你在等人?”保安问,声音远比他的表情讨人喜欢。
“是啊,”我微笑着说。“在等我的朋友黛碧。她应该马上就到。”其实压根儿没什么叫黛碧的。我只是遵照凯伦的话,鹦鹉学舌罢了。我原地踩着小碎步,一副冷得发抖的样子,当然,这也是凯伦事先设计好的桥段。
这时走来三个操着英国口音的男人,他们向保安晃了晃手中的通行证,保安见状立马放行。从门口走过时,他们看了我一眼。
“站这儿不冷吗?”其中一个问我。他原路折返,向保安说,“她是和我一起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通行证,递给我。
凯伦即刻撒腿跑过来。
我冲着他笑了笑。“我还有个朋友,”我说。凯伦也扬起一张笑脸。
“很高兴认识你们,”男人同样一脸笑意。他一手挽着一个,把我们带进了后台。
“我还有事,你们自便。”说完便和其他乐队后勤迅速走开了。
凯伦一把抱住了我。“你太棒了!”
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知名乐队,不同的场馆,不同的乐曲,不同的乐队后勤在舞台上忙前忙后。然而,此情此景,我却早已习以为常。我看到一群乐迷,拓克乐队演唱会上也有她们的身影。舞台边,她们依旧摆出一副互不相识、寂寥落寞的样子,可一到洗手间,她们又立即称姐道妹,亲亲热热地聚在一起。
“这有什么讲究吗?”我问凯伦。
“如果女人成群结队,男人是不会过来搭讪的。扎堆的女人让男人发怵,所以尽量不要拉帮结伙。最好是一个人呆着。男人总爱勾搭落单的女人。”
“你想一个人呆着?”
“说什么呢,你开玩笑吧?老天,当然不是了!”她放声大笑。“我就在你旁边站一晚上,捡你挑剩下的。反正我脸皮厚。”她一心只想再回英国,那对她而言至关重要,她解释说。人必须勇往直前,哪怕是乏人问津的剩女也不能自暴自弃。她接着说,站在我身旁远比一个人呆着强。不但所有的男人都会过来打招呼,而且我也是一个难得的好伙伴。
凯伦说我是个难得的好伙伴,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我忍不住开心地笑了,结果招来了更多的男士。
整个晚上,男人们趋之若鹜,不过每次我都婉言拒绝,告诉他们我已经有男朋友。于是,他们转而向凯伦示好,凯伦不时冲我会心一笑。
我和凯伦没商量好事后我怎么回家。演唱会将近尾声,她搭上了一个乐队后勤,随后我跟他们一起去了宾馆,我坐在大厅过道的地板上,背靠着墙壁打盹,等着他们完事后能捎我回家。虽然这有点无聊烦人,但今晚确是一次新奇的经历,一次长见识的机会。下一次,我会另做安排或自备车费。整装待发,迎接明天!
接下来的一个周末,凯伦留宿宾馆,我打车回家。我已深谙其中的门道,学会了享用免费的食品,免费的啤酒还有免费的消遣。我成了出入后台的行家里手,写信时特地将每一个细微末节告诉特雷弗。
几周下来,我心情不错,尤其是收到特雷弗的来信时,更加喜不自禁。但是,好景不长,这份喜悦在漫无边际的等待中逐渐消退。我接连不断地给特雷弗写信,一天不拉。我省吃俭用,克扣日常开支,从中挤出寄往英国航空信件的邮资;一下班,我便立刻飞身跑回家中,看看邮箱里有没有我日思夜想的信件。但是,抑郁还是无孔不入。好几次,我歇斯底里,几近发狂。
拓克乐队要到来年二月才会来美国巡演。目前他们正在录制乐曲,接下去的几个礼拜一定会关在录音棚里全力以赴。特雷弗在信中说,他们将会在圣诞节发行新专辑。忙完这段后,他就可以好好歇上一阵。我很高兴终于有个让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上班的时候我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同事。
又是几个月,缓缓而过。这期间,演唱会一个接着一个,那些夜晚将我从萎靡不振中搭救出来;我看上去还算精神,这全靠肾上腺素和各种各样的刺激勉强支撑。到后台还能顺便吃点东西,要不然就得饿肚子。然而,倘若两场演唱会之间相隔太多时日,那么我离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