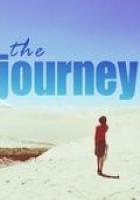伟大的艺术永远不会过时。再过一百年,我想不会再有人还会记得当今的那些“天皇巨星”,但只要人类一息尚存,在波恩,在维也纳,在许多其他的国度里,每年都会有贝多芬音乐节。贝多芬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这里不妨引用1812年贝多芬在给友人贝蒂娜·勃伦塔诺(BettinaBrentano,1785—1859)的信中的一段话,作为本章的结尾: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
哥尼斯文特
搭乘电车越过莱茵河大桥前往河东南边的哥尼斯文特(Knigswinter),这里有波恩附近最著名的历史名胜龙岩山(Drachenfels)。紧靠42号公路的山脚处有火车站,乘坐电动牵引火车经半山腰的王宫龙堡,可直达龙岩山顶。山巅处高耸着十二世纪科隆大主教建造的古堡废墟,登高四望,一览无余,是莱茵河上的佳景之一。174年前,拜伦曾站于此,把这佳景写进了他的长诗《哈罗尔德游记》。
在古堡废墟脚下有一个山顶花园,园内有个被封住的洞穴。中世纪著名史诗《尼贝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里的屠龙英雄齐格弗里德(Siegfried)就是在这个山洞里同潜藏在莱茵河底的那条恶龙大战后将其杀死。瓦格纳正是根据这个题材,花了整整二十六年心血完成了由四部乐剧组成、结构庞大、气势恢弘的《尼贝龙根指环》。
龙在欧洲历史上一直就是在水底兴风作浪的邪恶魔鬼的象征;不谋而合的是,在秦始皇之前的中国历史上,龙也是在水底兴风作浪的邪恶魔鬼的象征。大禹治水驱龙蛇,说明龙本来是坏东西。本人对那虚假丑陋、张牙舞爪的龙从来就没有好感,它不过是历来专制者和被愚弄者们所顶礼膜拜的图腾罢了。纵观历史,那些华夏优秀文化的创造者和哲人们,很少有谁提到或称颂过这怪物。他们大多不信鬼神,自然也不会对这非神非鬼、似蛇如鳄的怪物感兴趣。然而从秦始皇开始,龙却被改头换面,暴君竟然宣称自己为“祖龙”了,大概是需要自我神化来吓唬芸芸众生。自此,皇帝的尊容被称作龙颜,朝服称龙袍,卧榻称龙床,皇子皇孙就算是“龙种”了。从嬴政到溥仪,作为“天子”的“真龙”出了一条又一条,就算有“龙的传人”,也只能是那些皇子皇孙,哪里会轮得到唱《龙的传人》的那些仁兄们自作多情呢?至少本人不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当然多数中国民众对龙的崇拜,是出于对千百年来传统的尊重和善解,对于龙这个概念的真实历史并不太在乎。
龙岩山是齐根山(Siegengebierge)七座山峰中最大的也是最靠近莱茵河的一座,其他几座山峰,有的在过去已经被石矿挖走了许多;建造科隆大教堂所用的石料全采自于此。山坡上布满了葡萄园,这里是莱茵河上葡萄园的最北端,大河流淌到此,莱茵风光也就到此为止了。这里也是著名的“龙血红葡萄酒”(Drachenblut)的产地。
漫步下山来到山腰处的王宫龙堡(SchloDrachenfels也称Drachenburg),这是莱茵河上比较新的古建筑,落成于1883年,也就是德国统一后的第十三年,至今也不过一百年多一点,那建筑维护得依旧如新,塔柱上的人物雕塑金碧辉煌。这天参观的人不多,进入宫殿后,大家屏声静气地在楼上楼下观赏室内的建筑艺术和许多油画。
不一会儿从楼下大厅里那架大钢琴上传来了贝多芬著名的《c小调钢琴奏鸣曲》(“悲怆”,op.13,“Pathetique”)。我赶忙下到大厅,但见一位满头霜雪的老人坐在大钢琴前尽情地在演奏着。我停下来静听他演奏,同时也注意到,那高高的窗格上五颜六色的玻璃中居然有一块是贝多芬的头像。在波恩,贝多芬的确无处不在!
那位“老钢琴家”弹完第一乐章就停了下来,慢慢站起,由一位老太太扶着走了出去,原来他的腿有点瘸。见一位年轻人跟在他们后边,就上前去向他打听“老钢琴家”的名字?“钢琴家?哪里!他不过是个二战老兵。”这个回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德国文化!二战以后,电影里出现的德国军人的形象都很雷同,个个都是杀气腾腾;而我在德国,却偏偏无意中就遇上了这样的德国老兵。
阿登纳——从73岁开始
从山上西眺那滔滔北去的莱茵河,又想起了一位德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康拉德·阿登纳(KonradAdenauer,1876—1967)。脚下的小镇吕恩道夫(Rhndorf)是他的长眠之地。
当波恩在1949年被定为联邦德国(西德)的首都时,德国几乎是从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1950年,德国著名指挥家切利比达克(SergiuCelebidache,1912—1996)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原柏林爱乐音乐厅的废墟上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从断垣残壁间响起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这也许正象征了这个抚育过贝多芬的伟大民族在废墟上重建的开始。
当时的德国是被占领国,连主权都没有,更不用说法国的敌意,苏联及其东欧各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在这最艰难的时刻,阿登纳担起了领导西德战后重建的重任,这时他已经73岁。到1963年87岁的他因为健康原因告别政坛时,他领导下的西德已经从一个被占领国变成了重新获得主权的国家,政治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经济上不仅抚平了战争创伤,并且再次创造了德国的奇迹成为经济巨人。
阿登纳沉着、坚定,记忆力惊人;他注重礼仪,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还在战前当科隆市长时,他的司机驾车不慎撞上了电车。颧骨撞碎血流满脸的阿登纳从汽车里爬了出来,自己镇静地走去了医院,而只受了点轻伤的司机却被担架抬走了。
希特勒上台,阿登纳拒绝合作,两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仍被软禁,监听;退休金被剥夺,银行存款被冻结,几乎被断了生路,但凭借顽强的毅力他活了下来。
1949年他当总理后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成功地说服盟国不要大量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这为德国的复兴留住了“硬件”上的保证。1951年,阿登纳和德国主要劳工领导人之间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让工人与工业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这使得西德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没出现重大的劳资冲突。他的带头,加上经济部长、“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的有效管理,使西德赢得了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
1953年4月,阿登纳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邀首访华盛顿。他把住机会舒解了美国人因二战造成的仇德心态。当时美国舆论还充满反德情绪,认为美国应该拒绝参与欧洲防务。在他的疏通下主张美德友好的副总统尼克松不断为德国人说好话,并提到了美国独立战争年代普鲁士军官冯施托伊本男爵协同乔治·华盛顿训练美国军队,成绩斐然,并赢得了弗吉山谷(ValleyForge)那场关键战役的胜利。阿登纳则在施托伊本的塑像前献了花圈。他的访美大大地改变了美国舆论对德国的敌对情绪。接着阿登纳又先后六访美国,与美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